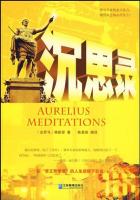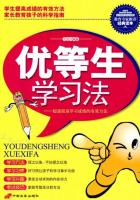我的佛教学术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初算起已将近30年了,其中因“文化大革命”浩劫等原因而长期中断,实际时间只有15年光景。这期间的研究工作,大体上经过了如下历程:佛典的校点、注释,佛教哲学研究(包括个案、微观研究和整体、宏观研究),佛教文化研究。这些研究前后交叉、彼此渗透,不是先后分明、截然分开的。
一、审慎选择,知难而进
我在北大念书时,兴趣最大的是中国哲学史,主讲教师是冯友兰先生,我是课代表。毕业后我被分到人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正合自己心愿。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到现代,长达数千年,一个人生命有限,要做到对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深入研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经过反复考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为研究重点。这段历史中佛教和道教占很大比重,我决定先主要研究佛教,尔后视情况再兼及道教。就是说,在专业方向上我是从中国哲学转向了中国佛教,也可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兼顾并进。当时我主要考虑的是:其一,佛教内容异常丰富,也很重要,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的影响可谓浃于骨髓,润于四体,既深且广,从事这项工程的研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其二,从哲学角度研究佛教,既可以揭示佛教思维的内核和特征,拓宽佛教的研究领域,提高佛教研究的学术水平,又可以利用佛教哲学研究的成果来丰富中国哲学的教学内容,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研究互促互补,相得益彰。其三,由于佛教研究难度很大,时尚又有一种偏见,以为研究宗教就是信仰宗教、宣传宗教,涉足者不免存在一种无形压力;还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使佛教研究成为冷僻和被冷落的领域,治佛教者稀稀,研究成果寥寥。我想投身这一领域垦荒、耕耘,也许是更有意义的。
确定以佛教为研究方向,也可以说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不是容易下定决心的。因为研究佛教,一是难,所需知识结构要求很高,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哲学等知识。二是乏味,虽然有些经典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但是那些戒律书和讲修持的书读来却味同嚼蜡,使人昏昏欲睡,近似哲学的著作又相当艰涩,宣扬佛国世界的典籍则使人玄惑不解。三是研究条件差,主要是客观物质条件(如资料、出版等)和舆论气氛不够好。但是,面对这些困难,我有一个信念,学术研究,就是克服困难、解决疑难的过程。战胜困难、征服疑难,就能获得成功。一个人要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不就是要知难而上、百折不回,以取得新的突破吗?
二、下苦工夫,整理佛典
研究佛教的基础环节就是要通读原著,要深知佛典所蕴涵的义理。读一些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基本派别的代表性著作,对于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一切研究工作都无从谈起。读佛教典籍可有不同的要求和方法,而读透几本,以总结经验、掌握方法,更具有重要意义。而要读透佛典,最切实有效的方法是,对佛典进行校点、注释、今译。虽然一个人不可能对汗牛充栋的佛典都进行整理,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是否做过整理佛典工作是大不一样的。我把整理佛典工作自觉地视为研究佛教绝对必要的训练和准备,于是和几位同道友人就中国佛教的重要典籍进行较系统的标点工作,出版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全书四卷,已出三卷八册)。我还就华严宗的代表作《华严金师子章》进行校释,成《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此书除校勘、注释外,在每章之后,还用现代语言串讲该章义理,并在书前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系统地介绍该书作者、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的生平,评述《华严金师子章》成书经过,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剖析了《华严金师子章》的宗教哲学思想实质。后来我又在原有校释的基础上,撰写《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将由巴蜀书社出版。我深刻地体会到,整理校释一种佛典,不仅对于研究这一佛典及其作者乃至作者所代表的宗派思想具有直接作用,而且也为研究其他佛典、人物和宗派积累了经验。
三、深入一点,全力突破
按照研究工作的一般程序来说,首先要进行个案、微观的研究,然后再进行整体、宏观的研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真正科学的宏观研究。就一项具体的研究工作来说是如此,就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生涯来说也是这样。我对佛教的研究,是从魏晋南北朝佛教人物开始的,我选取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道安、慧远、支道林、僧肇、竺道生和梁武帝萧衍为研究对象,进行逐个研究。我要求自己深入一点、全力突破。对每一个研究对象都要写出专文。我采取的方法就是将研究对象的著作和有关传记等史料,尽可能无一遗漏地反复阅读,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阅读十多遍,僧肇的《肇论》则阅读二十余遍。在阅读时我注意勾勒出书中哲学观点,寻觅其间的思想关联,体会全书的精神实质,并随时记下读后的感想、评语,形成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独立看法。这可谓“入乎其内,出乎其中”。然后,博采众家之长,尤其是前辈学者如汤用彤先生等有关论著,校正、调整、充实自己的看法,再度构思,略前人之所详,详前人之所略,形成专文。我在研究过程中,绝不掉以轻心,力求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我的第一篇佛教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发表在当时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新建设》(1964(3))上。随后我又研究道安的弟子慧远,撰写成两篇论文《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和《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我以为只有对佛教主要代表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清理和总结佛教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也只有从整个时代佛教思想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才能科学地评价佛教思想代表人物在佛教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深入一点,可以带动全面。事实上,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为研究整个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四、宏观探索,剖析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通史和断代史居多,而剖析佛教哲学体系的论著则不多见,并缺乏佛教入门书。广大读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佛教思想。我有感于此,就想写一本介绍佛教的综合性和知识性的书。后来由于个人佛教知识的逐渐积累,宏观探讨的条件也初步具备,又参照同行的著作,着手撰写了《佛教哲学》。这是从整体上宏观地进行研究、阐述佛教哲学体系的著作。此书的重点是解剖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对佛教的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逐层加以剖析。在增订本(即出)中又增加了认识论部分。我在书中运用的方法主要是:1.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根据佛教哲学历史演变的轨迹,筛选出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着理论思维成果的主要概念、范畴、命题和论纲,依其固有的逻辑,勾勒出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力求做到既保持佛教哲学思想体系上的整体性和具体性,又注意到佛教哲学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间断性。2.努力用现代术语表述佛教思想,介绍和解释佛教内容。尤其注意全书的知识性,寓观点于资料之中,淡化感情色彩,排除主观情绪性,多做客观的平实的叙述。3.摒弃“大批判”作风和简单化方法,注意如实地把佛教作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发掘出其特殊的价值与贡献,同时揭示其失误与流弊。努力做到辩证分析,合情合理。
五、开拓研究佛教文化
近四五年来,由于现今人们观念深处的传统文化与扑面而来的改革开放浪潮的碰撞,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反思热潮,这股思潮也深深感染了我,使我产生了探索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强烈冲动。同时,在撰写《佛教哲学》的时候,我就感到这本书偏于理论性,比较适合学术界的需要,对于较多的读者来说,更需要的是对佛教做全方位的立体化的概论性著作。这又使我萌发出从宗教文化实体的角度来论述佛教的设想。于是在完成《佛教哲学》后,我又开始撰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我撰写本书的注意点集中在佛教文化本身的结构及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两个方面。具体说,一是力图用系统和结构的观念来阐述佛教,强调佛教“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并从佛教的历史、经典教理、仪轨制度、寺院殿堂和名胜古迹等六个方面,多维地阐释佛教文化,指出佛教不仅包括信仰、思想和典籍,也是形形色色的物质实体。再是具体揭示佛教诸要素的文化层次,指出佛教的信仰观念是佛教文化的最深层结构,是其他诸要素的核心,佛教信仰通过思想义理的宣传、伦理道德的约束、寺院殿堂的作用、仪式轨范的感化,逐渐渗透到民族的情感内核、心理结构和民风习俗,深深地根植于社会实际生活之中。二是力图用文化比较学的观点,着重揭示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横向联系,通过对佛教与中国政治意识、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民间习俗的辩证关系的阐述,凸显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是开拓研究领域的必由之路。我所做的也是一种初步尝试。
治学虽然也有某些普遍性的规则和方法,但是任何人的学术研究都带有自身的特征。一个人的治学之道只对本人具有完全的意义,对于他人则只有借鉴作用。治学之道归根到底在于创新。佛教研究使我的学术生涯得到充实,丰富了我的生活意义,平添了不少乐趣。我今后仍将不断追求,努力探索,继续开拓,为伟大祖国的文化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原载《文史知识》,19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