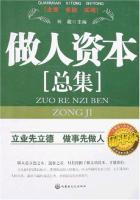记者:您和任老有师生之谊,昨天任老仙逝,您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方立天:是的。任公是我的老师,季老也是我的老师,但我没有上过季老的课。我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时候,任公给我们上过课,不过上得不多。任公是我学术上的导师和榜样,他走过的学术道路,也是我所走的路。我们都是从搞中国哲学研究转到搞佛教研究,我们的学术道路是一致的,所以我把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他是我的老师,是我治学方面的榜样。
任公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我国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等,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主导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范本。他发表的一系列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
他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期间,我先后担任副会长、常务副会长,配合他做了一些工作。他很敬业,很多事情他都很具体地抓,很注重落实。他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工作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担任会长期间,对推动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研究队伍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我们搞中国哲学的后辈学人,都受益于他。除此之外,他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有开拓之功。
方立天:是的。在宗教研究方面,任公的涉猎面也很广,包括佛教、道教,还有儒教,他都有所涉猎。
我个人认为,任公是新中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开拓者。他是开拓者,也是组织者、推动者,对新中国的宗教研究影响非常大。
记者: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方立天:是的。因为他当时写了几篇研究佛教的文章,被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评价很高。毛主席做了批示,后来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他是第一任所长。这个所的成立,是中国宗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记者: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
方立天:是的。这标志着中国宗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宗教研究。任公在这方面的开拓、组织、推动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他的专长是佛学,在佛学研究方面,贡献更大。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
记者:如《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方立天:对。我还为他这本书写过书评呢。他的佛教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研究佛教,这是很重要的,在当时可以说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道路、新方向。今天仍值得我们肯定和继承。
记者:他对道教也很有研究。
方立天:是的。因为他研究《老子》,而道教和《老子》又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主编过《中国道教史》,还有大部头的《道藏提要》,这些都是道教研究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值得我们怀念。
记者:任公提出的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但有些学者并不赞同。
方立天:这是他的一家之言。我曾经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那是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太原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中午要吃饭了,在电梯里,我问他:“任公,你怎么把儒学说成是宗教?”因为我和他交往较密切,说话随便一些。他开玩笑地回答说:“大概因为我是研究宗教的,所以就把儒学也算成宗教了吧。”他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论证这个观点。我尊重他的观点,但直到现在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个问题还涉及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等对儒学的看法,他们三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这个属于百家争鸣,很正常,但很重要。
另外一点,在宗教学的整体研究上,他强调要对宗教进行批判,并重视无神论的宣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见解。
总之,中国宗教学研究今天发展繁荣的局面,和任公的努力、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他应该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有些人不赞成他的学术观点,但我们应正确看待他的贡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07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