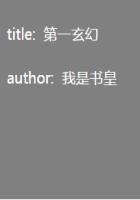既没出汗又没有粗重喘息的小离心抬头望了眼不远处的巨大城廓,便松开了提着江天夙的右手,而江天夙自然而然也就一头栽在田间的小道上,幸好也就是前几日的那场暴雨下得这泥土有些松软和龙珠的洗刷,不然以小离心的突然撒手和江天夙的半吊子身体,最轻的恐怕也就是要在没有美娘子陪伴的床上躺倒风雪迎新年。
小离心蹲了下去,伸出一双小手抱起了依旧趴在江天夙身上的小雅龙。
小离心没有去看被自己仍在地上的江天夙,而是将那双大眼睛望向了那一片又一片的金色麦浪。
金麦舞风千顷浪!
小离心一个人就这样望着连接于天际的麦浪,静静地看着,默默地红了眼。
少年不识愁滋味,但这样一个看起来及笄般大的丫头却绝不是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神情。
小离心蹲在那里,呢喃开口。
“那年大雪,师傅说是师姐把我从茫茫雪地里抱到了宗里,师傅说等到来年春花生便把我找个合适的人家送出去,是师姐和他整整磨了一个冬天,最后师傅熬不过师姐的倔脾气,松了口。我呢也就是成了我师傅的第二名的弟子,也就是我师姐的师妹。”
“其实在御灵离字辈中原没有心字一说,所以一开始宗里的大多数人包括我都不知道师傅为什么给我起了一个驴头不对马嘴的离心。十岁那年,师傅跟我说了一句都是缘分,合着本就该叫离心,这句话到现在我还没有真正地搞懂说的究竟是什么。十五岁那年,师傅告诉我是世上罕见的入仙体质,但若是离心,则更有鲤鱼跳龙门之绝妙。”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离开了我自己本心的想法,就能够像师傅、师祖那样厉害地可以保护很多人,或者可以说就是很简简单单地像小时候师姐保护我那样去保护师姐,最最不济地也可以再不用躲在师姐的身后,而是能够站在师姐的身旁。”
“但是,我真的很笨呀!到现在都没有能够领悟师傅所说的离心。是呀,到底什么叫离心?”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相信世界依然还活在这个世上,或许等待着有一天,有个人能够把她找回来。这个人可以是我,当然也可以是你。”
仿佛一夜不在的那个天真烂漫的小丫头不再老神叨叨下去。
晨曦缓缓,早间金色的日光渐而不在,那袭人砭骨的凉气也渐而温暖。
小离心站了起来,怀中紧紧抱着想往江天夙身上爬去的小雅龙。
“人总是要长大的,要学着去面对未有未来的一切,与你来说,就像师姐所说的那样,要以一个无耻王八蛋的身份面对你的生活,而又要以一个与之相反的身份面对另一面。也是呀,无论将要面对地是什么,都应该勇敢地去迎接,而不是一味地退避到桃花源地。”
“你呢,不能让师姐失望,我不希望有一天师姐看到的依旧是那个被打击地繁盛不再的御灵宗。”
“师傅常和我们说,有时间多在人世间走走,那时候我就总会笑话师傅说的好像我们都不是人似的。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宁愿不需要有的时间,去看看师傅说的市井小道,看看书中写的山川大河吧,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像师傅所说的那样成为绝妙的离心。”
本来说不清究竟是什么表情的离心双眼异常地尖锐起来,神情变化异常的小离心然后一口一个字地说出声来。
“然、后、把、失、去、的、加、倍、讨、回、来!”
……
历朝历代以来,农民的地位都不怎么高。虽然说也有不少身穿龙袍的皇帝能够明白君民与舟水的关系,能载舟也亦能覆舟,也做出了各式各样的措施来明暗中提高农民的地位,拉拢起人数远超士商两系的人心,可真正地效果却是极其鲜微。
这其中的原因嘛,其一大多数的统治阶层仅是为了提高而去提高,包含了太多的利益和道不清说不尽的瓜葛,就如同为了读书入圣而读书的人,远不如仅为了读书而入圣的来的强烈。
其二,可以说算是上千年的市井风气哪能说变就变能那么容易变的。这农民在整个天下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太平烈帝即刘莫之父,在山河破碎的动荡之中,以武强国,先平内乱后驱敌万里,有南征北战数十载,才算稳下了这座即将崩塌的江山,稳是稳住了,但极崇尚武的弊端也是愈来愈多,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官职部署上的混乱,然后就是愿意入伍从军的人远比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农民要多得多,自然农民的地位也就更加低下了。
郭士成便是住在这座繁华都城最外围的小农民,往上数十几代也毫无意外都是农户出身,用太平王朝如今极流行的话来说,都不知道是农十几代了。
十五岁那年,郭士成向可以算是青梅竹马的少女告了一次白,可光屁股玩到大的玩伴竟是不屑地嗤笑一声,然后说了一句郭士成认为脸红的应该也是她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郭士成认识的大字不算多,所以就想出了一句从学堂外听来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还不知道着不着调。
毕竟呀,她也不是什么王侯家的千金,员外家的小姐,或许往上翻几页家谱和自己一样都是农十几代。
这一次赤裸裸的打击让郭士成下定决心要断了自家农十几代延下去的势头。去寒窗苦读,三试而跃龙门的话,家里实在没有这个资金。修道以证飞仙,自己肯定没那根骨,去了招军那里,虽说自己肯吃苦,但是人家只给了一个相貌清秀的评价就给刷下……
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就,郭士成觉得自己还是回去延续传统吧。可做人嘛,怎么能没有点野心,纵是回家种地做最不起眼的的农民,也要做出一番名声出来,狠狠地讲这一记耳光甩在那极其自负的女子脸上。
郭士成还特意查了并记下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入秋的清晨,天气是带着些刺骨的凉意,多数的农家汉字正搂着自己的婆娘做着富甲一方,然后莺莺燕燕左拥右抱的美梦。
背上柴刀的郭士成早已出现在城外的田地上,倒不是因为那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而是满心打算争一口气。
自家的地不算太近,就算踏上这条人脚走出来的小道小路也要走上一段时间,可走了不到百步的距离,就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的路边躺着个人!
清晨在这条算得上荒径的小道边躺着个人,不管是带气还是不带喘气的,都多多少少把郭士成这个小农民吓了一跳。
郭士成靠近了些,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放在这个躺在路边一脸近乎妖魅少年的鼻尖,有呼吸,郭士成这才轻吐了一口气。
看着这张脸,他突然觉得这躺在道边的少年有些眼熟的感觉,但在自己的心中有近乎苛刻地否定,因为在自己的脑海印象里,完全没有过与这张俏俊妖魅的脸有过回忆。
那是在哪里?
虽说自己住在王朝中最繁华不过的京城之中,但农民的身份一直压制他在这座城市中抬不起头,不是说他不想抬,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都忙着勾心斗角,或是与小娘子们闹春宵,谁会理睬他这么一个近乎蝼蚁的小人物。
所以郭士成所在的圈子也无非就是那些家里种着小亩地的小农民,好点的也无非就是在城中的贫民街上摆个地摊啥的,天天还要学着与那些精明细算的人打着讨价还价的勾当。真说实在的,还不如种着一亩三分地的实在。
郭士成还想起一个人来,那个说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青梅竹马,一心想嫁入王侯府中,要做个有权有势的夫人。
想到这里,郭士成不知道是怎么一番心情,竟咧了咧嘴。
既然只是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来,那就不去想这些无用的事情。不过,既然碰到了,总不能把人家继续放在路边,听那些曾经化缘的僧人讲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虽然说真不知道浮屠是啥玩意儿,但这人呀,总是要救得。
郭士成望了一眼小道前方的金色麦浪,心中嘀咕着,赶紧把这个和自己一般大的少年送到官府那里,还要赶回来收麦。
于是,很利索地把背上那把磨得发亮的柴刀别到了腰间,然后背起了这个长相俊俏的少年,走上了刚刚走来回城的路。
郭士成来的时候东边日出顶多算是光芒初露,而现在却是艳阳高高照起。
好一个风和日丽的初秋之日!
那座繁华异常的都城越来越近,从模糊近似似有若无的地步已经走到了差不多可以看清那座城的轮廓。
郭士成突然发现前方视线中扬起一股子如线般地尘烟,移动地极快,转眼间这股烟尘的制造者,一群披铠戴甲的将士胯下骑着一匹匹体膘形壮的灰马。
数息间已到了眼前,然后擦身而过。
侧身一边让路的郭士成腾出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几滴汗珠,看着那股尘烟向远方飞去,然后后方的尘烟渐渐消散,马蹄声也远去。郭士成摇了摇头,心中沉重地叹了一声自己啥时候也能这样小小的鲜衣怒马一回。
郭士成没有过多叹息,转回了身子,背好了少年,继续踏步想那座城走去。
仅仅走了不到二十步,郭士成听到身后响起了疾速而沉重的马蹄哒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