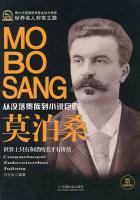在企业号上,我决心让自己成为把这个工作干得最好的人。我一直在想法让自己感觉好些——也有理由要这样做。可不管怎样努力,我总还是会受到因离开学校而造成的失败感的折磨。我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口音和有限的词汇,总使我觉得低人一等。我决心提高讲话的水平,并消除山区活的痕迹。这使我一场始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同龄人和我的任何同事,这好像并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我继续阅读,并选了一些函授课程,希望能扩大词汇量,提高学术水平。我感兴趣的一些课程中,有一门是“电子计数法入门”。我在这门课里学到了监测敌方通信的基本内容,并掌握了其他的一些尖端的科学。我已经知道了不少关于雷达的知识,因此反电子技术(ECM)是我专业知识的自然延伸。选修了这门课以后,我有资格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以掌握机密仪器的使用法。当时,海军设在弗吉尼亚的诺富克的机密仪器学校,开办为期两个月的ECM培训。企业号进人纽坡纽茨港之后,我想法让他们送我到诺富克。这是相当困难的一门课,而且这些设备都是尖端机密,你还不许与别人讨论课程中的难处。那里的每个人都是高级技师,分有机密安全防护等级。我回到企业号航空母舰后,舰上如果机密仪器出了问题,我当班的那一组中就没有谁能够帮助我。有关ECM仪器的信息是“按需要”透露出来的,我这个班上“需要”知道它的唯一的人就是我。因此,这可真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
回到企业号以后,我刚学到的新电子专业知识很快就投入实际使用了。作为海军旗舰航空母舰,我们被指派前去回收宇航员约翰·格伦。我们的情报设备不仅能找到在高空飞行的物体,它还能定位太空飞船——或者说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在舰上安装了一种叫做“高度定位器”的特殊机密仪器。当时,雷达的跟踪高度一般不超过6万英尺。可是,海军建造了一种新的机密仪器原型雷达机,它最早安装在企业号上。它可以找到10万英尺以上的空中飞行物。因为全世界都注目以待,加上美国的民族骄傲所系,海军不希望格伦的返程会出任何麻烦。要让他安全返回本舰,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必须在很高的高度监测到他的飞船。没有人能肯定这艘飞船到底会落在哪一片水域,我们只能依靠船上的高度定位器尽早锁定格伦,这样他的着陆轨迹就可以测算出来,并在海图上定位。我们希望让飞船落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这样。我们的回收直升机就可以立即着手打捞。
计划中的海中溅落的前3天,雷达出了毛病。这是非常复杂的一台设备,以前谁也没有修过。指挥官派人修复它。4位技术人员弯着腰在上面工作了四天也未见成功。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回收工作次日早晨就要开始了,可我来接夜班时,雷达还不能工作,其他一些技师已经睡觉去了。这一班当得真够难受,其他的人都在我的监督下管理其他一些设备,因此我只好自己来对付这东西。当进还没有集成电路,大部分电子设备都是通过成百上千根电缆连接起来的,各种元件散布在各个部位。这台设备的里面布满令人发毛的小表阀和用颜色编码的电线,随便哪个地方都可能出问题。
当我按系统一根根地测试电路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雷达突然开始工作起来!我报告指挥官说雷达又开始工作了,他跑去唤醒舰长,大家都高兴得不行。因为是我“修复”了设备,他们就以为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此就让我当飞船回收的操作员。这样一来,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自己身处灯光昏暗的一间屋子里,身边挤着8位或者10位官员,我在操纵着机器。雷达指示器就跟一台圆形的黑白电视一样,雷达扫瞄线与外面的天线同步扫动。进人的物体在屏幕上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光点,其高度和距离都可以测算出来。当我盯着绿荧荧的屏幕时,转动不停的扫瞄线牵动着每个人的注意力。我是个神经质的人,希望这鬼东西不要再出麻烦。我不希望格伦返回时会在我当班的时候出问题!果真,在11万英尺的高度上,一只小光点出现在屏幕上。雷达起作用了!当我在雷达上一路追踪飞船,直到落入洋面时,大家都欢呼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我海军生涯的制高点,但还不是最高点。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海军中最快乐的日子,还是参加“普通教育发展测试”或CED的时候,这次考试使我得到上张毕业证。我准备了好几个月,因此一次通过考试。这很难解释,可这次经历就像分水岭一样,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海军和GED考试让我得到了梦想的自我价值感,无知和贫穷的枷锁好像应声而碎,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展现出来。对一个来自山谷的孩子来说,这就像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产生了一种对知识的渴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自信心。看起来就好像这次通过考试给了我进行探索的门票。雷克维尔没有图书馆,萨利亚斯维尔也只有很小的一座图书馆。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现在,我对书有了很大的热情。我加入了“每月读书俱乐部”,开始读所有能拿到手的书。在我年轻的脑海里,整个世界展现出来。我读过拿破伦·希尔的《通向成功》和艾玛·莱特曼的《如何展示自己的销售技巧》。希尔的书对我有很大影响,它使我的梦想看上去极可能实现。这些书,以及我读过的其他一些书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可它们打开了我的双眼,使我看到了以前从没有想到和看到过的整个世界。
除了书以外,我的其他爱好是扑克和女人。我以前一天到晚玩扑克。我当海军每月可得约600美元的薪水,可有些月份里,我通过打牌得的收入可能会翻几番。我的名声是,我在舰上拥有最大数目的非法基金。扑克为我挣来奢华用品,也为我挣来了泡女人的费用,这可是相当惊人的一笔费用。我特别记得有天晚上,在法国靠岸时我花了一老鼻子钱。我们在康尼附近靠岸,我口袋里装满了打扑克挣来的钱,我想尽快上岸,在最好的妓院里胜过我的船友们。管无线电的水手通常是第一批上岸的人,岸上巡逻兵跟他一起上岸,他的任务是在其他船员离舰时确定岸上通信设施。我戴着岸上巡逻队的臂章,别着警棍,随他混了出去。再把这些东西脱下来放在这位同事的无线电架子上溜走了。没有谁想得出更聪明的办法。
我的康尼之夜两个月后,企业号航空母舰返程到了弗吉尼亚的诺富克港。上岸以后,我径直奔往戴依登。在全世界许多自由港的性经历,并没有打消我急于跟佩吉再续旧好的愿望。可是,接下来的事情绝不是我所盼望的——我最差的恶梦里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
到了佩吉的家后,我在门前被她母亲恩内丝汀挡住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问好就碰见她了,她大声吼叫双手乱挥着走出来。我朝大厅退出来。一定是有某些事情出差错了。她骂我完全把佩吉当成泄欲工具,然后又迫使她流产。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或者她为什么会对着我吼叫。我傻头傻脑地站在那里,想听出她在说些什么,可是她却转过身去,双脚跳着进了屋,消失在浴室里面。我走上前去,就站在屋里,呆着不知道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恩内丝汀又出来了,她手上拿着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她还在不停地骂着,突然往我脸上摔来一只罐子,里面好像是装着一只胎儿,泡在酒精中。我退回身去,忍着没有吐出来。她对我说,如果我稍微有点责任感,“这孩子可能就活下来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得到这可怕的标本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从佩吉的子宫里弄出来的,因为这似乎不太可能。我赶紧逃跑了。一肚子的火,也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