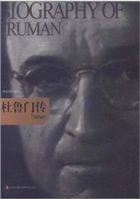雷姆斯和他的出庭律师认为,以1972年1月实行的色情淫秽物品标准来衡量,他不能被认定有任何犯罪行为。可是,帕里什并不是用这些标准起诉的,他是用最高法院在1973年6月裁定的极不同的标准进行公诉的,当时,雷姆斯完成电影角色已有一年半了。根据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在“米勒诉加利福尼亚案”中的裁定,对一部含有“补偿性社会价值”的影片也可以起诉。一般来说,对一个被告起诉,适用的法律必须是他进行犯罪活动之时适用的法律。可是,帕里什对威尔福德法官说:“该阴谋”持续到1973年最高法院对“米勒”案裁决之后,而且,只要《深喉》一片继续发行,它的影响就会持续下去。(根据这个理论,雷姆斯的犯罪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因为《深喉》一片迄今仍在放映。雷姆斯有一次问德肖维茨说。如果电影发行人使用的一些后期制作效果在该片完成几年之后造成某人的死亡,他是否犯有谋杀罪。德肖维茨教授告诉他,根据帕里什律师的理论,他可能会被认定有罪。)可是,假设雷姆斯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他也没有一点办法。他没有办法“揭露”这项罪行,因为这部电影已经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性公演,他也不可能防止该片发行和放映,因为他没有这项权利。公诉人是否想要他站出来亲手毁掉全国所有的《深喉》拷贝呢?
陪审团经过几小时听证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得出结论。他们一致认定,所有被告犯有所有被指控的罪行。因为等待被告呈交一份提请重新审判的动议,法庭裁决暂缓量刑决定。
对黄色淫秽物品来说,从来就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是否黄色淫秽全决定于观看者怎么看待。道格拉斯大法官曾讥讽地说:“就依观看者两腿根部的反应而论。”对一个人来说是黄色淫秽的物品,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艺术品,对其他人来说也可能是一场瞎胡闹。美国前任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曾承认,他无法具体写出何为黄色淫秽物品的定义,可是,他敢肯定“看见了我就知道是不是”。而其他一些大法官的看法又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每位法官又很少将黄色淫秽物品的定义写进正式法庭裁定中去。怀特大法官的书记员们称,他们的上司在决定一部电影是否属于黄色淫秽物品时,是依据片中描绘性的程度而定的。前任大法官沃伦认为描绘“正常的”性活动,不管多么露骨,都受到宪法保护,可是,对“不正常”的性活动,哪怕只是一种暗示,也会使他勃然大怒。“我女儿是否会感到受了伤害”就是他的个人标准。已故大法官雨果·布莱克认为,肮脏下流的电影绝对地应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可脏话,下流话,如“操你妈的征兵”,却不受保护。因此,大法官们对宪法原则和判例法的解释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们个人的趣味、头脑里的框框限制及各人不同出身背景的影响。而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又在很大程度上依判例而定。
是否属于黄色淫秽物品的最低限度是,当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有5位认为它是属于此类物品时。这种现实贬低了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者的身份,使大法官有权置个人趣味于国家利害之上。一些艺术工作者经常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使人想起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犹太人要修表,见一家店子外面挂着表就进去。店主奇怪地问:“修表?我不修表。我是祭司,专割包皮的。”顾客也奇怪:“专割包皮?可你为什么在店外挂着钟表呢?”店主答到:“那你要我在窗外挂什么?”
德肖维茨教授和雷姆斯决定先从新闻媒体着手工作,因为自“米勒案”以后,对黄色淫秽物品的反对呼声越来越高,法院呈一面倒的局势。他们希望通过媒体让公众和法院明白,给雷姆斯定罪是倒行逆施的违法行为。《纽约日报》首先报道了该案。文中说:“按照德肖维茨教授对《深喉》案的见解,任何人,只要参与了一部露骨描写性活动的电影、报纸、书籍、绘画或杂志的创作、制作、编辑和发行工作,就可以被押解到美国任何地方的联邦法院,以参与全国性阴谋活动的罪名提起公诉。”德肖维茨教授还通过其他媒体用通俗的语言对公众解释说,如果这类阴谋罪指控在上诉中得到维持,政府就可以在一些政治案件,如牵涉到反战积极分子的审判中开创一种危险的先例,同时,他还说:“人们必须认识到,雷姆斯被认定有罪的罪行是他‘进行’犯罪时并不存在的一种罪行。”
这种宣传鼓动作用开始生效了。美国联邦副总检察长罗伯特·博克在一个陈述中说,关于《深喉》的判例援引是错误的,因为电影的放映发生在“米勒案”之前。威尔福德法官闻说后“极为震动”,他给最高法院文书处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对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的关切,并附上一份长达60页的陈述书。但是,因为法官在未决案终审之前是不应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他的邮件未加拆封就被当作“怪信”原封退回了。不久,1976年1月,吉米·卡特上台,很快就撤换了共和党保守派的特尔利,代之以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拉里·帕里什宣布将辞职,威尔福德法官也对雷姆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决定对他的案件加以重审,几天之后,美国司法部宣布对雷姆斯撤诉。德肖维茨和雷姆斯胜诉。
但是,关于《深喉》电影,德肖维茨教授还与美国保守派的代言人之一威廉·巴克利进行过辩论。巴克利认为:“如果我们赞同德肖维茨的哲学先验模式,我们就会逐渐看到,终有一天,十五六岁的黄牙小儿会在公众场合大模大样地白日宣淫,只要付给他每小时最低工资就万事大吉。”但是,德肖维茨教授却认为:虽然黄色淫秽品“使人的感情变得粗俗不堪,可以极大地贬低妇女的人格,甚至可以使社会生活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变化”,但是,他认为,如果用这些东西作为禁止一切产生“不理想作用”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借口,从而在更大程度和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查禁,限制之门就会洪泄而开,“像《飞翔的恐惧》一类的书籍,《花花公子》、《大都会》、《销魂时光》一类的杂志,以及像《巴黎最后的探戈》这类的电影和包勃·迪兰一类的歌星——这些都是性革命中的‘先锋’——将都会遭到查禁。为了开始对男女性行为的混乱和其他‘罪过’进行有效的影响,就必须对电台、电视、歌曲、大学、新闻界、畅销书、好莱坞电影等所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检查和控制。”
《深喉》拍摄8年后,拉芙莱斯写了一本自传,题为《炼狱》,书中描述了她悲惨的经历,说她在电影中的纯洁无邪是装出来的,在这个面具之下,掩盖着一个受拉皮条的男人侮辱损害的妻子的苦闷,说她是如何在枪口威逼之下表演。她从当众表演并没有得到任何快乐,相反身心却受到极大摧残。可是,德肖维茨教授看完该传记后打电话给雷姆斯,问说琳达在电影《深喉》中扮演角色是否受丈夫逼迫,雷姆斯大笑,说她男人当时根本就不在场,说拉芙莱斯当时并非做戏,她并没有掩饰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窘境。这本书是别人替她写的,赚钱的把戏。
可是,这本书却引起了女权运动分子的高度注意,《深喉》已经成了商业性黄色淫秽物品业摧残妇女的罪恶象征。因此,德肖维茨教授代表民权卫士与女权主义分子就《深喉》展开了辩论。
事情是在1980年春天发生的,当时,哈佛大学电影协会决定在学校放映《深喉》,一些女生立刻抱怨说:“我们不应该在自己的卧室里受到这样的贬低和侮辱。”在女权主义分子的协助下,学校女生决定在放映那天设置纠察线,并利用这个机会向学生宣传黄色淫秽物品的危害性。可是,在预定上映的前几天,两名女生不满足于设置纠察线,她们告到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要求警察阻止放映《深喉》。哈佛所在地的米多尔塞克斯县检察官约翰·德罗奈不喜欢哈佛学生,他听说黄色淫秽物品脑袋就大了,立即派出一位助理到法院去,要求法官下达不准该片上映的禁令。星期五下午,电影协会的两名主席,即卡尔·斯托克和南森·黑根接到地区检察官的电话,通知他们下午两点到法院接受禁止令的听证。这两位当时都是哈佛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因此立即给德肖维茨打了电活。
德罗奈以马萨诸塞前几年通过的允许法院预先禁止已发现内容属于黄色淫秽物品的影片放映这条法规为理由,要求法院下达禁止令。可是,美国民权联盟反对这项立法,认为它是违宪的,因此,德肖维茨教授以该地民权联盟的名义在法庭上充当代理,反对禁止令。阿尔贝蒂法官准备亲自看一遍《深喉》,以决定该片是否为黄色淫秽物品。看了约40分钟后,该法官突然下令关掉录像机,并召出庭全体人员回庭。他决定,虽说他认为这部影片中的男女都是堕落的,可是,根据当地法律,该片还构不成黄色淫秽,因而决定不对预定上映的《深喉》发出禁止令。
当晚,德肖维茨教授对在场学生发表演说,他说,他愿意参加纠察队,保护抗议放映电影的人的权利,可是,他又说:“援引法律来逮捕,起诉和检查控制,这是一件极严肃的事情。正像尼克松试图对‘五角大楼文件’进行检查控制一样。女权主义的法西斯分子并不比任何一种法西斯分子更好。”可是,电影放映完毕后,德罗奈派的两名侦探上前逮捕了斯托克和黑根,没收了影片,查抄了电影协会的门票收入。根据当地法律,这两名学生最高可判5年徒刑。
几天后,民权联盟向波士顿联邦法院呈递了一份民权诉讼请求,控告德罗奈侵犯了斯托克和黑根的权利。这纸原告诉讼使地区检察官处于承担取证任务的位置,因为一般来说,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取证这一程序,因而无法强制德罗奈在刑事诉讼中回答辩护方律师提取公诉方在起誓所言皆实后的证言。但是,取证可以作为联邦民权诉讼中的一部分。辩护律师经过巧妙的提问后,迫使德罗奈当堂承认:如果让他在提供影片的人和放电影的学生之间选择起诉方的话,“毫无疑问,我将起诉提供影片的人。”律师问,如果被告提供《深喉》影片供片人的名字,他是否会撤诉。德罗奈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发誓声明他宁愿向影片提供者起诉也不愿起诉学生。他只好同意。该片提供者为“S·R·O娱乐公司”,是纽约一家规模很大的发行公司,它发行一份目录,上面有向全美各大学出租的影片名单,还有它在纽约的地址。所有指控罪名撤消了,检察官也没有起诉纽约的公司。当地民权组织继而撤消了对德罗奈的起诉。
可是,《深喉》引发的有关色情物品的争论却还在持续进行中,特别是与一些女权主义者的争论。德肖维茨教授说,人民对色情淫秽物品有选择的自由。他对这些女权运动者说,伊朗刚刚通过了一项禁止色情淫秽物品的法律,同时也规定所有妇女必须把脸部遮住。高唱道德经的多数派正努力荡涤电视节目中的污泥浊水,符合这个标准的女权主义节目也不例外。那个曾经企图禁映《深喉》的检察官成功地制止了一部优美的关于妇女同性恋的影片上映,他的根据就是那条反色情淫秽物品法律。他说,“反对黄色下流物品法律的漫长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法律经常被用来反对在政治上或生活方式上持异端思想和走极端的人。”而那位著名女权主义者的著作可能就是那些道学先生们首先想要查禁的书。他还对一位要求禁止亵渎上帝的书,只需读一读《圣经》的牧师说,《圣经》这本书本身就是世界历史上受查禁最多的一本书。
德肖维茨教授认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希望对他不喜欢的东西进行检查控制。但是,没有一种客观地衡量什么是有害什么是无害的程度标准。一个政府是无法对纷纭复杂的种种观念作出一个绝对的答复的,如果政府准备禁止任何一种现象,它就必须一视同仁地禁止所有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东西。如果不能禁止其中一种,政府就不应该禁止其中任何一种。因此,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所以保护表达自由,不许国会立法限制言论和信仰自由,是因为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也是唯一明智和可行的选择。一个社会如果要相安无事,要么大家都对自己感到有害的东西作些容忍和让步,从而换取一个多样化的社会,要么只允许没有任何人感到有害的东西存在(这也是不可能的),从而生存在一个单调和倒退的社会中。历史是前进的,人类从物质和思想的禁锢中超脱出来,随着生活实践产生不断的飞跃,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多样化、富于更多选择的光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