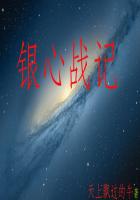格兰特曼转身,从原告桌上拿起一本《风尘女郎》,向我走来说:“我会站在你身边,你可以跟我一起读。”他拿的是1976年6月号的《风尘女郎》。他大声宣读:“(《风尘女郎》)将(一如既往地)报告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坦诚、实事求是。不管这个人是一个不出名的公民,还是一个公众人物,如果他是个王八蛋,一个粪堆,或者是一个垃圾袋,你在《风尘女郎》里看到的也必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又停了一会儿。
“你有什么问题?”我问。
“如果你认为某个人是王八蛋,是粪堆,或者是一只垃圾袋,你在杂志里就会这样说——是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我拒绝落入格兰特曼的圈套。“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王八蛋,因为每个人也的确有个蛋,”我说,“如果某些东西不能给它一个定义,这就谈不上诽谤。你谈论的是一种编辑方针。它可能格调不高,可是我之所以被起诉,到底是因为我的格调不高,还是因为诽谤?”
格兰特曼不理会我的答复,接着问道:“弗林特先生,你是否说过‘自由表达是绝对的’?”
“是的,”我答到,“只要没有人受到伤害。”“而绝对的意思是指你可以说你想说的任何东西吗?”
“是的,”我答道,“我认为你有权说你想说的任何话。”
“不管一个人的感情是否会受影响?”
“啊!”我说,“你是在谈论格调的问题。我想说清楚的事情是,没有人应该因为他所说的话而遭到囚禁!如果你不喜欢电视里说的一些话,关掉电视就行了。如果你不喜欢《风尘女郎》里面的东西,不看就得了。”
格兰特曼和我唇枪舌剑干了两个多小时。阿兰提出了异议,格兰特曼拿出了好几篇文章,还有《风尘女郎》里面说的一些话,但都与本案无关。所有这些材料都是想让陪审团产生偏见,并试图使他们相信,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坏,最粗野的人。这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我经常是很坏,而且很粗野。可是,那与我们此刻在这里争论的东西有何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这是一种个人推论庭审策略,对处于考验之中的第一修正案议题的理解毫无关系。
我的证词答辩结束后,证人到堂,双方也做出了结论性的辩解。阿兰·伊萨克曼重申了我方立场:康巴里广告是个玩笑,是一种滑稽,永远也不可当真。“对于像感情伤害这样一些琐碎的事情作出损害赔偿,”他说,“这是非常可笑的。”格兰特曼的结论性辩词意在于陪审员中制造一种赫然,感觉认定我是个粗野可鄙的家伙。他对陪审团这样说教,而他们的责任是要给我这种极端无礼的行为划一个句号。他开始听上去像西蒙·莱斯了。
“很显然,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盯着容恩诺克,”他说,“而诸位也得拿出一个意见来。你们在这个法庭上所说的话将传遍全国,深入祖国各地。全国人民都看着,这个国家希望知道宪法站在谁的一边。你们会让混乱和无政府主义横行霸道吗?你们会使美国退回到‘猿猴纪’吗?”
格兰特曼表演完毕之后,特克法官对陪审团作了最后的讲解,仔细解释了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条款。他禁止陪审团在未经他准许的情况下,就认为康巴里广告构成了对法尔威尔的名字和肖像权有“商业目的”的滥用。我们并没有打算销售康巴里酒,因此他裁定,这项罪名是没有基础的。他们面临的两个问题,他解释道,涉及到诽谤和故意造成感情压力的问题。诽谤罪的实质,他说,取决于该广告是否能够“被合理地理解为描述了有关原告的实际事实,或者原告参与的一些实际事件”。如果陪审团裁定答案为“是”,则他们必须考虑第二个要点:我刊登该广告是否出自“实际的恶意”?“实际的恶意”的定义,他解释为“知道是虚假的,或者不顾后果地忽视实际情况”。他们必须决定,他说,我是否采取了有意对法尔威尔牧师进行感情伤害的行为;另外,如果采取了这种故意的行为,还得决定这份广告是否冒犯了普遍接受的风化标准。
陪审团的审议时间并不长。阿兰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判决下来了,说他会在法院见我。我的助手通过木门把我推进法庭,安置在被告席后面的地方。特克法官进来了,不一会儿,陪审团也进来了。书记员宣读了判决。关于诽谤的诉讼理由:赞成被告方。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该广告为实际发生的事情。关于感情伤害方面:赞成原告。该广告是否冒犯了普遍接受的风化标准?是的。法尔威尔赢得了部分胜利。陪审团裁决给他10万美元以补偿损害,10万美元用于罚款。尽管有罚款,我还是极感高兴。我一直很担心结果,我担心陪审团会让我做不成生意了。比较起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说,这笔罚款真可谓九牛一毛。我掂量了各种选择,如果上诉,我要花的钱可能比这笔罚款更多,我可能会输。不过赌注很大,宪法原则已经放在赌桌上了,我们立即向美国上诉庭——第四巡回庭提出了上诉。
由上诉庭的3位法官组成的法官组于1986年8月5日作出了他们的决定。这是颗炸弹。这个小组拒绝推翻法尔威尔裁决。在较大案件中,法庭第一次维持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仅依据造成情绪伤害的意图就可以判定责任,哪怕发表的材料即不是诽谤,也不是对隐私权的侵害。酝酿其裁决时,该法庭曾考虑过一个极端重要的案例,该案例创下了新判例: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特克法官对陪审团讲解法规细则的依据)。
(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是最高法院1964年作出的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案。最高法院驳回了对《纽约时报》上登载的一则攻击南方种族歧视活动和警察暴力活动的付费广告的诽谤判决。阿拉巴马的一个陪审团曾判决,因为广告中包含的所谓的诽谤,给蒙特哥马利的一位警官L·B·苏利文赔款50万美元。最高法院法庭裁定,公民有权说不利于政府及其官员的话,而不必担心会受到“危及治安”诽谤罪——诽谤政府罪的起诉)
新闻界一向以苏利文裁决为神圣文书,全国的出版人突然间都紧张起来。法庭是否抛弃了苏利文裁决?我们要求再行审理——这次是第四巡回庭的全体法官(这种审理叫做en banc,即全体出庭法官受审)。阿兰起草了一份申请,要求进行EN BANC审理。第网巡回庭的一位法官J·哈维·威尔金森第三看过我们的申请后,起草了一篇口才极好的吁请信,对同行法官们说应该给予EN BANC审理。威尔金森是第四巡回庭无可争议的最优秀的学者,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弗吉尼亚人学法学院。他曾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教授,著有多本著作。威尔金森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可是,这个巡回庭以6票对5票否决了重新审理。我们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
美国最高法院每年接到的审诉案数以千计,能够接受复审就算是一件稀罕事。每年平均约有150件案件得到全面听讯,而只有最为紧急和最重要的一些案件才予以考虑。
递交到最高法院申诉的案件,大多数都是要求得到certiorari。律师们都喜欢使用拉丁词。certiorari来自一个表示“被告知”的拉丁词。如果该法庭批准该申诉,它会同意对某个特殊案件的事实进行复审——“使法庭了解(事实)。”
阿兰提出申诉,要求该法庭复审,要求最高法院行使其处决权,并复审本案。当然,格兰特曼也反戈一击,要最高法院否决复审,维持第四巡回法庭的原判。
当法院接到申诉时,局外人,即与原告无关的人,都可以提出叫做amicus curiaer的建议性的简单说明,即“法庭之友”简单说明。法尔威尔最初起诉时,没有人愿意站在我这一边提出“法庭之友”说明,原来的诉讼和后来的上诉中都没有。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主流新闻缺乏道德勇气,而且担心法官只会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从而确立一个新的判例。他们都认为我是个十分不得体的人,不值得一交。可是,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提议下——没有来自组织以外的任何支持——我的律师获胜了,1987年3月20日,最高法院批准了我的复审要求,并决定复审第四巡回庭的裁定。
突然间,我有了很多朋友——一些勉强的朋友。既然赌注如此之高,议题如此清晰,主流媒体开始改变观点了。如果第四巡回庭的意见维持不变,则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通过30多年的法庭裁决才得以形成的、能够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第一个胆敢将其赌注押在我这边的媒体组织是《里奇蒙德时代电讯报》及其姊妹出版物《里奇蒙德新闻导报》。可是,其他一些单位也接踵而至。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有纽约时报公司(洛杉矶)、时代镜报公司、弗吉尼亚新闻协会、美国报业协会、杂志出版人协会、HBO、ACLU、美国作家联盟、美国杂志漫画家协会和政治讽刺家马克·卢梭。这整个儿就是一本美国出版业的名册。
最高法院将口头辩论的日期定在1987年12月2日早晨。只有8位法官听诉。刘易斯·包威尔法官春天起就辞职了,他的继任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里根总统提名罗伯特·博克继任,可是,经过争执激烈的听证会后,国会拒绝确认他的继任。里根的第二选择是道格拉斯·金斯伯格,可是,金斯伯格的提名在一片火焰中完蛋了,因为有人披露,他在哈佛当教授期间曾吸过大麻。里根的第三选择,安东尼·肯尼迪得到确认,可当时尚没有落座。其他法官中有好几位都是一些年届70或80的老家伙。最高法院院长威廉·任奎斯特是1986年9月接替厄尔·沃伦院长走马上任的。他在第一修正案的涉案事件中,对新闻界几乎总是投反对票——次数已达20多次。任奎斯特唯一可以补偿一些的品格就是,我们认为,他因为有很好的幽默感而名声卓著。我们不知道他或者其他任何法官会投什么票。根据阿兰对最高法院权威的综述,任奎斯特和至少其他5位法官都偏向于法尔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