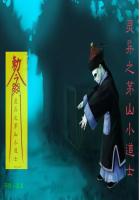伯母终于可以退居二线,准备去省城某剧场做一个小型的告别演出。
一众亲戚开车去为她捧场,在后台看见演出服:“哗,这么亮!”
“这么闪!”
“这么细的腰!”
伯母一个近六十岁的人,打上厚粉,抹了胭脂,甩开长发,嘴角轻轻一挑,眼角眉梢带笑,立刻脱胎换骨,作二八佳丽形貌。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她平日里勒紧裤腰吃饭,坚持练功,才保全了一副好身段。外人谁晓得?
只有木辰撇撇嘴:“啧啧,至少用了三斤****。”一面说一面摇头,转一个圈子便出去。还顺道拉上我:“走走走。”
观众席早挤得满满当当。她带的学生,认识的朋友,多年的同事……都伸长了脖子在等。
我们占了最好的席位,正对台中央。
母亲也抱着牧牧坐过来,趁演出没开始,低声说:“林兆最近不约你?”
我微怔,半晌,“他大概在忙。”
“也是。”她安心靠上椅背,“他们家的产业也很大。”
灯光渐黯,开场音乐悠悠响起。木辰翘着二郎腿,提醒我:“要开始了。”
幕布缓缓拉开。
伯母直直站立,背对观众,一袭银白长裙,长发如瀑。台下顿时掌声如雷。
她随音乐慢慢扭身回眸,手似流波微动,身体之柔韧令人惊叹。
所有人看得如痴如醉。她不枉舞蹈家盛名。
我不经意看到木辰掩嘴打呵欠。
“这是你妈的告别演出。”我压低声音,“好好看。”
他微微一笑,“从小到大,我看的还少?她在家里有练功房,整天没事就对着镜子摆姿势。”
我不再说话。
天下总有儿女对父母不屑一顾。拿亲情当理所当然。
大伯却是看得入神。
他当年是伯母身后一票疯狂追求者之一。不惜场场追随,大把撒金。待得抢到美人归,结婚多年,狂热依旧。
回去时后台被花海淹没,每人车上都分得一束花。
牧牧一路把花抱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左右拨弄。我吩咐她:“回去以后拿花瓶养起来,还可以放几天。”
母亲感慨:“你伯母才比我小了两岁,看起来真年轻。”
“妈,你也不差。”我说,“是你自己不肯化妆。”
她笑笑:“我化了妆也没她漂亮。”
到家时天色已黑。我匆匆洗菜淘米。
母亲挡开我:“我来。你去陪牧牧看电视。”
我走到客厅,电视里哗哗作响,牧牧已经蜷在沙发里睡着,似一团小猫。
孩子多么幸福,说睡就睡。
我关掉电视,拿走她手边花束,给她盖上薄毯,调暗灯光,蹑手蹑脚回到厨房。母亲正往锅里加水:“怎么了?”
“可能白天坐车太久,已经睡了。”
“那等晚饭做好再叫她起来。”母亲看我,“你要不要也去躺一躺?”
“我哪有那么娇贵。”
我将花拆去包装,放进花瓶,往里面灌一些冷水,丢半片阿司匹林进去,端去饭厅。
母亲剖了两条鱼,将脏物装袋打结,命我出去丢掉。
我提着垃圾袋出门,走出不远,猛觉前面路灯下有人影,抬头一看,正对上林徐晶亮亮的眸子,整个人顿时如被点穴,僵住不动。
“木小姐。”
他轻轻叫我:“我没有打你的电话……就送LUNA来了。”
我顺他手上看去,LUNA就牵在他身边,眯着眼睛看我。
我许久才能开口:“谢谢你。”
他向我走来。
LUNA凑到我脚边,用自己身上白毛轻轻磨蹭我脚背。
“……木小姐?”
这脸,这眉毛与眼睛,这嘴唇,太像林兆。
我仰头看他:“你……走过来的?”
“噢,还好。”他轻松笑笑,“当作是遛狗,也不觉得远。”
他将LUNA的牵引绳交到我手里。
我听见自己声音:“这段时间麻烦你了。”脚不自觉向前走。
他走在我身侧:“要出门?”
“不,去丢垃圾。”
我觉得自己四肢发抖,一个不慎便会跌下去。偏偏走得分外平稳。
一直走到斜坡下面。“那我走了。”他冲我笑,“再见。”
“再见。”
我呆呆站了许久,想起来去看时,他的背影已经不见。
我慢腾腾回到家里,牧牧已经被母亲叫醒,在餐桌上摆筷子。
“妈咪!”
我脱力靠在门口。LUNA迫不及待冲进客厅,直奔饭厅。
牧牧又惊又喜:“LUNA!”丢下筷子去抱它。
母亲闻声从厨房里出来,看满地泥爪印迹,不由叹气:“阿晓,快拿拖把来。”
她处理完地板,又忙不迭牵LUNA去洗澡,等终于可以坐下吃饭,连汤也凉透了。
我替她重热饭菜。
“LUNA不是被你留在那边吗?”她随口问,“谁帮你送回来的?”
“是林徐。”
“看来他知道他哥哥在和你谈恋爱。”
“他以前就经常给我们帮忙。”我说,“未必是因为林兆。”
蓦然想起来:是了,也许上次发生的事情,他并不知道。
我勉强放下心中重担。
夜里却梦见一场婚礼。我茫茫然分开人群走进去,穿着白纱的新娘正在抛花,不偏不倚直飞到我头顶上。还不待我伸出手去,花已经被别人抢走——我回头一看,真真要命:林兆穿一身新郎衣服,手里捧花,看着我。
他说:“木晓,我们……”
我吓出一身冷汗。
醒来后才想起那天在停车场,已经没有别的车在走,安安静静,林兆把手放在我手上,微微捏紧:“你做林太太。”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林兆已经俯身过来,热气一点点拂在我脸上。
他的身上有一种男性的清冽气息。压迫感明显。
我已看清他睫毛,电光火石间大脑一片空白,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巴掌重重扇了过去。
我不由嘲笑自己:木晓,你不是以为自己并不怕井绳的么?
现在哪里还有脸面见人。能躲且躲才好。
我神思不定。生怕某个时刻手机响起,屏幕上便是林兆姓名。
隔日帮母亲一一拆了窗帘去洗。大桶大桶的水倒进去,洒上洗衣粉,任它上下翻滚。在洗衣机旁一守就是半天。
总算明白母亲为何洁癖愈发严重。人在心绪纷杂的时候,倘用单调低级的力气活来转移,可以得到片刻安宁。
窗帘过水便变重。我费力将它们一一抬到晾衣绳上,还要留心是否有边角垂到地上,以防前功尽弃。做得腰酸背痛。
从阳台下来,我揉着肩膀去洗澡。把热水调到最高一档,放满一缸,整个人躺下去。
热热的水波撩动我面部,将我与俗世隔绝。
我浑身放松。
忽闻牧牧敲门:“妈咪,外婆问你要不要吃酒酿汤圆。”
我只好从水里钻出来:“别做太多。”
不过隔绝了五秒钟。
我草草洗完出去。母亲将酒酿汤圆递到桌上:“刚才有你电话。”
我的心立刻漏跳一拍。
“是谁打来的?”
“陌生号码,我不敢接。”她努一努嘴,“你去看看。”
现在已经是九点多。应该不会是林兆。
我去看未接来电:这号码我从没见过。
“也许是骚扰电话。”
“好像不是。”她说,“响了两次。”
“熟人的号码我都存着。”
我只好坐下。
假如真是相识的人有事找我,应该还会打第三次。
谁知它再也没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