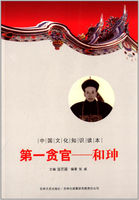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我想是我们的退场的时候了,华生。”福尔摩斯低声说道,“你搀着太过忠实的多罗雷思的这只手,我搀着那只。好了,走。”他关上门时又加了一句,“我想剩下的就由他们自己解决好了。”
关于这个案子,我只有最后一点要补充,那就是福尔摩斯给本篇开头的那封来信的答复。全文如下:
贝克街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吸血鬼事宜
尊敬的先生:
接到您十九日的来信之后,我已调查了贵公司顾客——敏兴大街,弗格森—米尔黑德茶业经销公司的罗伯特·弗格森所提的案件,事情已圆满地结束。对贵公司的推荐特此致谢。
歇洛克·福尔摩斯
(陶玢 译)
三个同姓人
这件事也许是喜剧,也许是悲剧。一个人因此精神失了常,我因此负了伤,另一个人因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当然这里面又还有些喜剧的味道。行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判断吧。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件事正是发生在福尔摩斯拒绝爵士封号的那个月里。他要被授爵是因为立了功,这功劳也许将来有一天我还会写出来。封爵的事我只是顺便提及,因为我是合作者,应该谨慎从事,避免一切冒失的举动。然而这件事却让我记住了上述的日子。那是一九○二年六月底,就在南非战争结束后不久。福尔摩斯像通常一样在床上一连躺了几天,这是他常有的行为。但那一天早晨他却从床上起来了,手里提着一份大张的文件,严峻的灰眼睛里有一抹逗趣的笑意。
“华生老兄,现在有个好机会能让你发财。”他说道。“加里德布这个姓你听说过吗?”
我说没听说过。
“喏,要是你抓住一个加里德布,就能赚一笔钱。”
“此话怎讲?”
“说来那可话长了——而且有点稀奇古怪。在所有我们研究过的复杂的人类问题里头,碰到这么新鲜的事还是第一遭呢。这个家伙马上就会来接受我们的盘问了,所以现在我们暂不谈他,不过我们却要查查这个姓氏。”
电话簿就放在我旁边的桌上。我不抱希望地打开翻找着。但使我诧异的是还真有这么个古怪的姓氏排在它该排的位置上。我得胜般地叫了一声。
“在这!福尔摩斯,就在这儿!”
福尔摩斯从我手里接过簿子。
“加里德布,”他念道,“西区小赖德街 136 号。抱歉,华生,要让你失望了,这是写信者本人。咱们得再找一个加里德布。”
说话间,赫德森太太用托盘托着一张名片走了进来,我拿起看了一眼。
“有了,在这儿!”我惊奇地喊道,“这是一个不同名字的首字母。约翰·加里德布,律师,美国堪萨斯州穆尔维尔。”
福尔摩斯看看名片,笑了。“我看你还得再找一个才行,华生,”他说道,“这位也已是计划内的,不过我倒没想到他今天早上会来。但无论如何,他能告诉我们许多我想知道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律师约翰·加里德布先生就进来了。他矮而壮,一张圆圆的脸修得干净整洁,气色很爽,正如许多美国事务家所具有的特征那样。他整个看起来是丰满和相当孩子气的,所以就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一个笑容可掬的青年。惹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我很少见到过一双如此广泛地反映内心思想活动的眼睛,那么亮,那么机警,那么迅速地反映出任何细小的思想变化。他操美国口音,但并不怪。
“哪位是福尔摩斯先生?”他来回打量我们两个,“啊,不错,你的照片跟你本人确实很像,福尔摩斯先生,恕我冒昧,据我了解,你已收到了我的同姓者写来的信,是吧?”
“请坐下来谈,”福尔摩斯说,“我觉得有很多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下。”
他拿起那叠书写纸,“这份文件中提到的约翰·加里德布就是你喽。但你来英国已有一段时间了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
我在他那富于表情的眼中似乎看到了忽然的狐疑。
“你的服饰是英国风格的。”
加里德布勉强笑了笑,“我拜读过你侦探的技巧,福尔摩斯先生,但我从没想到我也会成为你的研究对象。你是怎样看出来的呢?”
“你衣服的肩式,你的靴尖部——谁会看不出呢?”
“噢,我倒是没想到自己是一个这么明显的英国人形象。好些日子以前我因业务关系来了英国。所以,正如你说的,现在装束几乎都伦敦化了。不过,我想你的时间一定很宝贵吧,我们见面并不是为了讨论鞋袜的式样,谈谈你手里拿着的文件好吗?”
福尔摩斯在某方面惹恼了来访者,他那孩子气的脸变得不那么随和了。
“别急,别急,加里德布先生!”我的朋友安慰他说,“华生医生可以证明,我的这些小插曲往往是颇能解决问题的。不过,内森·加里德布先生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呢?”
“我不明白究竟他把你扯进来干什么!”客人突然光火了,“这事与你有何关系?本来是两个绅士之间的一点事情,而其中一个偏偏要找来一个侦探!今早我见到他,他告诉我他干的这件蠢事,所以我到这儿来了。真倒霉!”
“这并不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加里德布先生。这纯粹是他太热情地想要达到你的目的——依我看来,这个目的于你两人同样关系重大。他知道我能多种途径获取信息。因此,很自然地他找了我。
客人的怒容这才渐渐散开了。
“既是这样,倒也没什么,”他说,“今早我一见他,他就告诉我找了侦探,我马上要了你的地址便赶了来。我并不想警察介入我们的私事,但如果你乐意帮我们找到这个有用的人,那倒没啥坏处。”
“唔,正是这样,”福尔摩斯说,“既然你来了,我们最好是能听你亲口谈谈情况。我这位朋友对详情还一无所知。”
加里德布先生用不太友好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 番。
“他有必要知道吗?”他问道。
“我们经常合作。”
“好吧,也没必要保密。我尽可能简短地把基本情况告诉你。如果你是堪萨斯人,你当然会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加里德布是什么人。他靠房地产起家,后来又在芝加哥从事小麦交易发了财,他又在道奇堡以西沿着堪萨斯河买下了足有你们一 个县那么大一片土地,包括牧场、林场、耕地、矿区,每种地产都给他带来大把的钞票。
“他没有亲属后代——至少我没听说过有。而他对自己的稀有姓氏却颇引以为豪。这一缘故使得他和我相识。我在托皮卡从事法律工作,有一天这老头突然找上门来。因为认识了我这个同姓人,他乐不可支。他有一种怪癖,他决心认真地找一找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加里德布了。
“‘再给我找一个加里德布!’他说。我告诉他,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整天满世界乱跑找加里德布们。‘不管怎么说,’他说,‘如果事情按照我布置的发展,你会去找的。’我只当他是说笑话,谁知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他的话是认真的。
“因为他说这话不到一年就死了,他留下一份遗嘱。这真是堪萨斯州有史以来最古怪的一份遗嘱了。他把财产平分为三份,我得其中一份,条件是我必须再找两个姓加里德布的人分享那另外二份遗产。每份遗产不多不少正好五百万美元,但非要我们三个人一起来,不然不得动用分文。
“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哪儿找?我索性把法律业务丢到一边,出发去找加里德布们。美国没一个。我跑遍了美国,先生,用密梳把美国细细梳了遍,但一个加里德布也没找到。后来我决定到英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来碰碰运气,在伦敦电话簿上真有这个姓氏。两天前我找到内森,告诉了他整个情况。
但他也是孤家寡人,和我一样,有几个女亲属,但没有男的。遗嘱里规定是三个成年男子,所以,你看,还缺一个,要是你能帮我们再找出一个来,我们当即酬谢。”
“你瞧,华生,”福尔摩斯微笑道,“我说过这事很稀奇古怪,是不是啊!不过,先生,我认为在报上登启事是最简便的办法。
“早登过了,无人应征。”
“哎呀!这可真是古怪的小问题呀。好吧,有空我会为你留意一下。对了,你是托皮卡人倒真凑巧,我以前有个书信朋友,就是已故的莱桑德·斯塔尔博士,一八九○年他曾任托皮卡市长。”
“老斯塔尔博士么!”客人说道,“他的名字至今受人敬重。好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看我们能做的就是向你报告事情进展的情况。这一两天我会给你信的。”说完,这位美国人鞠了一躬,走了。
福尔摩斯已经点燃烟斗,脸上含着古怪的笑坐了好一会儿。
“怎么样?”我终于问他了。
“我觉得奇怪,华生,我很奇怪!”
“奇怪什么?”
“我一直觉得奇怪,”福尔摩斯拿掉烟斗说,“这个人对咱们编了这么一大堆谎话究竟目的何在。我都差点脱口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单刀直入最奏效——但我还是决定让他自以为骗过了我们。独自一人跑来,身上穿着穿了一年以上的磨破了肘的英国上衣和膝部变形的英国裤子,而据信上和他本人口述都说自己是一个刚到英国不久的美国人。他根本没在寻人栏登过什么启事,你知道我是从不放过那一栏的任何东西的。那个地方是我喜欢的惊弓之鸟的隐蔽所,我不会忽略这样的一只野公鸡的。我也从来不认识什么托皮卡市的斯塔尔博士。他处处露马脚。我看他倒真是个美国佬,只不过在伦敦多年口音未改而已。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假装找加里德布又是出于什么动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如果他是个恶棍,那就是个阴险复杂、诡计多端的家伙。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另一位加里德布是不是也是假的?给他挂个电话,华生。”
我摇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颤音:
“不错,不错,我就是内森·加里德布。福尔摩斯先生在吗?我想跟他说几句。”
福尔摩斯接过电话,我听到他那跟往常一样断断续续的对话。
“对,他来过。我知道你不认识他……多久了?……才两天哪!……当然,这件事很吸引人。今晚你在家吗?你的同姓人今晚不会在你家吧?……很好,那我们就来,我希望我们不当着他的面谈一谈。……华生医生跟我一道来……从你信上知道你是深居简出的……好,我们六点左右到。不用对美国律师讲……好,再见。”
这是个可爱的晚春黄昏。连狭窄的赖德街在落日斜辉中也呈现出黄金般动人的色泽。这条街只是艾奇沃路的一条支巷,离开那个在我们记忆中不祥之地泰伯恩只有一箭之遥。我们走访的这座特别的房子是旧式宽敞的早期乔治式建筑,正面是平砖墙,只有第一层楼有两座大的凸窗。我们的主顾就住在一层,两座大凸窗就是他平时活动的那间大屋的正面。经过时,福尔摩斯指了指刻有那个怪姓氏的小铜牌。
“这牌子钉在这上面已有些年头了,”他指着褪色的牌子说道,“至少这是他的真姓氏,这点值得注意。”
房子有一个共用楼梯,门厅里标着一些住户的姓名,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私人居室。这不是一座配套的居民楼,而是生活无规律的单身汉的住所。
是我们的主顾自己来开的门,他抱歉说女工四点下班走了。内森·加里德布先生身材又高又瘦、肌肉松弛、肩背微驼,秃顶,年纪六十出头。他的脸色苍白如死人,皮肤灰暗无血色,正是一个从不搞运动的人的样子。戴着大圆眼镜,蓄着山羊胡子,再加上肩背又微驼,使他显出窥探而好奇表情。但他给人的总印象是和蔼的,虽说有点古怪。
屋子也是一样的古怪,看起来像个小博物馆。房间广且深,四周都放满了地质学和解剖学标本的各式柜橱。屋门两边排放着装蝴蝶和蛾子的箱匣。
屋子中间一张大桌上堆满了零七碎八的物件,一台铜制大型显微镜高高地矗立中央。环顾四周,这个人的兴趣如此广泛令我吃惊。这里堆一箱古钱币,那里放一橱古石器。大桌子的后边是一大橱的古化石,上边陈列着一排石膏头骨,刻着“尼安德特人”①、“海德堡人”②、“克罗玛农人”③等字样。显然这位先生爱好多种学科。这时他站在我们面前,右手拿着一块小羊皮在擦一枚古钱。
“锡拉丘兹古币——属于全盛时期,”他举起古钱说道,“晚期就大大退化了。我认为它们是其全盛时期的最好古币,虽然有些人更推崇亚历山大钱。这里有把椅子,福尔摩斯先生。让我先来把这些骨头挪开。这位先生——对,华生医生——麻烦你移开那个日本花瓶。你瞧,我有这么多的小嗜好。
我的医生老说我怎么从不出去活动,但你看,房子里有这么多吸引我的东西,我干嘛要出去呢?不用说,为一个柜橱的内容搞个象样的目录也得花上我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福尔摩斯好奇地四面环顾。
“你说你从来都不出去是吧?”他问道。
“除了有时乘车去撒斯比商店或克利斯蒂商店外,我极少出门。我身体不好,而我的研究又很费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福尔摩斯先生,当我听说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运时,我是多么惊人——令人兴奋但是骇人所闻——的意外啊。只要再有一个加里德布就妥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我有一个兄弟,但已去世,女性亲属又不符条件。但世界上总还会有其它姓加里德布的人。
我听说你专门处理奇异案件,所以把你请了来。当然那位美国先生也说不错,①最早的人类。被认为是史前人类的代表。生活在 40000—115000 年前。1864 年首次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发现其化石。——编注。
②与猿人同时代的人种。名称根据 1907 年在德国海德堡附近出土的下颌骨化石所定。属于欧洲直立人。——编注。
③史前人类。1868 年在法国西南部多涅省西德塔雅克附近的克罗玛农山洞中发现骸骨。最早出现在 35000年前的欧洲。——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