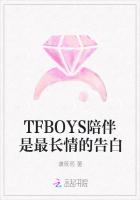白幻辰,我的主治医生,仁德医院的第一把刀。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墙边的办公桌前埋头写着什么,看到我他明显有点意外:“对不起,这里不是治疗区,我想你找错地方了。”
“你好,白大夫,多谢你前几天对我的救治,我是来感谢您的,同时因为其他大夫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的伤,所以希望您给我一些建议。”我自报家门,并抬起我的左臂示意。
“哦。”白大夫终于想起来了我,“抱歉,我把这个事忘了,好吧,你看我这里。我的意思是要不要去治疗区。”
“没关系,是我打扰您,以您方便吧,如果不麻烦的话,这里也可以。”我打量着这个房间。关于白大夫的这个房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作为记者天生敏锐的嗅觉和易于让人亲近的沟通手法,并不难让我得到下面的故事。
白大夫刚进这家医院的时候,以精湛的医术和美艳的外表几乎征服了医院里的所有人,可以应付甚至是独立应付任何手术,从心脑血管到外观整容,就没有他做不了的手术,且创面小,患者恢复快。身材长相又好,个头182CM,头发从来都整理的丝丝不乱,脸虽然白些,却并不奶油气,高高地鼻梁,微微下陷的眼窝似乎有着西方的血统,棱角分明的脸型,略带忧郁的眼神让医院里的小护士们几近疯狂。这样的大夫无论在哪都是备受瞩目的,但是他却甘愿呆在这个市属三甲的小医院里,让院长很是感动。毫无疑问,这间医院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但是可惜不是所有。后来出于对白幻辰成绩的肯定,和表示对优秀大夫的奖赏,院方分配给他一间带套间的高级诊室。
套间的外间是诊治间,用于给患者作初步的检查和诊治,有配套的护士和一些简单的设备;里间是一个宽敞的办公室,用于休息和处理一般公务。这是刚离休、隐退的沈老教授的办公室加诊察室,沈教授也医界德高望重,从学校退休后接受院长的邀请来坐镇仁德医院,在正式隐退前的几年,一天他只看不到10个病人,但价格很高。沈教授有一个学生,何涛。在白幻辰来医院之前被誉为医院的未来之星,可是这种情况随着白幻辰的到来而改变,于是,当他开始针对他,搞得医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两人不和,而何涛当时的诊室就是我现在身处的这个房间。
而白大夫则处处忍让,不与何涛计较,还主动向院方提出和何涛交换办公室。院方也是为了息事宁人,同意白幻辰和何涛互换办公室,于是这里变成了白幻辰的办公室。白大夫因此得到了全院的尊重,何涛成了笑话,大家都疏远他,他也变得越来越沉默,我行我素。
屋子不大,摆设也很简单,一张方桌一个书架,以前还做诊室的时候还有几张患者和护士的椅子,一个长桌放一些简单的医疗设备,现在就只做办公室用了,这些东西也没了用处,整齐的摆放在一边。
白大夫认真的检查了我的断臂,冲我笑笑:“没事了,你的胳膊好了,这三个月稍微注意点就行了,不需要再开刀了。”
“里面没有支架或者钢针什么的东西需要取出?”
“呵呵,没必要,我用的是特殊材料,会自己吸收的。”说完又冲我笑笑,示意我可以走了。
“哦,那。”处于好奇也好,处于对自己的保护也好,我本想问一下这种特殊材料,可是看到他微笑的看着我,就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支支吾吾半天,“那谢谢大夫了,您忙,我先走了。”说着穿好衣服,起身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一个完美的大夫,医德高尚,主动救死扶伤,当然我还轮不到他就死,目前只遇到他扶伤。医术高明,是院里第一把刀。为人谦和,与人无争到了几乎忍气吞声的地步。
但是这个年头找个完人是不可能的,你总能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不过有些事确实比较奇怪的。
白大夫为人谦和,但对人客气的过分,总给人一种不容亲近的距离感,所以这么多年,也没听说他和谁关系比较近。他医术精湛,有很多独到甚至不为人知的“绝技”,但是谁也没见他当着别人面做过,和别的医生一起做手术的时候表现的中规中矩,只是手上的技术更快点,更准确些,有些大夫特意请教过他,想和他学点,可是他从来不教,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手现在没人能治得了的原因。
最奇怪的就是这件地下办公室。我可是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这里,空荡荡的楼道里根本看不到人,只有头顶的荧光灯闪烁着惨白的光,发出“吱吱”的交流声,搞得我头皮直发麻。
前些年,医院条件不好,所以很多大夫只能被分配到地下的房间做私人办公室和诊室,但是近年院里经济条件好转,盖了新的医护大楼,所有的大夫都搬到了新大楼里,原来的地下房间都做了库房等别的用处。白幻辰更是分到了院长楼下的一间大房间,可是白大夫执拗的不肯搬,坚持留在这件屋子里,只有出诊的时候才去新大楼。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我自己的感觉,也不知道算不算,那就是我总觉得白大夫看我的眼神很古怪,有说不出哪里古怪。
走出阴森的地下室,我很快忘记这些奇怪的感觉,像我这个大有前途的报业青年,现在要做的事还很多,哪有心思浪费在一个古怪大夫身上;比如那些小护士,就需要我付出更多的精力去“沟通”,经过几次交道,我已经和小徐护士很熟了,既然伤好了,“感激”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现在的医院真是有钱,诊疗大楼的顶部居然有这么大个休闲区,上面是钢筋架起的玻璃穹窿顶,太阳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很是舒服。我和徐护士坐在靠边的位置上,要了两杯咖啡,晒着太阳,听着她和我讲述着诊室里林林总总的趣闻。其他的桌位上,休息的大夫,住院的病人都在享受着这温暖的阳光。
这时,一个年纪在三十出头的年轻大夫走过来坐在离我不远的位置上,喝着咖啡翻看着手上的病志夹,仿佛是无意中瞥见了我的,又瞅了眼我的左臂,眉毛皱了一下,好像在犹豫什么,又低下头看他的病志。
“前天晚上我值夜班的时候,9点多去小饭店吃夜宵,同桌一个混混看我们小罗大夫不顺眼,出言不逊,罗大夫脾气火爆就打起来了,边上的人很快把俩人架开,混混嘴里不干净,罗大夫顺口就说了句:别让我碰到,碰到了让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结果你猜怎么的,到了半夜,送进来一个被砍伤的,伤口不是很深,缝缝就好了,结果仔细一看,就是晚上那个混混……
罗大夫很客气的问:还记得我不?混混点点头,不敢吭声,然后罗大夫很客气的问到:要不要麻醉啊?混混想了半天……摇了摇头,估计是怕被麻翻了被使阴招…结果真的没有让打麻药缝的,那个小混混疼的鬼哭狼嚎的……
“哈哈哈哈,当时我们都笑翻了。”我很喜欢听小徐将她的故事,一方面是作为记者,已经习惯作为一个听众,听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另一方面,小徐在说故事的时候,很阳光,很可爱。
这时,那位年轻的大夫好像终于做出了决定,起身走了过来;看了一眼小徐,小徐便不再说话了,转头对我说:“你好,我可以坐下吗?”
“请问有什么事吗?”我注意到小徐将脸别了过去,好像不愿看见他,所以反问他,表示了我们的不欢迎,而这位年轻的大夫似乎没看出来一样,拉过椅子坐了下来。
“我们…认识吗?”我可不愿意有这么个大灯泡在这儿,而且是小徐好像很不喜欢的大灯泡。
他轻轻的笑了笑:“可以把你的手臂给我看下嘛?”
原来又是一个想偷学手艺的,这几个月这种人我见多了,每个看见我手臂的大夫都是这样,我都快成活体标本了。反正我现在外伤也好了,手上也没有打绷带、石膏什么的,看就看吧,没准又能听到一些白大夫的传奇故事。
当我正要把手臂递过去的时候,一只纤细的手挡在我和年轻大夫之间,是满脸不快的小徐:“对不起,何大夫,我的病人需要休息了,这是白大夫的患者,就不劳您费心了。走,我们走。”
年轻的大夫失望地坐回椅子,轻轻的摇了摇头,不再说话。小徐则拉着我快步的离开了休息区。
“那人就是何涛,少理他。”小徐气呼呼的说。
“他就是何涛啊,有点意思。”我想追问关于何涛的事,可是小徐好像并不想说,正好她的休息时间快结束了,便和我简单告了个别,回急诊去了。
我信步向大门走去,在门口遇到了好像刚从外面回来的何涛,手里依然拿着病志本,像不认识我似的和我擦身而过。但是就在到我跟前的时候故意的撞了我一下,病志本掉到地上,里面夹的纸撒了一地,他忙连声和我说对不起,并弯腰捡了起来。
看着他拙劣的演技我有些好笑,但是他从顶楼追下来,又在门口制造这么场偶遇估计是有话要和我说又不太方便,所以我决定配合他一下,也弯下来腰来帮他捡。
“多吃点补血的东西,小心姓白的吸血鬼。”捡完地上的东西,何大夫匆匆走了,只是留下这么奇怪的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