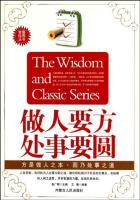那是第十八天头上,爷爷实在受不了了。不错,到这儿就是来修水库的。爷爷想,可是,这白天没头没脸地在烂泥巴里挖泥、抛泥、挑泥、夯堤,放工回来身子骨早散了架,为啥每夜还要检讨会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地开呢?
这天晚上,检讨会又开了三个多小时。回到小窝棚,爷爷浑身冰凉,他想弄点热水泡泡脚,就去拎墙角火炉上的水壶,却发现火炉早已熄了火。爷爷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说:“哼!开会!开会!鸟会!谁有问题,拉出去,毙了得了……”爷爷的话还没说完,就像木偶一样立在那儿不动了,脸色也变得煞白。窝棚里的另一个人更是大惊,瞪大眼看着爷爷。然后一声不吭,衣服也不脱,一头钻进被窝里。
爷爷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他知道自己刚才那句话的性质和后果——可以杀头!爷爷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人能放过他,不把他的话报告给大队长(大队长对思想和路线问题从来都抓得最严厉,何况爷爷还是曾经的地主)。可是,可是那人能放过自己吗?按理说爷爷是不必担心的,因为那人不是外人,而是爷爷的儿子——我父亲。然而,这几年来爷爷亲眼所见的那么多真真切切的事,哪一件哪一桩都让他放不下心。
爷爷再也承受不起批斗了,他宁愿永远、永世做牛做马,只要不批斗他。爷爷害怕极了,生起一堆柴火,把我父亲湿透的鞋子拿到火上烘烤,他想以此打动他的儿子,放过自己。鞋子烘干了,爷爷却矛盾了:他想,一旦儿子真的放过自己,但隔墙有耳,往后要是被别人揭出来,那儿子可就犯了包庇罪——包庇罪同样是可以死的。这样想了,爷爷就不希望我父亲不报告大队长了,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把老骨头而毁了才三十岁的儿子。爷爷于是把刚烘干的鞋子又泼上了水。
第二天,阴沉了多日的天,终于飘起了鹅毛大雪。爷爷虽然一夜没合眼,可到水库上挑起泥土来却是从未有过的卖力。爷爷一担又一担地挑,虽然每挑过一担就累得差不多呼不上气来,但爷爷却一担比一担挑得多,一担比一担跑得快。爷爷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心里的恐惧感。但恐惧感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因为我父亲总是远离着他,躲着他,看也不看他,甚至有几次爷爷挑着泥巴经过我父亲身旁时故意摔倒,但我父亲也像没看见,低着头迅速跑开。
晚上,爷爷病倒了(毕竟是六十二岁的人了)。躺在床上,爷爷的身子高烧得滚烫,嗓子也像冒着烟。爷爷想让我父亲到别的窝棚里倒碗开水来。可我父亲分明是一只早已吓破了胆的小兔儿,蜷缩在床角,一动不动,仿佛身旁正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与他根本没有关系。
第三天,爷爷拖着高烧的身子又在雪地里拼搏了一天。夜间十点半,开完了检讨会,爷爷跌跌撞撞地回到小窝棚,左等右等不见我父亲回来,爷爷知道我父亲是不会回来了——今晚检讨会现场的气氛就告诉了他这一点。爷爷能理解我父亲——像爷爷这样的“阶级敌人”,谁还敢不与他划清界限呢?
爷爷刚爬上床,就听门“吱”一声开了。爷爷一看,是大队长,身后还跟着我父亲。爷爷触电一般站起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大队长——灾祸终究是躲不掉的。
大队长铁青着脸,看着僵立的爷爷,摇摇头,压低声音对我父亲说:“记住,你前天晚上啥也没听到,你刚才啥也没对我说。”大队长叹口气,走到我爷爷身边,掀起爷爷的被子,示意爷爷快睡下,“挺住啊,老伙计。”就转身快速向门外走去。
突然,我父亲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抓住大队长的衣襟,“扑通”一声,直直地跪在大队长脚下,张开嘴,刚要哭出声,大队长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爷爷也终于明白了过来,他也要给大队长下跪,可他忘记了自己是站在床上。“啪”,爷爷一头栽到地上,膝盖骨跌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