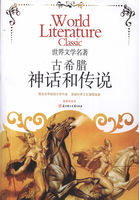晚秋天,仍是轻薄寒凉。
沈透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粉蓝色的羊毛衫,一条深黑色的小脚裤,一件深蓝色的呢大衣,她拉上窗帘,转身脱掉了身上的睡衣。
“你的纹身怎么不见了。”程依依惊讶的声音从后传来。
“什么纹身?”沈透套上粉蓝色的羊毛衫问。
“你后颈上不是有一个深蓝色的小弯月亮吗?”程依依举起右手,摇了摇无名指说:“就像这个一样。”
沈透看见程依依的无名指上纹着一个小小的深蓝月亮。
“这个你很早以前就纹了。”沈透在以前就留意到了它。
“我看见了你脖颈上的图案,觉得很漂亮,也就去依样纹了一个。”程依依看着自己的手说,“你原来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吗?”
“我不知道?”沈透把头发扶到一侧,对着镜子反照后颈,边看边说,“什么也没有啊?”
“怎么会?”程依依凑近她身侧,“真的不见了。这真是太奇怪了,我明明看见过的。”
沈透看着镜子,她摸了摸羊毛衣领下的月亮吊坠,它的颜色及形状都和程依依指上的那一个纹身相同。也就是说它和自己后颈上的图案丝毫不差,这一切一定就是苍肆做的,是他法力的衍生物。沈透理明白了这一系列情况后,笑着对程依依说:“你一定是看错了,又或者是记错了人。”
“等等,这是什么?”程依依从沈透的衣领下勾出项链坠问,“这可是新的。”
“这是我新买的。”沈透松开头发,把吊坠放进衣领里说。
“不是某人送的定情信物吗?”程依依嘟着眼睛问。
沈透笑了笑,不说话,她套上外衣,背上包,走了出去。
门关上了,沈透从衣领里拿出月亮吊坠,她低头看着,痴痴地笑了。
门在身后迅急地开了,沈透一下子转过身,看见冯雅清背着包走出来。
“一起走吧。我今天也约了人。”冯雅清看了一眼沈透衣前的项链。
路过一间饰品店的时候,沈透从橱窗里看见了一条蓝色的围巾。
那是一种很漂亮很艳丽的蓝色,沈透不自觉地走了进来。
“你最近迷上了蓝色?”冯雅清问,“你真的要买吗?你的衣柜里已经有了满满一大部分的蓝了,还不够吗?”
沈透春风拂面地说:“是的,我发现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颜色了。”
“最漂亮?”冯雅清无奈地说,“好吧。”
沈透付了钱,把围巾绕在脖子上,
“好看吗?”沈透笑着问冯雅清。
冯雅清看着沈透,她今天穿着粉蓝色的羊毛衫,深蓝色的呢大衣,如今再加上一条艳蓝色的长围巾,将同一个色系深浅交汇。
“好看。”冯雅清牵动嘴角,点了点头说,“很好看。”
这时吴循走了过来,冯雅清冲他招了招手。
“我先走了。”冯雅清说完就跑了出去,走到马路的另一边和吴循甜蜜相拥。
沈透拎着礼,用钥匙打开了门,走进去,发现客厅没有人。
她把东西放在茶几上,除下围巾,脱去外衣,听见房间里传来水声。
走进浴室,看见苍肆正蹲在大水盆盘给春儿洗澡,他把沐浴露倒在手心,双手揉搓出泡沫全抹在春儿身上。
春儿嘟着嘴,勉为其难地接受,眼见沈透来了,满脸洋溢着温暖笑容,甜甜地喊:“小透姐姐。”
“你今天的心情很好。”苍肆暖暖地笑容。
“我的心情一向很好。”沈透倚在门上说。
“先在客厅里坐会,马上就洗好了。”苍肆说着把满手的泡沫抹在春儿的头上。
“我来帮忙。”沈透走进去,说,“春儿变回原身,我也不算是占它便宜了。”
说完,见春儿点了点头附和自己,它或许并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
沈透把袖子卷上臂膀,以按摩的手法为春儿洗澡,从后背揉到小肚子。
春儿很舒服地享受着,她高兴地从水盆里站起来,摇着头甩开周身的毛发。
肥皂泡四下飞开,苍肆拉起沈透笑躲到一边。
“还是我帮它洗吧。”苍肆弹了一下春儿的脑袋,用花洒向它喷水。
“小透姐姐。”春儿委屈地喊。
苍肆给春儿洗完澡,沈透用一块大浴巾把它包裹住抱回倒客厅,轻放在床上。
洗完了澡的春儿,脱胎换骨般干净。胜雪纯白,还散发着一种薄荷的芬芳。
沈透到处找不到吹风机,大声地问:“吹风机放在哪儿。”
“放在叔叔的房间里。”春儿湿着声音说。
沈透推开苍肆的房门,不期地看见苍肆站在衣柜前,上身赤膊,谦谦笑容。
“对不起。”沈透红着脸关上了门。
正烧着心,门突然开了一条缝,沈透看见苍肆递出了吹风机。
沈透拿着吹风机,插上插座,把春儿吹得干干的。
春儿听着吹风机的声音一停就腾空跃起,扑在沈透身上,撞了一个满怀。它在沈透怀里嗅了一会,就趴下不动了。
“倒是把你累坏了?”沈透笑起来。
“春儿特别亲你。”苍肆换好衣服,进来看见沈透和春儿相亲相爱地其乐融融。
“当然。”沈透当仁不让地承认。
“我比喜欢叔叔还要喜欢小透姐姐。”春儿非常温顺地窝在沈透怀里。
“春儿,真好。”沈透说着拿过一边的围巾缠绕在春儿的脖子上。
……
正午过后的太阳喜气洋洋的,沈透伙同苍肆坐在阳台上的秋千椅子上享受光芒。
暖阳曛人醉,沈透莫名地想法消极。
爱这种东西,就算能胜得过人心,也敌不过时光。
就像数之不尽的前例一样。
她转头问:“苍肆,你能爱我多久?”
苍肆认真地看着她回答说:“至少一千年。”
沈透笑到极处,吟吟地说:“聪明的回答,看不出你平时那么老实,居然也有这么深的心眼。”
两人立得很近,近得沈透从苍肆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苍肆自然地抱住沈透,握起她的手转压在自己的心口上。
“你把它据为己有了。”他这样说。
沈透闻见融融的清香味道。
伴随着苍肆的清晰心跳,清香味变得越来越暖和。
沈透不知道自己此时应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他怀里,一直僵到苍肆放开她。
她头昏脑涨地发现自己在苍肆雪白的衬衫上印下了一小块橙艳。她看着他,不好意思起来,两颊妃色。
苍肆笑着,浑身上下都到是一种体贴和温柔。
沈透轻声说:“我喜欢你抱着我,喜欢与你纵情欢乐。”
苍肆听见沈透毫不羞涩地说出这样一句话,爽爽气气公开地承认她的依恋。心不胜欢喜,他笑着把沈透额前的细发扶到耳后,柔和地拥抱她。
“我永远的爱。”苍肆用双臂抱着沈透,正正经经地亲吻她的前额。
小透把头依在苍肆的肩上,两心相扣,她听见他的声音低不可闻。
“爱若太久,已和呼吸一样本能。”
尽管低不可闻,也还是听见了。她看见苍肆眼里有梦的气息,也有浓浓的怀念。
苍肆拥抱着沈透,立志天长地久,不愿放手。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苍肆依然使劲地抱着她,并无丝毫放松。
“我不会跑。”沈透解释说,“所以不需要抱得这么紧。”
“对不起。”苍肆松了松手,却依旧锁着她。
沈透靠在他的肩上,侧脸伏着,她的手放在他的腰上。
心血来潮的念头,迅雷不及掩耳地支配行动。沈透拥着苍肆亲了他一下,然后低着头飞快地跑开了。
沈透跑远了,才停下来,回想刚刚的一幕,烧红了脸。她是不是该矜持一些,娇羞怯人,楚楚含情。男人都喜欢这样的,苍肆已经修炼成人,审美观也应该入了乡,随了俗。
正思考间,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沈透很开心地回头,待看见王流光,表情变得有些叵测。
王流光发现沈透转过的面孔表情起伏,最终沉淀成一种尴尬的神态。
“好久不见。”沈透摇了一下睫毛说。
“真的好久不见。”王流光一直在笑。
“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沈透调整好面部的表情问。
王流光只言片语不答,他伸出手,黑色的眼睛里有依恋。
沈透后退一步,来源本能。
王流光立时屈了眉。
“你误会了。”沈透见他如此,心内不安,急忙开口解释。
“误会了什么?”王流光目光滚烫地说。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沈透措辞说,她还要再说什么,这时春儿冲上来咬她的裙子。
“春儿,你干嘛?”沈透拉住裙子。
春儿还是不放,咬住她的衣服把她往后拽,远离王流光。
“春儿,松开。”沈透拽出裙子。
春儿却又是一口,把她的裙子抓咬得更紧。
或许春儿以为王流光是它叔叔的情敌,所以这么防范措施。
沈透想狐狸可真是狡诈万端,只可惜聪明用不到好处。
“我们当然是朋友。”王流光笑得牵扯。
“我们只是朋友。”沈透垂下眼皮说。
王流光难过地看着她,强扯出一丝笑意,“我不想失去你。”
“我们还是朋友。”沈透眼睛一抬,又垂低下不看他。
“我依旧执迷。”王流光笑了,表现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样子。
沈透还是说:“你的幸福在别处。”
王流光上前一步说:“你就是我的幸福。”
沈透不想再作纠缠,转身就走,半途被王流光强硬地抓住手腕。
他说:“我很爱你。”
沈透使力地挣扎,也去不了禁锢,火气随着力道一起上升。
“我有权不喜欢你!”沈透怒气冲冲地说。
王流光终于松了手劲,阴气森森地看着她。
沈透稍稍平静下来,嗫嚅地说:“对不起。”
王流光看着沈透的眼睛说:“你别无选择。”
黑色的睫**近,沈透看见王流光的眼神里充满了阴郁,但他在努力平息。
身边的一棵大樟树上,站着好几只可爱的小鸟,它们全都叽叽喳喳地乱叫着,扑扇着翅膀想飞又不敢飞的凄凉。
王流光的眼神微变。
一阵阴风长呼之后,沈透莫名地就被王流光怀抱住,她想要推开他,却没有力道。又见王流光的眼神莫名,沈透发现他的眼睛飞快地掠过自己身后。她转头去看,看见了苍肆严冷的脸。
“苍肆。”沈透气冲冲地看了王流光一眼,一眼未完,已被苍肆拉住。
“你爱上了他。”王流光冷着声问。
三人僵持了好半天,直至沈透被苍肆拉走。
沈透被苍肆硬拉着走了很远的路,他们最后停在了一处百花盛地。
苍肆无言地站着,石化了面孔。
“苍肆。”沈透怯着声喊他。
苍肆不言不语,就只是站着看着她。他见她看过来,竟转身顾自迈步走了。
沈透见苍肆不理她,心中一慌,急忙快步追了上去。她一路小跑,才能勉强跟上他的大步流星。
沈透紧跟着苍肆,审视他脸上的表情。他快步走路,整张脸紧绷着,怒气冲冲。
“你别误会,我和他没有什么,刚刚只是……”沈透边说边拽他的衣袖。
苍肆不答不理,仍然快步走他的路。
“他的一厢情愿,他真的只是朋友,朋友而已。”沈透跟不上他的脚步,快速地说,“你不会真的不想理我了吧?”
“你要是真的不想理我,早就可以腾云驾雾飞走了。”沈透娇气地嗔。
苍肆停下脚步说:“我告诉过你,离他远点!”
沈透竭尽全力控制住熊发的怒火,强迫自己委屈求全,和颜悦色地说:“我对你神魂颠倒,如痴如醉。”
“我没有开玩笑!”苍肆大声地说,之后又是快步地走。
沈透吓了一跳。咬牙切齿,竭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想起了父亲,以前自己闹情绪时,不论对错是非,结果都只有一个。
“怎么了?”父亲带着笑问,一贯的缓势求和招数。
……
又不是自己的错,凭什么这样委屈地受他冷漠。她都已经好言好语地哄他了,他凭什么大声吼她。
沈透火冒三丈,话到了喉口,又觉得跟苍肆歇斯底里太不必要,她一跺脚,转身返折,头也不回昂首挺胸而去。她才走几步,就听见苍肆在身后喊她。
沈透置之不理,继续往前走。
叫喊声继续跟上,沈透置若罔闻,她又走了几步,臂上一紧,就被苍肆拉住。
沈透甩开了苍肆的手,快步向前方跑去。
苍肆轻易地抓住沈透,力度很大,拉她折回身,控制住她的行动。沈透使劲地推踢苍肆,奈何他不动如山。
沈透不耐烦,拨开视线前的头发,怒不可遏地瞪着苍肆。
他看着她不说话,两人陷入长久式的沉默。
沈透听着彼此整齐步调的呼吸,面无表情。
“我道歉。别生气了。”苍肆的声音暗哑。
沈透黑着脸不作声。
“我错了。”苍肆认错伏低。
“狐的性格真是不可捉摸,一会儿指高气昂,一会又低声下气。”
“我错大了。”苍肆低眉下首地说。
沈透压着回春的心情说:“你该知道的,你有能力读出我的心,可以看见我的心思。苍肆,你到底在气什么?”
苍肆不答反问:“你不是不允许吗?”
沈透无力地笑,口不能言。
苍肆也笑得开心,两人和好如初,其乐融融。
沈透笑着,心思百转千回,一团乱麻有了一个出挑的头绪。她掩去面上的难以置信,斩钉截铁地说:“他和你是一样的。”
苍肆突如其来地不可理喻,他和王流光对峙时银装素裹的面孔、剑拔弩张的对视,以及王流光过于森黑的眼睛……
所有的事情都指引出一个方向,王流光是苍肆的同类,不是狐,也是妖。
沈透仰头问:“王流光……他也是九尾狐?”
苍肆反问:“你不害怕?”
植物的光和作用强烈,回光反照光芒。
沈透虚软地笑着说:“我已可以面不改色地面对一切奇人异事。如今我未知的领域正在逐步缩小,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话题了。”
“你看过《封神榜》吗?”苍肆突然问。
“电视剧看过,小说看不下去。”沈透说,“满篇文言不知所云,从头到尾就是说女娲娘娘拿天下苍生赌气。”
沈透不明白苍肆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题,封神榜难道不仅仅是个神话传说吗?
这天下午,苍肆对她讲起了一段博大精深的九尾狐史。
古时,狐分两派,玄白各自为政。白狐一族毛色尽皆雪白,玄狐一族则是彩色缤纷。两族起初只是色相不同,但都一心一意信奉道法,认为“犯杀生罪,必坠恶业。”两族各自隐于山谷,闭洞迁修。
千年百世,沉心息虑,清净度时,终生持戒。
奈何修炼正道,真途深奥,纵使专心致志地千载修行也难以企及。时日一久,玄狐一族便不再苦行难练,他们急功近利内丹邪修,****借气,迷人害命。
“此非登仙之路,而是成魔之法。灭残生命,所行不正,罪在不赦,天当施诛。”
白狐之主宜主苦言劝说,希望玄狐一族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希望他们可以痛改前非,为善行慈,累功积德,但大都是无功而返。
人世新旧,尧传舜,舜传禹。禹传位于子启,建“家天下”,国号为夏。夏传于十七代,履癸继位,史称夏桀。夏桀嗜酒好色,生活奢侈,以致国事荒废,民不聊生,愁声障天。
大地之母女娲娘娘招聚众妖,选中白狐始祖宜主灭夏基业。许之功成之日,便能得入神道,名列仙籍。
宜主为白狐先祖,纯修苦练,行功积德,已达千载之功。她一心修道成仙,是以谨奉女娲法旨,扶商灭夏。
当时,夏桀征伐有施,有施氏屈膝求和,将公主妹喜作为赎罪送至夏宫。妹喜国色天香,绝色姿容,诗文描述:“有施妺喜,眉目清兮。妆霓彩衣,袅娜飞兮。晶莹雨露,人之怜兮。”
宜主日思夜想,心生一计,她隐去妖形,附身妹喜,隐于夏宫。自此妹喜为夏桀所宠,日日酒池作乐,笑听裂帛之声。不久之后,她被立为王后,尊荣无比。
珍重荣宠,夏桀情深。
国中百姓,苦不堪言。
怨气冲天,众人心毒咒诅:“时日曷丧,予及如偕亡!”于是商汤归应天意,起兵讨夏。桀于鸣条战败,携妹喜同舟度江,后死于南巢之山。
南巢山上,宜主九尾全修,成就正果,身列仙阶,修到天狐地位。据苍肆的姑姑说,那一天的宜主全身毛发金光辉煌,灿烂罩世。
自此,狐修九尾为瑞。
众狐见宜主仙化飞升,豪光万丈,心中向往大甚,纷纷致力于股生九尾,修炼仙体,故此更加专注虔诚。
玄狐一族希望族中也能出一九尾天狐,一直等到商纣王时,成汤气黯,当失天下,凤鸣岐山,圣主已生。
玄狐族中一只金毛狐狸,名夷简。其取得法旨,附身于冀州侯苏护之女苏妲己。后而潜入宫禁,惑乱君心,使其不行正道,断送成汤六百年。
礼乐崩坏,殷商业毁。大周新立,夷简任务完成,但她荼毒忠烈,残害众生,甚至炮烙虿盆,敲骨验髓,剖腹看胎,其罪足以弥天。
夷简终为姜子牙所斩,首级挂于辕门。
玄狐一族获罪于天,暗于地室。
“自此,九尾狐族的神圣和荣光就彻底丧失了。”苍肆如此说。
“王流光是九尾玄狐一族?”沈透了然。
“他是玄狐这一代的王。”苍肆随沈透走进房间,关了门回答说。
“那这几个月的人口失踪,也是他干的?”沈透的脑海里拼凑出一只黑色的九尾大兽,它黑着疯狂邪恶的眼神。
分明是程依依受伤那夜,树后一闪而过的黑影,无数条鞭形。
“他是不是一头黑色的狐狸?”沈透抓住脑中的思绪。
“玄狐一族有修炼邪法,长此以往,魔气缠身。他们或浅或深都是黑色的,皮毛越是深黑,魔力就越高。”
“程依依也是他害的?”沈透的声音残缺难辨。
苍肆摇了摇头说:“不一定是他。”
沈透松下了一口气,又猛地想到了一个问题,玄狐一族应该不会想暴露出他的秘密,哪怕是丁点的蛛丝马迹。可他们却没有再加害程依依灭口,也没有抹去程依依脑子里关于那一夜的记忆,玄狐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沈透紧张地说:“程依依她还记得那晚发生的事。”
苍肆僵了僵说:“我施了禁咒,她不可能想起那夜的事。”
“她还记得。”沈透看着苍肆问,“你抹去了她的记忆?”
“或许是有人对她施加了第二次忘咒,两法相冲,失了作用。”苍肆抱住沈透说,“没关系的,不要担心。我会处理好的,你只要离王流光远远的就好。”
沈透依在苍肆怀里,只觉得脑子里一团麻乱,就连眼睛也疼了起来,她闭上眼睛不去想任何事情。
“叔叔,我……”
沈透听着声,张开眼就看见春儿用一双狡猾的眼睛牢牢盯住他们。
“我太没眼力劲了。”春儿一本正经地说。
说完,它天真烂漫地大笑,边笑边卷起短尾巴,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体,白白地滚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