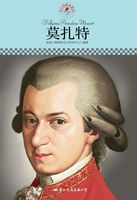据说:浩瀚的沙漠中,一支探险队在艰难地跋涉。头顶骄阳似火,烤得探险队员们口干舌燥,挥汗如雨。最糟糕的是,他们没有水了。水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信念,信念破灭了,一个个像散了架,丢了魂,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队长。这可怎么办?队长从腰间取出一个水壶,两手举起来,用力晃了晃,惊喜地喊道:“哦,我这里还有一壶水!但穿越沙漠前,谁也不能喝。”沉甸甸的水壶在队员们的手中依次传递,原来那种濒临绝望的脸上又显露出坚定的神色,一定要走出沙漠的信念支撑他们踉跄着,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去。看着那水壶,他们抿抿干裂的嘴唇,就觉得周身不断地升腾起力量。终于,他们死里逃生,走出茫茫无垠的沙漠,大家喜极而泣之时,久久凝视着那个给了他们信念支撑的水壶。队长小心翼翼地拧开水壶盖,缓缓流出的却是一缕缕沙子。他诚挚地说:“只要心里有坚定的信念,干枯的沙子有时也可以变成清冽的泉水。”
我去投奔黑龙江绥滨县姨妈家和三哥家。三哥是早几年带着三嫂和孩子投奔姨妈家的。在那落了户,姨妈家在庆和大队,三哥家在东升大队,都在一个叫大同的公社,相距18华里。
从海林到牡丹江到佳木斯到富利屯都是乘火车。那时候火车经常无缘无故地晚点,验票也松,一路上几次验票都让我轻而易举但又非常内疚地混过去了。只最后一次挺危险,我推开车门,躲到车厢外边的车梯上,那正是寒冬,我用胳膊紧紧地挽住冰冷的扶手,火车飞驰,刀子一样冰冷的飓风几乎可以把我掀下火车抛到车轮下轧成肉沫,我咬着牙与飓风顽强地抗争……从富利屯到富锦是长途客车,这可就不像火车了,不买票无法上去。我口袋里只有一角一分钱,从家里带的玉米面大饼子已经吃完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用这唯一的一角一分钱买了两个白面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身上就一分钱也没有了。我在富利屯长途客车站候车厅里茫然地转来转去,一张俊俏红扑扑微笑着的面孔给了我一丝暖意,那是一位披军大衣的兵团知青大姐,每当我从她面前漫无目的地走过之时,她都会冲我微笑着,示意我可以坐到她面前的大行李上,但我每一次从她面前走过之时,我都没有领她这份情,若干年之后,这张冲我微笑、给我让座的知青大姐的面孔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我遇到了几个拉家带口逃荒而来的安徽老乡。安徽老乡也是去绥滨的。绥滨与前苏联隔着道黑龙江,是当时的边防重地,没有边防地区通行证是不得随意出入的。安徽老乡没有边防证,又不熟悉路,怕去不成,我对他们说我也没边防证,但我去过绥滨,很熟悉,只要到了富锦,我就知道怎样走过去。几位安徽老乡如同遇到了救星,托我一定帮忙给他们带路,他们替我买了一张去富锦的长途汽车票。到了富锦县城,天已经黑透了,天寒地冻哈气成霜,富锦与绥滨隔着道松花江,相距二十多华里,正赶上刮烟炮(暴风雪)。
这是1976年12月底的一个夜晚,天寒地冻,正是可以冻掉下巴、冻掉鼻子的天气,零下四十度左右。我这样一位少年孤身只影背着书包在街头上徘徊,我已经难以抵御严寒了,我沿街逐家叩门,所叩开的商铺、机关、工厂的传达室里面,都烧着通红的火炉,要多暖和有多暖和,我恳求更夫留我住上一晚或者让我在传达室里暖和一小会,所到之处都遭遇了更夫们严辞拒绝:“不行!谁知道你是干啥的?兴许是苏联特务呢!”
夜更深了,天更冷了,风雪肆虐,像无数的野狼在大街小巷狂奔怒吼,我就要被暴风雪吞噬,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穿蓝制服的警察。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夜半更深,你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警察首先把你当坏人,“干什么的?不准动!”
我自投罗网向警察求助,“叔叔,我……没钱住旅店,您能帮帮我吗?”
警察厉声说:“有证件吗?”
我哆哆嗦嗦地从书包里摸出原始部落农村生产队的证明,证明上写着我要去与富锦县一江之隔的绥滨县大同公社东升屯的三哥家探亲。这下完了,警察“咔!”给我带上了手铐,“你知道绥缤县是什么地方吗?边防重地,必须有边防通行证。跟我走吧。”
警察把我押到了一个高高的大铁门前,“当当当”踢了几下,大铁门开了条缝,我被警察推了进去,我还没来得急回头看一眼,大铁门咣啷一声关上了!这是拘留所。一个阴森森的大院,周围高墙上拉着铁丝网,一间低矮的平房,里边闪着昏黄的灯,透过小铁窗,可以见到里面晃来闪去的人影,有唱的、有怪叫的、有骂娘的……警察押着我进了拘留所,这里马上鸦雀无声,刚才还又吵又闹形形色色的嫌疑犯们这会儿都如老鼠见猫一样规规矩矩地沿两侧大火炕垂手而立。
警察往大炕上盘腿一坐,抽着当时名贵的牡丹牌香烟,铁青着脸开始训话了:“把小号里的也给我放出来!”刚才进来时,开大铁门的那人把一排像囚野兽的木笼子一样的小号的门逐个打开,里边出来的人都疲惫不堪。有一位是漂亮女人,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有一个是残疾人,前面一个包身后一个包,龟缩着脖、愁眉不展,痛苦得直哼哼。
“你们他妈的都是些什么人?都给我坦白交待!从你开始。”警察手指着那残疾人。残疾人小声说:“在街上掌鞋(东北方言:修鞋),走资本主义。”
“你那?”警察指着漂亮女人。漂亮女人垂着头说:“公社主任调戏我。”
“你家庭出身?”警察横眉立眼手往火炕上一拍。
漂亮女人流下眼泪,“俺爸是地主子弟,可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弟的子弟”但他还是主动认罪:“是我拉拢腐蚀革命干部。”
这个年代把人分成三六九,把早已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子弟、子弟的子弟,永远地烙上个印迹:你出身不好,就是个坏人,所有的动机都是有罪的。当人们嘲讽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的场合就变了一种说法。三十多年后的一些看守所的公安人员也许会这样问:“你爸有钱吗?有钱拿钱放人,没钱你在这呆着吧你。”
接下去的有酒后行凶、打架斗殴、聚众赌博、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强奸嫖娼、偷听敌台……最后轮到我了。
警察声色俱厉:“你哪?坦白交待!是不是特务!”
我吓得两腿筛糠,如实坦白:“我不是特务,我是黑龙江省海林县三道沟公社二道河大队原始部落屯儿的,我要读书、我要学习。”
“扯蛋!读书学习不在家老实呆着,跑出来干啥?”
我委屈地哭了:“我妈老打我,说读书学习不当吃也不当喝还有娶不上媳妇,俺们那屯的生产队长也不让,说俺一心成名成家。我去投奔绥滨县东升屯俺三哥家。”
警察勒令:“身上、还有书包里都藏着什么东西?统统交出来!”
我从书包里掏出了第一件东西,是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掏出了第二件东西:还是一本书:《红岩》;掏出第三件东西:《青春之歌》!警察怒目圆睁,跳了起来,“好啊,这些都是毒草!还有什么?”
我又从书包里掏出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党史》……然后我把书包翻过来,抖落了一下,没抖落出任何特务用的犯罪工具,抖落出了一层玉米面大饼子楂……
警察没话说了,但也没说放我走。
接下来,警察叫出酒后行凶的大汉,命令他把残疾人用根细麻绳勒起来,残疾人被勒得呲牙咧嘴,一个劲儿求饶:“哎呀呀,爷爷饶命啊!我再也不上街掌鞋走资本主义了。饿死也不干了,俺也是贫下中农啊。爷爷饶命吧。”
大汉心软了,把麻绳松了,警察马上又叫个人来勒酒后行凶的大汉。这人一脸横肉,心狠手毒折磨人很专业。他用细麻绳捆住大汉的一只手腕,从后背往肩上吊!吊!大汉咬紧牙关、脸涨得紫红,豆粒大的汗珠成串地滚落下来,终于忍不住了,骂道:“我操你八辈子祖宗——强奸犯!”强奸犯把细麻绳从大汉的脖颈前绕过去把他的另一只胳膊也狠狠地吊了上去,吊得咯咯直响,大汉呼天喊地:“操你妈呀,胳膊断了胳膊断了……”大汉喘不了气了,被勒得翻白眼了,眼看就要勒死了。
警察命令强奸犯松手,骂道:“你他妈也太狠了。”又叫刚脱离酷刑的大汉反过来折磨强奸犯。大汉脱下鞋子,猛扇强奸犯的嘴巴,强奸犯的嘴巴眼看着被硬鞋底扇得乌青,强奸犯爹一声妈一声地嚎叫,最后被关进小号,换出来了残疾人……
我在这被称之为“不法人员学习班”的拘留所关押了五天,每天刨大院厕所里冻成冰块的大粪用人力车往郊外的农田里面送。有几次,同情我的伙伴悄声对我说:“你又没犯什么法,溜掉算了。”
我也想溜,但我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放在拘留所里的那些宝贵的书。这天,我想利用往郊外送大粪的机会逃掉,出拘留所之前偷偷地把书包背在外衣里面,把几本宝贵的书籍分别藏在衣口袋、书包、裤档里,但被不法人员学习班的班长——货真价实的抢劫犯发现了,他凶神恶煞一般地追了出来,他喊着:“抓住他!他想跑。”
和我一块往郊外推车送粪的伙伴用眼神向我示意:“快逃吧。”
我撒腿便逃,我知道万一逃不脱,落入抢劫犯的魔爪肯定会遭遇生死劫难,不死也会扒层皮。我慌乱之中却逃进了一个死胡同,情急之下我像一只被逼急的野狗那样攀上一堵墙,在飞身跃下之时我还心存侥幸,这下枪劫犯追不上了,哪曾想,落地才发现我自投罗网——这是公安局的大院内。
我听到抢劫犯在大院外喊:“他跳进大院了,把住大门,逮到他要他大腿分叉!”我恐怖极了,像个走投无路的羔羊,怯生生地走进公安局司法科,一个瘦高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长得像面条似的警察发现了我,“你找谁?”
我哭了:“叔叔,我就因为没边防通行证明被关进拘留所。”
面条似的警察叔叔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怒目圆睁,直奔我走过来,用两只白净棉软的拳头把我击出门外,“去去去,谁让你出来的,回拘留所去!”
我被守在大门口的抢劫犯押回拘留所,他叫来几个小偷流氓把我毒打了一顿,然后把我塞进小号。那小号阴暗潮湿,坐不能坐躺不能躺只能在里边像条狗似地蜷曲着,那份屈辱那份委屈令我一生都忘不了。让我担忧的是拘留所的种种黑幕,一个晚上我听这里的人闲聊:一位管教干部握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用枪管猛敲被拘人员的额头,一下、两下、第三下,“咣”地一声走火了,倒下的不是被拘人员,而是管教干部自己,子弹射中了他自己的小腹,我如果在这里被长期拘留万一有一天那样的子弹射中了我,我的理想我未来不都变成子虚乌有了吗?
“二月二龙抬头”那一天,管教所所长来了,所长瘦瘦的,脸尖尖的,有一双怀疑一切的冷峻的眼睛,他审迅我:“你怎么回事?”
我把随身携带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又一本的书给他看,所长目光变得柔和善良,他石破天惊地笑了,“你比我们公安人员都爱学习,这些就是你的边防通行证,好了,你可以走了。”围观的“不法人员”们都为我绽放出了笑脸,一个做旅窃的小偷说:“他一进来我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干坏事的!” 我装好书正要走,所长朝我摆摆手,“今天二月二龙抬头改善伙食,你吃了过水面条再走!”
中午,我在拘留所陪着形形色色的嫌疑犯们吃了两大碗过水面条,走出拘留所森严的大铁门,登上高高的松花江大坝,当我眺望到千里冰封的松花江下游江对岸的一个小村落时,我兴奋极了,那个还要走上二小时路程才能抵达的小村落就是三哥家所住的东升屯!我高声呼喊“我要上大学啊!”朝着东升屯一路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