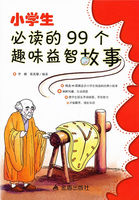福尔摩斯先从壁炉台角上取下一瓶药水,接着从一个整洁的山羊皮匣子内拿出皮下注射器。他那白皙而有力的长手指装好了细细的针头,挽起他左臂的衬衣袖口,他默默地凝视了一会儿自己胳膊发达的肌肉,上面留有许多针孔痕迹,最终将针尖刺入了左胳膊,他推动小小的针心,接下来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自足地喘了一口长气。
他每日三回这种举动,几个月来,我已经见惯不怪了,但我心中总是有些不舒服。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这种情形对我的刺激越来越大。由于我缺乏勇气阻止他这样的行动,每当夜深人静,一想起这事,我就感到内心不安。我多少次想对他说说心里话,不过,因为我的伙伴性情孤僻,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并且不大接受别人的意见或建议,让我感到要想向他进一次忠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坚定的毅力,自以为是的神态,以及我所体验过的他那非同寻常的性格,都使我怯懦而不想惹他不高兴。
然而,这一天的午后,或许是我在午餐时喝了不少葡萄酒,或许是他满不在乎的态度惹恼了我,我感到再无法容忍了。我追问他:“你今天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吗啡,还是可卡因?”
他刚翻开一本旧书,软弱无力地抬起头来,说:“可卡因,7%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我毫不客气地说:“我不需要这种东西!参加阿富汗战争,害得我的体质到今天也没有恢复,我再也不会摧残自己的身体了。”
这回我真的生气了,可他却没有丝毫不满,含笑说道:“华生,或许你是对的。我也清楚这东西有害身体,但我感受它既有如此强烈的兴奋与醒脑的功能,它的副作用对我也就不重要了。”
我真诚地说:“但你得考虑一下利害得失呀!你的头脑或许如你所说的那样,能够因这东西的刺激而兴奋,不过,这到底是危害自身的行为。它会不断导致加剧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也会引起长期衰弱,你也清楚它能引起的种种不良反应,对你实在是得不偿失。你为何只顾短暂的痛快,危害你那天赋的过人的精力呢?你应当清楚,我这不单单是从朋友的立场说话,我还是作为一个医生对你的健康负责而说话。”
看起来,我的伙伴听了我的话不但没生气,反而将十指对顶在一起,让两肘安放在椅子扶手上,他摆出一副对这番谈话很感兴趣的模样。
他解释说:“我不好静,天性好动,一旦无所事事时,我就会六神无主。要不断给我难题,给我复杂的工作,给我最深奥难解的密码,给我最精密的分析工作,这样一来,我才会觉得很舒适,才不需要这种人为的刺激。平庸的生活,是我最憎恶的,我总是追求精神上的兴奋,所以,我选择了自己特殊的职业——换句话说,是我创立了这个职业,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我问道:“唯一的私家侦探吗?”
“唯一的私家咨询侦探!”他加了“咨询”这个词表示更正,自豪地说:“我是侦探工作的最高裁决机关!当雷思维德、格莱格森或阿瑟尔尼·琼斯遇到难题时——这是他们经常遇到的——他们就会来向我求教。我以专家的资格审查材料,仔细观察,然后贡献作为一名专家的意见或建议。因为我不居功,报纸上也不表彰我。咨询工作本身令我的超凡精力得到发挥的这种快乐,就是我最喜欢的报酬。你总还记得在杰弗逊·霍普一案里我的工作办法告知你的经验吧?”
我热烈地回答:“对,我还记得。那是我生平从未遇到过的破案经历。我已经将案情的始末写成了一本小册子,还用了一个新鲜的题目——《探究血字的秘密》。”
我的伙伴表示不满地摇头说道:“我大概看了一遍,但实在是不敢恭维你。要明白,侦探术是——或者应该是一门无比精确的科学,应该用冷静的方法而不是凭感情来研究它。你将它渲染上小说故事的色彩,结果,写得就像是在几何公理中掺入了恋爱故事一般。”
我反驳说:“不过,事实当中的确有像小说故事的情节,我总不能歪曲事实吧!”
“这样的事实,你可以不写,至少要将重点所在说明清楚。这个案件里唯一值得一提的,仅仅是我如何从发生的结果找到原因,再通过精密的分析、准确的推断而破案的过程。”
我写那本小册子,本来是想让他高兴,没料到反而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我承认,他的自负傲慢惹恼了我,他的要求好像是这样:我的写作必须百分之百描述他个人的行为。在我跟他一起居住在贝克街的几年时间里,我很多次发觉,我的伙伴在沉默不语或好为人师说教的态度里,隐藏着傲慢与自负。此时,我真不愿多说话了,只是坐着慢慢抚摩我的伤腿,我的腿曾被枪弹打穿过,尽管现在走路无碍,不过一遇天气变化就觉得十分痛楚。
停了几分钟,福尔摩斯装满了烟斗,平静地说:“最近,我的业务已发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了。上个礼拜就有一个叫弗朗索瓦·勒·维拉德的人来向我求教,你或许清楚,此人在法国侦探界里已初露锋芒,他具备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但缺少提高他的侦探技术所需要的广博学识。他求教的是关于一个遗嘱的案件,颇有趣味。我介绍了两个类似的案件给他作为参考:一是1857年发生在里加城的案件,二是1871年发生圣路易城的那个案件。这两个案件给他指明了破案的正确途径。这就是今天一大早我接到他的感谢信。”他把一张被弄皱了的外国信纸递给我。我仔细看了看,发觉信中出现了不少恭维话,有“伟大”、“手段高超”,“行动有力”等表达这个法国人的热情、赞誉甚至景仰的话语。
我评价说:“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在跟老师讲话。”
我的伙伴淡淡地说道:“哦,他把我给予他的一些帮助估计过高了,其实他自己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理想侦探家的条件,他大多都具备。他有非凡的观察、推断能力,仅仅缺少学识而已,不过,学识他以后是可以学到的。目前,他正将我的几篇简短的作品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我的伙伴笑道:“你不知道吧?说来惭愧,我写过几篇专业论文,全是有关侦探技术方面的。你记不记得这一篇:《浅论各种烟灰的辨别》。在论文里边,我列举了140种雪茄、烟丝和纸烟等的烟灰,还应用彩色的插图形象地说明各种烟灰之间的差异。这是在刑事案件中经常出现的证据,有时很可能是案件最重要的线索之一。若你回忆一番杰弗逊·霍普案件,你就会明白:烟灰的识别,对于破案是会有一定帮助的。比如,你能发现在一宗谋杀案里的罪犯是吸印度雪茄的,如此一来,就大大缩小了侦查范围。印度雪茄的黑灰与‘鸟眼’烟的白灰之间的差别,在有经验的侦探看来,就好比土豆与白菜之间的区别一样清清楚楚。”
我说:“你侦查细微的事物,的确拥有非凡的才能。”
“只是它们的重要性被我感觉到了而已。这即是我写的有关跟踪足迹的专业论文,里面还提及运用熟石膏保存足迹的办法。这儿还有一篇新写的微型论文,主要说明一个人的手形受其职业的巨大影响力,配有水手、石匠、排字工人、木刻工人、织布工人、磨钻石工人等职业的手形插图。这些对于科学的侦探术,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或意义。尤其是在遇到无名尸体的案件或探究犯罪分子的身份时大有用处。哦,我只顾说我的爱好,你是否心烦了?”
我诚恳地说:“不心烦,我听得津津有味呢!因为我曾亲身体验过你对这些方法的应用。你刚才说到观察、推断,我以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
我的伙伴舒适地靠在椅子上,从烟斗里吐出一缕浓浓的蓝烟,悠悠地说道:“这两方面没有任何关联。举例而言:我现在观察的结果说明,你今天早上曾到威格摩尔街邮局去过,进一步推断,我就知道了,你还在那儿发了一份电报。”
我说:“是的,你推断得完全正确!不过,我不明白,你是如何知道的呢?那只是我一时突然的举动,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看到我的惊讶,我的伙伴颇为得意地笑道:“这个非常简单,根本不用解释,但可以说明一下,可以弄清观察、推断的范围。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沾着一小块红泥,威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挖出的泥堆在便道上,进邮局的人,很难不踏进泥里去,那儿的泥是一种特殊的红色,据我所知,附近其他地方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这就是我从观察方面得来的,其他的就是由推断得来的结论了。”
“那么,你如何推断到我发电报呢?”
“今天几乎整个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对面,并没有发现你写信。在你的桌子上,我看到有一大整张的邮票与一摞没发出去的明信片,那么,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还会干什么呢?排除多余的因素,剩下来的就是真实情况了。”
我稍微想了想说道:“这件事,确实是这样,正如你所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了。现在,我要给你一个较为复杂的考验,你一定不会觉得我在无礼吧?”
他说:“恰好相反,我很欢迎你的考验,这能够令我不再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你所提出的问题,我都愿意进行研究。”
“我常听你吹嘘,在任何一件日用品上边,很难不留下某些可以发现使用者一些重要特征的痕迹,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出来。现在,我这儿有一块新得到的表,你能不能从上边发现它的旧主人的习惯或性格呢?”
我将表递给了他,心里不由暗暗好笑。在我看来,这个实验是特别难以成功的,可以算是我给他傲慢、自负的一次教训吧!他将表拿在手里,仔仔细细地端详,先瞧了瞧表盘,接着打开表盖,留心查看里边的零件,他先用肉眼然后又用高倍放大镜进行观察。我似乎发现他面部的表情有些沮丧,我差点儿笑了出来。终于,他关上了表盖,把表递还给了我。
他说:“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遗留的痕迹,这是因为这块表最近擦过油泥,把最重要的痕迹掩盖了。”
我说:“确实不错,这块表是擦过了油泥之后才到我手里的。”我心里对他用这一点做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非常不以为然。就算是一块没修过的表,又能发现什么有助于推断的痕迹呢?
他眼睛似闭非闭,对着天花板说:“尽管遗留的痕迹很少,但我的观察并没有全部落空。我姑且猜一猜,请你斧正。我想,这块表是你哥的,而且是你爸留给他的。”
“对!你是从表的背面所刻的HW两个字母知道的吗?”我问道。
“是的,W代表你的姓。这只表基本上是50年前制造的,表上刻的字与制表的时间不相上下,因此,我推断这是你老一辈的遗产。根据习俗,凡是珍贵的物品,大多传给长子,长子通常又沿用爸爸的名字。若我没记错,你爸爸已去世多年,因此,我判定这块表是属于你哥的。”
我承认说:“这些都没错,你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你哥是一个行为放荡的人。起初他前程似锦,但好机会都被他错过了,因此,他时常生活艰难,偶尔也有境况很好的时候,最后,他因为嗜酒而亡,这些都是我所发现的。”
我忍不住从椅子上跳起身来,心中充满酸楚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说:“伙计,你这就不对了。我真难以相信,你居然会搞这么一套,你肯定事先查访清楚了我哥哥的悲惨经历,现在,你假装用一些玄妙的理论,推断出这些真实情况。你想,我会相信你是从这块老表上发现这些真实情况的吗?”
福尔摩斯温和地说:“医生,亲爱的,对不起。我根据侦探学理论来冷静地推断这个问题,却忘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保证,在你让我观察这块表之前,我并不清楚你还有一个哥哥。”
“但你如何这样奇妙地推断出这些真实情况的呢?你所说的,都与真实情况相吻合。”
福尔摩斯说:“这算是侥幸,我仅仅说出一些极为可能的情形,并没有料到会如此精确。”
“那么,你并不是猜想出来的?”我问道。
“是的,是的,我从来不猜想。猜想的习惯很不好,它有害于精密逻辑的推理。你之所以感到离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思维路线,没有注意到可以推断出大事来的那些似乎属于细节的问题。举例来说,我曾说你哥哥的行为放荡。请看这块表,不仅仅下面边缘上有两处凹痕,整块表的上面还有无数的伤痕,这是因为你哥哥习惯把表放在有钥匙、钱币等硬物的口袋里。对一块价值50多英镑的表这样漠不关心,说你哥的行为放荡,并不算太过分吧!还有,这块表应该很值钱,如果说遗产不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我点头,表示领会了我伙伴的理由。
他继续分析:“伦敦当票的惯例是:每收到一块表,肯定要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表的里边,这个方法比挂一个牌子要好,能够免除号码丢失或被搞错的危险。我用放大镜仔细看表里面,发现至少有四个这类号码。主要的结论是:你哥经常经济拮据;附带的结论则是:他有时境况不错,要不然,他就不会有钱去赎回表来了。最后,请你注意有钥匙孔的里盖,围绕钥匙孔有不少伤痕,这是因为长期被钥匙摩擦而形成的。清醒的人插钥匙,一插就进去。而醉鬼的表,没有不留下伤痕的。你哥经常在夜里上弦,因此表上留下了手腕颤抖的痕迹。这没有任何玄妙。”
我说:“一旦说破,如见青天白日。我刚才冒犯了你,请你原谅。对你极其神妙的推断能力,我应该有更大的信心才对。请问,你如今手中有没有要侦查的案件?”
“没有。因此,我才注射可卡因提神。脑筋不动,我就几乎活不下去。除了这个,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呢?请陪我站到窗前。看啊,难道有过如此凄凉而又无聊的世界吗?那黄雾沿街滚滚而来,擦着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还有再比这个更平淡无聊的景象吗?医生,如果英雄无用武之地,劲头十足又有什么用?犯罪是平平常常的事,生活也是平平常常的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平平常常的事,还有什么呢?”
我正要开口对答我的伙伴那一番激烈的言辞,突然响起紧急的敲门声。房东太太走进来,托着一只铜盘,上边放着一张名片。
她对福尔摩斯说:“一位妙龄女郎找你。”
我的伙伴读着名片:“玛丽·莫斯坦小姐。哦!这个名字很生疏呢!荷得森太太,请她进来吧!医生,你别走,我希望你留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