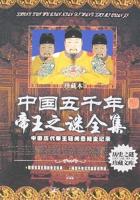十分遗憾,伊·伊·扬茹尔的《回忆录》是在上述情景的见证人均已亡故、它的准确性无从查考的时候发表的。《回忆录》的作者与我丈夫的第二次相逢也同样使我觉得奇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少去剧院,即使去,也总是和我在一起(而我不记得有这么一次会面);而且,我丈夫未必会认出伊·伊·扬茹尔教授,因为他完全记不得人,特别是他只见过一次的人。
在1901年(3月)的《历史导报》上发表了圣彼得堡神学院一个学生的回忆录[25],其中每句话都是捏造的。他描述在耶稣受难节耶稣受难节,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纪念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译者注,教徒们抬着圣像举行巡列仪时他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我可以证明,所有在受难节周和复活节周举行的重要的祈祷仪式都是我和丈夫一起去参加的(我担心他会由于屋里拥挤、空气憋闷而发病),而我们经常的去处是兹纳缅斯克教堂中右侧的副祭坛,最后三年则是弗拉基米尔教堂。我丈夫生前最后几年很注意保重身体,提防得感冒;而我们的住所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有五俄里光景,春天,当涅瓦河上流动着涅瓦河和拉多加湖上的冰块、散发出寒气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想到去那个修道院的。
回忆录的作者说,他来访时在我丈夫的书房角落里看到普希金的一个胸像,其实,这个像是不存在的,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的胸像。
此外,这位写回忆录的人不可能在圣灵教堂吻别死者;因为棺材没有打开,连亲人也无法这样做;为了埋葬时方便,盖子只是稍稍抬起一点。总之,我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写回忆录的人梦见的,而他却把梦境当作了现实,把它写进回忆录了。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这位写回忆录的人;因为他没有像不久以前“回忆录的作者”尼·尼·菲尔索夫所做的那样,在1914年(6月号)的《历史通报》上发表的题为《回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的进步活动家》[26]一文中,把一些恶劣的习气硬加在我丈夫身上。此文的作者在他逗留旧鲁萨期间曾见到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据他说,我丈夫每天晚上都要听乐队演奏,一边沉思默想,一边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在军乐队周围踱步,在音乐的影响下,考虑自己的作品;这样,他一回到家里,就立即重新在房间里来回走,一面口述数页自己的长篇小说。但是最奇怪的是,回忆录的作者在1858或1859年在莫斯科于诗人普列谢耶夫家初次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可能三十七至三十八岁)也是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暗示戴脚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管怎么说,这是捏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步行,而且能够步行很久,但是从来不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路,而是脚步匀称,这是他服兵役时留下的习惯。上文的作者不注意自己描述的不合理:只有足部有病的人才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行走,而这样的病人宁愿坐在位子上,而不会经常踱步的。在旧鲁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也不参加音乐会,而经常去阅览室看报,或者上矿泉公园散步,始终远离人群。在旧鲁萨没有军乐队,而有一个十至十二人的弦乐队,它的演奏不大可能激发人的灵感。何况当着听众的面,在乐队周围踱步很不雅观,而我的丈夫是从来也不愿把自己置于可笑的地位的。我问自己,为什么写回忆录的人要编造这样的谣言,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牵扯上?[……]
注释:
[1]这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的弗·索洛维约夫的演讲会于1878年3月10日举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曾在前文中引用斯特拉霍夫的话,说托尔斯泰本人请求斯特拉霍夫不要向他介绍任何人。(参阅本书页326)此处与前文中的说法有出入,这也许可用下述原因说明:斯特拉霍夫出于妒忌,自己不愿意介绍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因为他那时对自己的“朋友”怀有恶感,但同时又试图在表面上保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真诚、友好的关系;斯特拉霍夫这种不体面的两面派行为在他1883年11月28日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暴露无遗。(参阅本章第二节——《给斯特拉霍夫的答复》)
[2]根据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89年2月25日给她的儿子费·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参阅Л。兰斯基《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手稿集》,《文化遗迹。新的发现》,1976年年鉴,莫斯科,1977年,页74),这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列·尼·托尔斯泰的会见是在1899年2月进行的。
[3]斯特拉霍夫1883年11月28日给托尔斯泰的信还发表在《列·尼·托尔斯泰和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的第2卷中,圣彼得堡,1914年,页307—310。
[4]此处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和札记》。这本《传记》是奥·费·米勒和尼·尼·斯特拉霍夫应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请求编写的。关于奥·费·米勒和尼·尼·斯特拉霍夫编写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传记》的情况可参阅他们与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往来的书信。(С。Β。别洛夫出版,《贝加尔》,1976年,第5期,页138—140)
[5]指《在吉洪家》一章,这章写斯塔夫罗金的自白和他那真诚忏悔、自我净化的失败企图。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构思,这一章应该放在《伊万王子》一章后面,而且已经付排,但是《俄国导报》的总编米·卡特科夫不同意把它发表。
[6]此处究竟指新教神学家普雷桑塞的哪一部著作,不详。据悉,托尔斯泰有他的以下两部著作:《基督教会最初三世纪史》(1856—1859)以及《耶稣基督,他的时代及生平》(1865)。
[7]指马可·奥勒留的哲学名著《自省录》的巴黎版:《马可·奥勒留皇帝的自省录。若利译自希腊文》,巴黎,1803年。
[8]参阅托尔斯泰1883年12月5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63卷,莫斯科,1934年,页142)这封信的准确原文最初见于Н。Н。古谢夫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传记材料》,莫斯科,1970年,页221。
[9]参阅《列·尼·托尔斯泰和尼·尼·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310。
[10]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中短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概述》,德·瓦·阿韦尔基耶夫编,圣彼得堡,188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中短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活动概述》,康·康·斯卢切夫斯基编,圣彼得堡,1888年。关于斯卢切夫斯基的《概述》,可参阅T.Π。马祖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卢切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集》,第3卷,列宁格勒,1978年,页209—217。
[11]1863年,《当代》杂志4月号出版后,由于该杂志发表了署名“罗斯基”的《决定性的问题》一文(出自尼·尼·斯特拉霍夫的手笔)而被最高当局勒令停刊。这篇文章涉及波兰问题,是用官方的爱国主义精神加以探讨的;然而文章却受到曲解,被人认为是对波兰文化的推崇而有损于俄罗斯民族。(参阅Α。С。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受检查的经过》,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汇编》,第2卷,页423—430)还可参阅Β。С。涅恰耶娃著《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当代〉》,莫斯科,1972年。
[12]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这一章中所引的1877年的《作家日记》可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
[13]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4月9日致赫·丹·阿尔切夫斯卡娅赫里斯季安娜·丹尼洛芙娜·阿尔切夫斯卡娅(1841—1920),乌克兰女启蒙教育家。——译者注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206。
[14]《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84。
[15]原稿中没有号中的这段引文;但是,根据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引用的是《屠格涅夫的第一本书信集》这一点来看(虽然她提到的出版年份不确切,应该是1884年,而不是1885年),首先,根据引文的涵义来看,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没有写全的正是屠格涅夫1877年3月28日(公历4月9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中的这段话。
[16]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卷集》,第10卷,页447。
[17]这件事也可能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虚构,借以“逗弄”屠格涅夫的。至少,И。И。亚辛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十分肯定地写道,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屠格涅夫那儿,向他坦白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唉,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我来找您,为的是要您以崇高的道德观来衡量我卑下的程度!”可是,当屠格涅夫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而气愤的时候,后者却在临走之际说,“这都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这完全是出于对您的爱。我想逗您乐一下。”根据И。И。亚辛斯基的说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后,屠格涅夫同意此一说法:这件事完全是由作家虚构的。(参阅И。И。亚辛斯基《我的生活的长篇小说。回忆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页168—169)索·瓦·科瓦列夫斯卡娅证明,还在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构思了类似的情节。(参阅索·瓦·科瓦列夫斯卡娅《回忆录与书信》,页107)安·帕·菲洛索福娃的孙女З。Α。特鲁别茨卡娅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底在安·帕·菲洛索福娃的沙龙里的叙述:“‘最令人震惊、最可怕的罪恶是强奸幼女。剥夺人的生命是可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但是使人对爱情的美失去信心是更可怕的罪行。’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叙述他童年时代的一件事。‘在我童年时,我父亲曾在莫斯科一所给穷人治病的医院里当医生,我就住在这所医院里,常和一个小姑娘(车夫或厨师的女儿)玩耍。这是个约莫九岁的柔弱、优美的孩子。当她看到一朵花从石头中间钻出来的时候,总是说:“瞧,多美、多好的花啊!”可是有个喝醉酒的坏蛋强奸了这个小姑娘,她就此流血而死。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被打发到医院的另一所侧屋去找父亲,父亲奔了来,可是为时已晚。这件事作为无法饶恕的滔天罪行终身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就以这最可怕的罪行来处决《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З。Α。特鲁别茨卡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帕·菲洛索福娃》,出版者:С。Β。别洛夫,《俄国文学》,1973年,第3期,页117)Β。Н。扎哈罗夫在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问题》一书中就斯特拉霍夫这一诽谤事件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有力的驳斥。(彼得罗扎沃茨克,1978年,页75—109)
[18]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8月16日(公历8月2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在这封信中,作家叙述了他在德国与某个俄国人相会的情况:此人在国外定居,憎恨俄国,只是为了收取领地上的进款才回国来。(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8)但是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根据什么理由认为陀氏此处指的就是帕·亚·维斯科瓦托夫教授,不详。
[19]根据列·尼·托尔斯泰1881年2月初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和他发生过直接的关系;可是突然间,他去世了,我这才明白,他是我最亲近、宝贵和需要的人。[……]我失去了一个支柱。我惘然若失,后来意识到他对我来说是如何珍贵,我就不禁哭泣起来,此刻也在哭。”(《托尔斯泰全集》,第63卷,莫斯科,1934年,页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