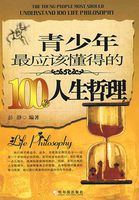[3]对招魂术的兴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瓦格纳接近的主要原因,后者为降神术和招魂术的热烈宣传者,曾在《欧洲导报》(1875年,第4期)和《俄国导报》(1875年,第10期)上发表过卫护降神术和招魂术的文章,轰动一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人士开始迷恋招魂术。经常有一些降神者,主要是英国人,来到彼得堡,举办招魂会,招魂会的参加者中间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布特列罗夫、博博雷金、Α。Н。阿克萨科夫、瓦格纳、列斯科夫。(参阅Н。莱纳《神秘的结。陀思妥耶夫斯基碰到的一件事》,收入文艺集《红色全景》,1928年,10月号,页36—42)这种迷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彼得堡大学的物理协会建立了一个以德·伊·门捷列夫为首的小组,以便对招魂术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新时报》的信——《关于第四维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10—11)正是在这个时期写的,此信也证明作家对招魂术的兴趣。(参阅Β。И。普里贝特科娃《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字形谜》,1885年,第25期,页230—232;第26期,页240—245)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在1876年《作家日记》中有关招魂术的三篇短文证明他对招魂术的兴趣逐渐冷淡。在最后一篇短文《三言两语再说招魂术》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提到尼·彼·瓦格纳的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274—275)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彼·瓦格纳相识于1876年的说法不确。实际上,他们是在1875年夏相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尼·彼·瓦格纳的五封信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五封信没有收入由Α。С。多利宁编的四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而首先发表于捷克斯洛伐克,由捷克文学研究家Φ。考乌特曼收入《布拉格人民博物馆文集》(1962),后来才在苏联发表。(参阅С。Β。别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苏联档案》,1969年,第2期)还有一封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尼·彼·瓦格纳的信,发信的日期与上述五封信接近,也没有收入四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由Φ。考乌特曼发表于捷克杂志《文学档案》,1967年,第2期,并由С。Β。别洛夫发表于《文学问题》,1967年,第5期。还可参阅尼·彼·瓦格纳1877年10月9日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由И。沃尔金发表于《读者给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一文中,《文学问题》,1971年,第9期,页190—191。
[4]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明了法庭辩论的时间——从晚上八时检察官开始讲话到午夜一时陪审员们离开为止。
[5]《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页253。
[6]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屠格涅夫借钱一事,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此处的叙述不确。1865年8月3日(公历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威斯巴登写信给屠格涅夫,请求后者赶快借给他一百塔列尔,而不像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写的那样,是五十塔列尔。(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410)不过,屠格涅夫寄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五十塔列尔,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8月20日发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410)
[7]亚·费·奥涅金1883年(不是1888年)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由Л。兰斯基发表在《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手稿集》一文中,该文收入《文化遗迹。新的发现》一书,1976年年鉴,莫斯科,1977年,页71。
[8]指《作家日记》。
[9]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把年份记错了。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格里布死于1876年1月1日;因此,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后文谈到的购买旧鲁萨的别墅一事不是发生在1877年,而是在1876年。(参阅Л。М。赖因努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页35;Л。Π。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页248)
[10]指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
[11]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7月20日至21日的达罗沃耶之行,请参阅Д。斯通诺夫《达罗沃耶村》一文中达罗沃耶农民И。马卡罗夫的回忆,载《红色田地》,1926年,第16期;Β。С。涅恰耶娃,《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达罗沃耶之行)》,《新世界》,1926年,第3期。
[12]符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在其所写的《回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叙述了他陪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访问女占卦者的情况。(参阅《历史导报》,1881年,第4期,页849)
[13]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吸引了俄国人士对所谓东方问题或者斯拉夫人问题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他所发挥的“根基论”思想来探讨“东方问题”,他认为俄国的参战是实现俄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的开端,俄国人民将在基督教博爱的基础上把人类,首先是斯拉夫人团结起来。(参阅《作家日记》,1876年,第6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316—333)
[14]长诗《不幸的人们》不是像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写的那样属于涅克拉索夫最后创作的诗歌。它发表在《现代人》1856年第5期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回忆他和涅克拉索夫的会见时,写道:“我从服苦役回来时,他(涅克拉索夫)指着他书中的一首诗说,‘我当时写的就是您。’”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可能正是这首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33)
[15]涅克拉索夫的妹妹Α。布特克维奇在她的日记中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7年3月23日与大诗人会见时的情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了。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把我哥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同龄人),他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能说话,但是请告诉他,请他进来一会儿,我很高兴看到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儿坐了不长时间。他告诉我哥哥,他今天在狱中的囚犯那儿看到《彼得堡风貌》,觉得很惊奇。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脸色十分苍白,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就探问他的健康情况。‘情况不妙,’他回答,‘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这个月里已经发了五次。最后一次是在五天以前发作的,直到现在头脑还有点糊涂。我今天老想笑,你们可别感到奇怪:这是一种神经质的笑,我在发病过后经常是这样的。’”(《同时代人回忆涅克拉索夫》,莫斯科,1971年,页441)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1877年的《作家日己》中提到过他在1877年11月下旬和涅克拉索夫的会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436)
[16]在大多数彼得堡的报纸所刊载的有关涅克拉索夫逝世的文章中所写的与其说是涅克拉索夫的诗歌的意义,不如说是他的“实用主义”、“缺陷”和二重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上发表的论涅克拉索夫的文章,正如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说的,“是对涅克拉索夫这个人的最出色的辩护词”。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涅克拉索夫是俄国的一个历史性的典型,是一个重要的例证,说明在我们这个可悲的转折时期,一个俄国人在精神领域和信仰领域会达到何等矛盾、何等两重化的程度。但是这个人始终留在我们心里。这位诗人的激情经常是真挚、纯洁和淳朴的!他对人民的向往是多么高尚,这使他,作为一个诗人,处于崇高的地位。至于作为人,作为公民,他又以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证明自己是无可指摘的,而且弥补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如果真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363)像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斯卡比切夫斯基这样一些《祖国纪事》的主要撰稿人正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涅克拉索夫的发言看成“辩护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涅克拉索夫的发言对同时代人产生的印象可参阅以下回忆录:Α。Α。普列谢耶夫,《涅克拉索夫三十周年忌辰》,《彼得堡报》,1907年,第355号,12月27日;格·瓦·普列汉诺夫,《文学和美学》,第2卷,莫斯科,1958年,页206—209;弗·加·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莫斯科,1965年,页429—431。还可参阅Β。Α。图尼马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时代》,列宁格勒,1971年,页3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