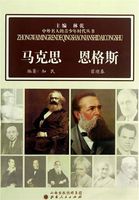起初我允许债主们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判。但是这些谈判的结果很糟:债主们对我丈夫说话放肆,威胁他要没收家具,把他送到债户拘留所。经过这样的谈话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陷于绝望,接连几个钟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揪着自己鬓角上的头发(当他十分激动时通常就是这副样子),嘴里反反复复地说:“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到了第二天,他的癲痫病就又犯了。
我非常怜惜我那不幸的丈夫,于是我便瞒着他,决定自己单独挑起与债主们谈判的担子。在这个时期里,先后来过我家的是些多么奇怪的角色啊!他们大多是期票的转售者——官员的寡妇、出租带家具的住房的女房东、退职的军官、低级代理人。他们大家都花了很少的钱买进期票,但是却想拿到足数的钱。他们以查抄财产和送债户拘留所来威胁我,但我已经知道怎样跟他们周旋。我的论据和我跟京特尔施泰因交涉时的论据完全一样。债主们看到威胁无效,便软了下来,于是我就跟他们分别订立契约以代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期票。但是我要在指定的日期支付我答应的钱款,那是多么艰难啊!我得绞尽脑汁,想出种种办法:向亲戚们借债,把东西押出去,让自己和全家放弃必不可少的需求。
我们不是按时可以拿到钱的,这完全取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工作是否顺利。我们不能不拖欠房租,向商店赊账,因此我拿到钱——一下子四五百卢布(我丈夫总是交给我的),可第二天却往往只剩下二十五或三十卢布了。
有时候,债主们找上门来,不能不让我的丈夫察觉。他追问我,来者是谁,有什么事,他看到我不愿意讲,就责怪我瞒着他。这种抱怨也反映在他的某些书信中。但我不可能事事都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说。为了工作顺利,他需要安静。不痛快的事会诱发癫痫病,使他的工作受到影响。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一切使他不安和难过的事瞒着他,甚至不惜让他感觉到,我似乎对他不坦率。干这一切有多么艰难啊!可是这样的生活我却过了差不多十三年!
想起我丈夫的亲戚们那些毫不客气的请求,我心里也感到不好受。不管我们的手头如何拮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拒绝帮助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继子,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帮助其他的亲戚。除了规定的金额(每月五十卢布)外,科利亚尼古拉的爱称。——译者注弟弟每次到我们家来总会拿到五个卢布。[10]他是个温良、可怜的人,我喜欢他心肠好,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但是当他在祝贺孩子们的生日或命名日,担心我们的健康等等各种借口下来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还是会生他的气。这倒不是出于吝啬,而是由于家里只剩下二十卢布,准备明天付给某个人,他一来,我就又得去抵押东西了。
特别使我冒火的是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他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而且深信,他有权提出要求。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要拿到数额大的稿费,每次总要给继子不少钱;但是后者经常有急需,每每来找继父要钱,虽然他很清楚,我们的物质生活过得相当窘迫。
“呶,爸爸怎么样?身体好吗?”他一进门就问,“我一定要跟他谈一谈:我急需四十卢布。”
“您要知道,卡特科夫还一个钱都没捎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钱,”我回答,“今天我把别针抵押掉,拿到二十五卢布。您瞧,这是收据!”
“那怎么办呢?请您再抵押掉什么东西吧。”
“可我什么都抵押掉了。”
“我需要这笔钱花,”继子坚持道。
“等我们拿到了钱,您再花吧。”
“我不能延期。”
“可我没钱啊!!”
“这我不管!您想办法上哪儿去弄吧。”
我开始劝说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请求他别向继父要四十卢布,因为我没有那些钱;而是要十五卢布,给我留下五卢布明天供家用。经过长时间的恳求,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让步了,显然,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帮了我的大忙。我拿出十五卢布,让丈夫交给继子,心里忧伤地想,我们本来可以用这点钱过两三天太平日子,这样一来,明天就又得抵押掉什么东西了。我不能忘记,这个无礼的继子给我造成多少痛苦和麻烦!
也许,多有人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不拒绝这种索钱的无理要求。然而,我要是和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发生口角,那他就会立即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儿去告我的状,就会歪曲事实,显得非常委屈,这样就会发生争吵,搞得我丈夫苦恼不堪。为了让他精神上保持平静,我宁愿自己忍让,放弃自己的一切需要,只求我们的家庭和睦安定。
五
尽管苦于债主们的纠缠和经常性的穷困,当我回忆起1871年冬至1872年春那个时期的生活,我还是感到愉快。我们又到了祖国,处在俄国人和所有俄国的事物中间,对我来说,单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幸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自己能够回国也感到高兴,回来以后,他就可以与朋友们会面,主要的是可以观察当前的俄国生活,他觉得自己已经有点与之疏远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恢复了与先前许多朋友的来往,而在他的亲戚米·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教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弗拉季斯拉夫列夫(1840—1890),哲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那儿,他有机会碰到许多学术界的人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喜欢与其中的一位学者——瓦·瓦·格里戈里耶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戈里耶夫(1816—1881),东方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政论家。交谈。[11]他还在《公民周报》的发行者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梅谢尔斯基(1839—1914),作家,政论家,1872年起发行《公民周报》。[12]那儿认识了捷·伊·菲利波夫[13]和每星期三在梅谢尔斯基家聚餐的全体人员。就在这儿,他碰到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后来他与后者交往甚密,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14]
我记得,这一年冬天,经常住在克里木的尼·雅·丹尼列夫斯基来到了彼得堡,还在青年时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知道他是傅立叶学说的狂热的追随者,对他的《俄国和欧洲》一书十分推崇,很想恢复与他的旧交。[15]他邀请丹尼列夫斯基到我们家吃饭,除了他以外,还有几位聪明、有才能的人物在座(我记得有迈科夫、拉曼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拉曼斯基(1833—1914),斯拉夫派历史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斯特拉霍夫)。他们一直谈到深夜。
此年冬,莫斯科著名的美术馆的创立者帕·米·特列嘉柯夫请求我丈夫允许美术馆请人替他画一张像。[16]为此目的,著名画家瓦·格·别洛夫特地从莫斯科赶来。在动手画像以前,别洛夫连续一星期每天来访问我们;画家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不同的各种场合碰到他,跟他谈话,挑起争论,得以察觉我丈夫脸上最富有特征的表情,那就是,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沉浸在自己的艺术思维时他那特有的神态。可以说,别洛夫在肖像画中抓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瞬间”。我曾多次发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脸上的这种表情,有时候,我走进他的房间,看到他仿佛在“朝着自己望”,于是我就一句话也不说,退了出来。后来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正在聚精会神地思索,根本没有察觉我进去,而且不相信我去过。
别洛夫是个聪明而和善的人,我的丈夫喜欢跟他聊天。[17]他每次来的时候,我总在场,他在我的回忆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冬季很快过去,1872年的春天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不幸和灾难,留下了长久难以忘怀的后果。
六一八七二年。夏季我不得不十分详细地叙述我们在1872年夏所遭到的灾难,这主要是为了要使读者了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时期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俗语说:“祸不单行”,几乎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接二连三地碰到各种意外的不幸和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幸是从1871年底开始的,当时我们的女儿莉利亚(她当时两岁半)在房间里奔跑,我们眼看她绊了一下,跌倒了。她拼命哭叫起来,我们急忙冲过去,把她抱起来,哄她,但她还是哭个不停,并且不准别人碰她的右手。这使我们意识到,她跌得不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姆和女仆赶紧去请医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一家药房里打听到住在附近的外科医生的地址,过了半小时就把他请了来。几乎在同时,保姆带来另一位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外科医生检查了那只受伤的手,认为是关节脱臼,他就使脱位了的关节复了位,然后给小手扎好绷带,绑上厚厚的纸夹板。第二位医生同意外科医生的诊断,并且肯定地说,既然骨头已经复位,那它很快就会愈合。两位内行的医生的诊断使我们安了心。我们请外科医生上门出诊,他在两个星期里每天早晨到我们家来。他解开绷带,总是说,情况发展正常。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指给外科医生看,在手掌上方三俄寸俄国旧长度单位,1俄寸等于4.45厘米。——译者注的地方,有个凸出的地方,呈紫红色。外科医生断言,病人的整只手都是肿的,这是脱臼时一般的出血现象,肿会逐渐消退的。由于我们即将启程去外地,外科医生向我们建议:为了路上安全起见,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不要解开手上的绷带。我们对这次不幸的事件就不再担心,于1872年5月15日前往旧鲁萨旧鲁萨,苏联诺夫哥罗德州的城市,矿泉泥疗疗养地…
我们接受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亲侄女玛丽娅·米哈伊洛芙娜玛丽娅·米哈伊洛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43—1888),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的丈夫——米·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教授的建议,选择了这个疗养地作为我们度夏之处。他们夫妇俩都肯定地说,住在旧鲁萨既安宁,物价又便宜,他们的孩子们由于去年夏天在那里洗了海水浴,身体健康多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想把他们带到旧鲁萨去,使他们有洗海水浴的机会。
我们第一次到旧鲁萨去旅游,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是我们家庭生活中愉快的回忆之一。[18]虽然1871年冬至1872年春我们的生活过得安宁、有趣,但是从大斋期开始,我们就想望在早春时离开这儿远一点,到某个偏僻的地方去,那儿既可以工作,又可以待在一起,不像在彼得堡那样,生活在众人中间,而是像我和丈夫在国外习以为常的那样,两人作伴,感到心满意足。现在我们如愿以偿了。
我们在一个晴朗、暖和的早晨出发,过了约莫四个钟头,抵达索斯尼克站,从那儿乘轮船沿着沃尔霍夫河到诺夫哥罗德。在车站上,我们得知轮船已于夜间一时驶走,我们不得不在这儿等待整整一天。我们临时住在旅店里,由于屋子里很闷,我们就和孩子们及老保姆在村子里转悠。这时候我们碰到一件滑稽的事情:还没有走完半条街,就看到一个农妇带着一个脸上布满红斑点和水泡的孩子。我们朝前走去,又看到三四个脸上同样有着红斑点和水泡的孩子。这使我们惶惶不安,怀疑村子里有人出天花,担心我们的孩子们会受到传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赶紧下令回家,并问女房东,村里是否有流行病,为什么孩子们的脸上有红斑点。这位农妇听了甚至有点生气,回答说,他们那儿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什么“病痛”,这都是“给蚊子叮的”。关于天花一事,我们很快就释疑了。过了不到一个钟点,我们便确信,这实际上是“蚊子”搞出来的,因为我们孩子们的脸上和手上都被这儿的蚊子咬得伤痕累累了。
我们在半夜乘上轮船,安排好孩子们睡觉,自己则在甲板上坐到深夜三点钟,欣赏着沃尔霍夫河以及河两岸刚刚长出叶子的树木。黎明前寒气袭人,我走进船舱,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一直坐在露天里:他是多么喜爱白夜啊!
早晨六点钟左右,我感到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坐起来,听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说:“安尼娅,到甲板上去,瞧瞧景色有多美!”
确实,那景色真美,叫人简直忘记睡觉。当我后来记起诺夫哥罗德时,这景色总是历历在目。
这是个绝妙的春晨,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河流的对岸,那儿耸立着内城带雉堞的城墙,索非亚大教堂的金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寒冷的空间,响起了召唤人们去做早祷的洪亮钟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爱并且理解大自然,他此刻心醉神迷,我不由自主地受他这种情绪的感染。我们久久地并肩坐着,不发一言,仿佛害怕破坏大自然的魅力似的。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始终保持着这种愉快的情绪,——我们的心灵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轻松,这样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