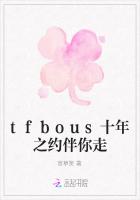一回到祖国
1871年7月8日,在一个晴朗、炎热的日子,我们在国外居住了四年之后,回到彼得堡。
我们从华沙车站经过伊斯梅洛夫大街上我们曾在那儿举行婚礼的圣三一大教堂。我和丈夫对着教堂画十字;我们的小女孩望着我们,也在自己身上画十字。
“我说,安涅奇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口道,“我们在国外这四年过得挺幸福,虽然有时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在彼得堡的生活将会怎样呢?未来的一切就像在雾中……我预料,我们要经历无数的艰难和忧虑才能站住脚。我只能指望上帝保佑我们!”
“你何必事先就担起心来,”我竭力安慰他,“上帝肯定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主要的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实现了,我和你重又回到了祖国。”
我们在大孔纽申街的一个旅馆里住下,但总共只住了两天;因为家里即将增添人口,住在旅馆里很不方便,而且经济上也负担不起。我们在叶卡杰琳戈夫大街三号一所房子的三层楼上租了两间带家具的房间。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女孩子可以在附近的尤苏普公园度过炎热的七月和八月。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亲戚们在我们回国以后的头几天来探望我们,我们对待他们都很亲切。在这四年里,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的境况有了好转,她的大儿子,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成了优秀的音乐家,他教授钢琴,收益颇丰。次子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银行里供职。她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也有了教速记学的工作,因此,一家的生活过得相当宽裕。况且在这段时期里,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想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了家室,只有在她碰到急事时才能支援她。
只有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一个人怎么也不能放弃原先的想法:“父亲”(他硬是这样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义务养活他,不仅他,而且他的家庭。但是对他,我也殷勤接待,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妻子娜杰日达·米哈伊洛芙娜。他是这一年4月才跟她结婚的。她长得美,个子不高,朴实无华而又相当聪明。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她怎么会下决心嫁给像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这样令人难以容忍的人。我真诚地为她惋惜:我预料,她的生活将会十分艰辛。
我们抵达彼得堡以后八天,7月16日清晨,我们的大儿子费奥多尔出生了。[1]分娩的前一天,我感到不舒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祷告了整整一昼夜,祈求上帝保佑我分娩顺利,他后来对我说,如果生下的是个儿子,那么,即使在午夜以前十分钟生的,他也要给儿子取名为弗拉基米尔,这是功德不下于圣徒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指公元十世纪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他接受东正教,宣布东正教为罗斯国教,教会则确认其政权是神授的。——译者注的名字,这位大公的纪念日是7月15日。但是结果孩子是在16日生下的,为了让他记住自己的父亲,我们就给他取名费奥多尔,这是我们早就决定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幸福之极,因为生了个男孩,同时,他为之焦虑不安的家庭“大事”终于顺利地过去了。
当我们的男孩受洗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复原了。和我们的女儿一样,他的教父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朋友、著名诗人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选定自己的女儿柳鲍奇卡做他的教母,而她还不满两岁呢。
8月底,我丈夫去莫斯科向《俄国导报》领取187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群魔》的部分稿酬。[2]这笔钱数目并不很大,但还是使我们有可能从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搬到过冬的住所。我们的主要困难是没有一件家具。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到阿普拉克辛市场,问问那边的家具商,他们是否同意让我们用分期付款——每月付二十五卢布的办法向他们购买家具,在全部货款尚未付清以前,家具仍归卖主所有。我们碰到了一个同意这些条件的商人,他一下子就供应我们价值四百卢布的家具。但是这都是些什么货色啊!家具虽然是新的,但全是赤杨木和松木做的,不用说式样难看,做工也很拙劣,以致三年以后,全部脱胶、散架,不得不换一套新的。但是我拿到这样的家具还是高兴的:我们就此可以安排自己的住所。继续住在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各种各样的不便外,幼小的孩子们待的地方紧邻我丈夫的居室,他们的哭叫声妨碍我丈夫睡觉和工作。
家具问题解决以后,我就着手找房子。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表示愿意帮我的忙。就在当天晚上,他宣称已经找到一套包括八个房间的住所,租金低廉,——每月一百卢布。
“我们要这样大的住房干什么?”我惊奇地问。
“这住房根本不大:你们需要客厅、书房、卧室、儿童室;我们呢,——客厅、书房、卧室,饭厅可以合用。”
“您难道打算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对他的厚颜无耻感到惊讶。
“要不然,怎么办呢?我已经对妻子说过:父亲回来以后,我们就搬到一起住。”
到了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跟他严肃地谈一谈,说明现在情况有了改变,我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跟他住在一起。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照例出言不逊,他威胁说,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儿去告状,但是他的话我连听也不听。对我来说,四年的独立生活不是白白过去的。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把他的威胁付诸行动,去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求助,但他听到的回答是:“所有的家务事我都听任妻子处理,她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计划破了产,为此,他很久不能原谅我。
经过长久的寻找以后,我终于在谢尔普霍夫斯基大街上,靠近工艺学院,在阿尔汉格尔斯基的房子里,觅得一套住房,用我的名义把它租了下来,为的是使丈夫摆脱家务事的麻烦。这套住房有四间屋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儿工作和睡觉的书房、客厅、饭厅和一间大的儿童室,我就住在那里。
虽然我们的家具简陋,但是我安慰自己,我们不用购置家用什物和御寒物品了,因为我们过去曾将它们分托几个人保管。但是,真糟糕,在这件事上,我们也不走运。
餐具、铜器和厨房用具交给我们房子里一位熟悉的老小姐保管。她在我们出门期间去世了,她的姐妹把她的全部遗物,不管是她的还是别人的,一概都带到外省去了。我们曾将我们的皮大衣抵押出去,委托一位太太支付利息,虽然我们为此按时把钱寄去,但她却逾期未付。玻璃器皿和瓷器放在我姐姐玛丽娅·格里戈利耶芙娜那儿,她将它们交给女仆去涮洗,不料女仆脚下一滑,装瓷器的托盘掉在地上,东西就此打碎。最后的一项损失使我特别难受:我父亲是鉴赏瓷器的行家,他喜欢到古董商那儿去走动,买到很多漂亮东西。他过世后,我分得几只非常可爱的古萨克森的瓷碗,尼古拉时代的塞夫勒产的瓷器和古老的、边缘很薄的餐具。直到现在,我想到失去那些可爱的、上面绘有牧女的小碗和一只玻璃上十分生动地画着一只苍蝇的杯子还觉得心疼,凡是用这只杯子喝酒的人都把玻璃上的那只苍蝇当成活的来抓。我宁愿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童年时代的这些亲切的往事能够重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东西也遭到同样可悲的命运。他有一批很好的藏书,他在国外常常想到它们。在这批藏书中,有好多是他的那些做作家的朋友们送给他的,书上有着他们的题词;还有许多是有关历史和旧礼仪派旧礼仪派是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教派,不接受十七世纪的教会改革,是官方教会的反对派,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译者注的严肃的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它们很感兴趣。在我们出国的时候,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求我丈夫将这批藏书留给他保管,硬说藏书对他的教育有用,并答应将书籍完整地交还;但是结果呢,他因需要钱花,就把它们统统卖给旧书商了。我责备他,他用蛮横无礼的态度来回答我,并且宣称,这全是我们自己的错,怪我们没有按时寄钱给他。
丧失珍贵的藏书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难受。如今他没有条件像过去那样花费大量的钱去买他十分需要的书了。而且在他的藏书中有几册是不可能买到的珍本。[3]
寄放在我亲戚家的一只放文稿的柳条筐还在,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乐事。我仔细查看了里面的东西,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数本有关长篇小说《罪与罚》和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的笔记本,他已故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的、经办《当代》和《时代》杂志的业务记事本以及为数很多的各种信件。[4]这些文稿和文献对于我们今后的生活,当我们需要证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或者对一些有关他的生活的说法予以驳斥时,是十分有用的。
二
1871年9月,某报向读者报道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从国外回来的消息,这可给我们帮了倒忙。我们那些至今保持缄默的债主们一下子都来要债了。第一个来的是京特尔施泰因[5],他的态度咄咄逼人。此人要的债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欠下的,也与杂志的业务无关,而是他已故的哥哥的烟草工厂欠下的。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很有进取心的人,除了办杂志外,他还经营一个烟草工厂。为了大量推销烟草,他想出了在雪茄烟盒里放置奖品——剪刀、刮脸刀、铅笔刀等等的办法。这种意外的赠品吸引了许多顾客。上述的金属制品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批发商京特尔施泰因那儿买来的。后者赊销商品,收取相当高的利息。当《当代》杂志的发行情况良好的时候,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逐步还清了京特尔施泰因的债务,他认为此人是他的最苛刻的债主。在他故世前几天,他高兴地告诉妻子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终于摆脱了这个吸血鬼——京特尔施泰因”。
哥哥故世后,所有的债务都落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京特尔施泰因的太太就来找他,宣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欠她近两千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起哥哥关于欠京特尔施泰因的债务已经还清的话,就向她谈了这个情况,但她却说,这是另一笔借款,而且,她借给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时候没有拿到任何单据。她缠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他或者付给她现款,或者给她期票。她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口口声声说,她的丈夫逼得她没法儿活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相信别人是诚实的,他相信了她,交给她两张期票,每张一千卢布。第一张期票已于1867年以前付款,而第二张期票,连同五年的利息,已增至一千两百卢布,我们一回国,京特尔施泰因就立即要求付清这笔钱。他写了一封威胁性的信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去找他,请求将这笔款子推迟到新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收到长篇小说的稿费后支付。他回来的时候陷于绝望:京特尔施泰因宣称不打算再等了,并且决定查抄他的动产。如果它不足以抵偿债务,那么,京特尔施泰因就要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送交债户拘留所这个拘留所设在伊兹马伊洛夫团一连,在塔拉索夫的房子里,那儿关押着为债务而失去自由的人。——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6]。
“难道我待在债户拘留所,远离家庭,和各式各样的陌生人在一起,还能写文学作品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说,“如果您使我失去工作的条件,那我怎样来还您的钱呢?”
“哎呀,您是个有名的作家,我估计文学基金会立即会把您从拘留所里赎出来,”京特尔施泰因回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文学基金会当时的活动家们。他表示,他不相信他们会帮忙,即使他们主动提出帮助,那么(他对京特尔施泰因声明),他也宁肯坐债户拘留所,而不愿意接受这种帮助。
我和丈夫就如何比较妥当地处理这件事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向京特尔施泰因提出新的协议:现在先付给他一百卢布,并表示愿意在一个月之内再付五十卢布,过了新年把余下的部分付清。我丈夫带了这个建议第二次去找京特尔施泰因,回来的时候气愤填膺。据他说,经过长久的谈话之后,京特尔施泰因对他说:“您是有才能的俄国作家;而我只是个小小的德国商人,不过,我想让您瞧瞧,我能够把一个有名的俄国作家送进债户拘留所。请相信,我会这样做的。”
这是在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获胜的时候,德国人都变得傲慢,趾高气扬。
这样对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使我感到愤慨,但是我明白,我们落在一个坏蛋手里,没有可能摆脱他。我预料京特尔施泰因不只限于口头上的威胁,就决定亲自解决这件事,我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向我丈夫透露(他想必会阻止我的),就径自去找京特尔施泰因。
他对我态度很傲慢,并且宣称:
“把钱交来,要不,一星期后就查抄你们的财产,把它变卖,您的丈夫就得关进塔拉索夫的房子指债户拘留所。——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