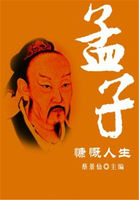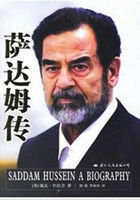[56]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9年4月18日(俄历4月6日)从佛罗伦萨寄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和补充,那封信中说:“您信中问我在读什么书。我整个冬天都在读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这当然对我有益,使我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186)正是在六十年代末,特别是由于长篇《无神论》的构思(参阅本章“注释”59),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哲学的兴趣增强,1877年12月24日,在动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前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终生需要记住的事情。一,写俄国的老实人(参阅本书页317)。看来,《俄国老实人》的未实现的构思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获得了体现。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伏尔泰的关系,请参阅Л。Π。格罗斯曼的《俄国老实人(论伏尔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欧洲导报》,1914年,第5期。还有Α。拉梅尔梅伊尔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伏尔泰》,《斯拉夫语言学杂志》,1958年,第26卷,第2册,页252—278。在这篇学术论文中,作者依据大量实际的和版本学的资料探究了伏尔泰的长篇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中反上帝的哲学对塑造伊万·卡拉马佐夫这个形象的影响。Α。С。多利宁在为上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斯特拉霍夫、告诉后者自己在读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的那封信所作的注释中指出:“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加尼亚(《白痴》中的人物)特别注意,此人的某些特征和狄德罗的主人公很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453)瓦·瓦·罗扎诺夫在论及《地下室手记》时写道:“与这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深刻的作品之一相类似的只有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瓦·瓦·罗扎诺夫,《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圣彼得堡,1906年,页31)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德罗的情况,请参阅Α。格里戈里耶夫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德罗(关于问题的提出)》,《俄国文学》,1966年,第4期,还可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佛罗伦萨阅览室的常客》,《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集》,列宁格勒,1980年,第4卷,页174—175。
[57]参阅1869年8月14日(公历8月26日)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00)
[58]这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两个人物,他们虽然负债累累,但却无忧无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0年3月25日(公历4月6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也称自己为“密考伯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62)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长篇小说《白痴》期间忆起这个形象不是偶然的:“密考伯先生”可能是塑造伊沃尔金将军这一形象的原动力。
[59]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完成长篇小说《白痴》时,于1868年在佛罗伦萨时就打算创作一部“篇幅巨大”的新的哲学小说《无神论》——写的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俄国人,他“在新一辈人中间,在无神论者中间,在斯拉夫人和欧洲人中间,在俄国狂信徒和荒漠的居民中间,在神甫们中间到处乱窜……临了,找到了基督和俄国的土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150、161、195)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无神论》的构思并没有实现,经过多次修改以后,变成了《一个大罪人的生涯》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只是在长篇小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部分地获得反映。
[60]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索·亚·赫梅罗娃(伊万诺娃)的两封不同的信看成了一封信。此处引文的第一部分——省略号以前的部分(以“直接参与俄国的生活……”结束)引自1869年3月8日(公历3月20日)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175。第二部分——省略号以后的部分(从“……而在这儿,我甚至失去了写作的可能性”开始)大体上引自1869年1月25日(公历2月6日)的信,但引文不精确。——《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161。
[61]作家的女儿——柳鲍芙·费奥多罗芙娜后来成了女小说家,是长篇小说《女律师》、《女侨民》和短篇集《病态的女孩》的作者。她于1913年出国,再也没有回国。她在国外以从事写作为生,出版了用德文写的有关她父亲的回忆录,书名为《Dostojewski,geschildert von seiner Tocher》(慕尼黑,1920年)。俄文的节译本由Α。Γ。戈尔恩费里德编辑,书名为《女儿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莫斯科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1922年)。还请参阅由С。Β。别洛夫发表的新的两章,《文学遗产》,第86卷,页297—307。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这本书不能称为准确意义上的回忆录,因为她父亲逝世时她还只有十一岁。因此,柳鲍芙·费奥多罗芙娜把她的书题名为《女儿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当回忆录的作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塑造”严格地遵照有根有据的事实、家庭传说、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她所记得的父母亲的叙述——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塑造”是可以凭信的。然而,当回忆录的作者有意识地歪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人所共知的事实时,这本书就带有作者明显的个人意图。例如,柳鲍芙·费奥多罗芙娜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和文献记录,硬说她的父亲不是俄罗斯人,而是诺曼立陶宛人。这也许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家谱”可以使他的女儿有条件说,她是世袭的贵族,这是1920年柳鲍芙·费奥多罗芙娜周围的侨民们所特别重视的。任意回避事实、明显的个人意图是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的基本缺点,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则严格地以文件和事实为基础,她的回忆录和她女儿的回忆录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关于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情况,请参阅С。Β。别洛夫的文章,载于《文学遗产》,第86卷,页291—296。
[62]引自1869年9月17日(公历29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引文与原文有出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11。
[63]引自1870年2月26日(公历3月10日)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56。
[64]此处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复述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3月25日(公历4月6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信中有以下的话:“这部长篇小说总的名称是:《一个大罪人的生涯》,但是其中每个中篇都有独立的篇名。各卷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个使我一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之苦恼的问题——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