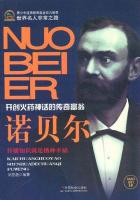[8]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读赫尔岑的作品,读了很多。他认为赫尔岑是最深沉而诚挚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赫尔岑的作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巨大的、至今还估计不足的影响,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在他1846年1月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首次提到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赫尔岑所有的作品。他把《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特别是《来自彼岸》和《法意书简》看作是他喜爱的俄国和世界文学中的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重视赫尔岑的政论作品,后者的那些有关欧洲的研究性论文和著作,就其反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对西方的主要社会和哲学问题以及社会动荡的实质的理解深度来说,和他的思想比较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赫尔岑的《自然研究通信》一书评价也很高,他认为这部著作“不仅是俄国的,而且是欧洲的哲学杰作”。(见《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页138)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赫尔岑在伦敦相会,这次会见对双方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后来,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见解有了很大改变,从而与赫尔岑在思想上的分歧趋于明显的时候,他在《老年人》中对赫尔岑作了极其主观的,但同时绝非怀有敌意的描绘,他写道:“这是位艺术家,思想家,杰出的作家,一位饱学之士,又是一位机智、绝妙的交谈者(他谈话甚至比写作更出色),同时,还是位好沉思与反省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7)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惊闻赫尔岑的女儿自杀的消息,他在谈到她的父亲时,把后者称为思想家和诗人:“请注意,这是赫尔岑的女儿,赫尔岑是一位天才横溢的人,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固然,他的生活杂乱无章,充满了矛盾和古怪的心理现象。这是俄国最激烈的西欧派分裂分子之一,但心胸开阔,具有某些完全是俄国人的性格特点。”(《文学遗产》,第86卷,页86)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赫尔岑的态度请参阅Α。С。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赫尔岑》一文,收入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怎样写成的》(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一书中,以及С。Π。利希佩尔《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探索的辩证法》,载《俄国文学》,1972年,第2期,页37—61。
[9]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指的是1873年的《作家日记》第十五章《关于假话》,这一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在我们的妇女身上越来越表现出诚实坦率、坚韧不拔、严肃认真、正直纯洁、追求真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妇女在实际上比较顽强,有耐心;她们比男子认真,愿意为事业本身切切实实地干,而不是为了装样子。我们是否真的应该从她们那儿得到巨大的帮助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129)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说,作家直到七十年代才对妇女的解放持肯定态度,这种说法不完全确切。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否定的很可能是“库克希娜”库克希娜是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人物。——译者注式的那种表面上的虚无主义,早在1868年,他就在一封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写道:“关于妇女,特别是俄国妇女的问题,甚至在你们生活的时代,一定会获得某些巨大而良好的进展。我所指的不是我们那些时机尚未成熟就轻率行动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73)
[10]德国速记术的创始人和新的速记术体系的发明者弗朗茨·克萨韦里·加别利斯别格尔认为,传达语言声音的可见的符号必须适应人的语言结构。加别利斯别格尔的学生们在他逝世后建立了“加别利斯别格尔速记术教学体系”(慕尼黑,1850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老师帕·马·奥利欣是俄国最初遵照加别利斯别格尔的原理教授速记学的教师之一,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中有他所写的课本《根据加别利斯别格尔原理编写的俄国速记学教程》(圣彼得堡,1866年,第三版)。有关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做速记员方面的情况请参阅Б。Н。卡佩柳什和Ц。М。波舍曼斯卡娅所写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速记笔记》一文,收入《文学档案》,第6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61年,页109—111。
[11]原稿此处遗漏。关于1867年6月20日在德累斯顿举行,有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出席的那次速记术团体的会议报道载于1867年6月22日的《国民报》,而不是《德累斯顿通报》。在《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一书中,有一段引自该报的摘录:“在速记学院最近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有一位俄国的女士参加,她曾按照加别利斯别格尔体系学习速记术,并在彼得堡经常运用这一体系。”(页145)
[12]此处指波兰侨民安东·别列佐夫斯基于1867年5月25日(公历6月6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行刺亚历山大二世一事。几乎所有巴黎的报刊和巴黎的律师都特意组织示威游行,高呼“波兰万岁”的口号,为安·别列佐夫斯基辩护,认为他的行刺是为他那被奴役的祖国复仇的正义之举。1867年7月3日(公历7月15日),巴黎的陪审法庭不是判处安·别列佐夫斯基死刑,而是终生服苦役。作家虽然否定死刑,但是对陪审法庭主要着眼于使罪责得以减轻的客观环境,从而为罪犯辩护的意图感到愤慨。陪审员们的立场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个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主张相抵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8月16日(公历8月2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表示自己对别列佐夫斯基的图谋以及法庭对恐怖分子的审讯过程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发生在巴黎的事件使我震惊。那些叫喊‘波兰万岁’的巴黎的律师们可真行。嘿,多么卑鄙的勾当,——主要是愚蠢,是官样文章!我也就更加确信我先前的想法:欧洲不了解我们,把我们看得十分可恶,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对我们有利。而对别列佐夫斯基审讯的详情细节[……]多么卑鄙的官样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7)
[13]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政论家,在《作家日记》中确实不止一次地主张人民和“沙皇—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联合。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总是把亚历山大二世理想化。“我跟普希金一样是沙皇的仆人,因为沙皇的儿女,他的人民,并不嫌弃沙皇的仆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将更加忠实地做他的仆人,如果他真正相信人民是他的儿女。不知为什么,他已经很久不相信这一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和札记》,页366)
[14]根据最高军事法院院长1849年11月19日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案所作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剥夺财产权,到了1858年4月17日,亦即亚历山大二世已经登位之后,遵照参政院的最高指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贵族身份得以恢复。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下子获准住在彼得堡的,起初,从1859年8月到12月,他住在特维尔,直到1859年12月2日才经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在警察机关秘密监视下回到彼得堡居住。
[15]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11—20。
[16]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日记》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7年5月2日前往戈姆堡,答应四天以后回来,但一直在那儿逗留到5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一八六七年日记》,页46、86)
[17]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27—33。
[18]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态度时,她所依据的材料大概来自她与丈夫的谈话和1873年《作家日记》中《故人》一文(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1871年5月18日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前者在信中断言,“别林斯基用粗野难听的话谩骂……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364)。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问题上很可能有过原则性的冲突,但这不是他们之间后来存在思想分歧的主要原因。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显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的演变过程看得过于简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代受别林斯基的影响最大。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的全部生活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一位如此深刻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中的思想家或政论家。“当时我热烈地接受他的全部学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1卷,页10)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初次相见(1845年5月),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别林斯基那热情洋溢的语调以及他关于《穷人》所说的话——“您自己可知道[……]您写的是什么啊!……您触及了事物的本质,一下子就指出了最主要的问题……真理展示在您面前,向作为艺术家的您宣告它的存在,它像天赋一样为您所掌握,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吧!”(《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31—32)——所有这一切永远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忆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他过去对别林斯基的评价也就随之改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还对伟大的评论家进行指责,但是他始终不能忘怀,也不能冷漠地对待这位在他的青年时代令他感奋的导师。在苦役中经受了思想危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摆脱别林斯基的影响,但是他始终不能彻底地反对别林斯基。与此同时,作家思想上的演变恰恰特别表现在他对别林斯基的态度上,对六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别林斯基乃是敌对的无神论社会主义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和别林斯基的学说,跟四十年代“具有破坏性的思想”进行激烈的斗争。(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8月28日〔俄历8月16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4—36)这种“打倒理想人物”的过程在创作那部企图诋毁革命思想本身的长篇小说——《群魔》的时期达到了最高潮。(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笔记本中对别林斯基的评论”。——《文学遗产》,第83卷,莫斯科,1971年)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三年,他对别林斯基的态度有了新的转变。1877年1月,曾在《穷人》的作者和《现代人》的评论家的结识中起过媒介作用的涅克拉索夫病危的时候,好像已经完全与别林斯基疏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想起了他与别林斯基的初次相会,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在我服苦役期间,一想到这个时刻,精神上就变得坚强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十三卷集》,第12卷,页32)关于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请参阅Β。基尔波京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莫斯科,1976年,第二版。
[19]1846年2月,在《祖国纪事》上登载了别林斯基论《穷人》和《孪生兄弟》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承认上述两个中篇(特别是《穷人》)高度的艺术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主要是针对《孪生兄弟》的。这种善意的评论却使多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灰心丧气。他和《现代人》周围的一些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次没有把他的新作《普罗哈尔钦先生》交给涅克拉索夫,而给了《祖国纪事》的克拉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6年11月写信给他的哥哥说:“我告诉你,我碰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终于和以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现代人》闹翻了。[……]现在他们放出空气,说我受了虚荣心的毒害,妄自尊大,投靠了克拉耶夫斯基,为了要迈科夫称赞我。”(《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页102)青年作家这种由于过分多疑而引起的不大正常的行动引起了《现代人》周围的一些文学家对他的反感,招来了奚落、嘲笑和讽刺短诗。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合写了一首题为《别林斯基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这首诗的开头一节是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亲爱的小子,可怜相的勇士,你好比是文学的鼻子上新长出的一只发红的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