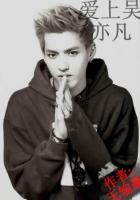二、“战力”无辜奈何?今日台湾,蒋先生说:“十五年来的生聚教训,成为了全球性‘反共’战局中的一股雄厚的战力(见台庆文告)。”吾人应知此“一股雄厚的战力”实有赖于十五年来艰苦卓绝的“生聚教训”才壮大的。生聚也,教训也,固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而有成。战力也,雄厚也,尤必须经过三战三胜的考验才铁定。再则,“生聚”所以充实“教训”之量,“教训”仅可保养“生聚”之质。二者虽相得益彰,但必先有其量,而后能求其质。以此,努力“生聚”,唯一为此时此地当务之急。一言以蔽之,“生育第一”是也。
今兹失败主义的节育论者,自认“穷途末路,故倒行逆施之”,无疑是落了共产党的“人口颠覆”的圈套。若更进而勾结其渗透分子,所到之处,危言挟众,致众陷溺于“乐普”邪门之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动摇我“反攻复国”之基础,自是罪无可逭。一经查出,倘X为中国人,应宫之以谢国人;若Y为外国人,则宫之以谢天下。浅见当否,至祈即席指正。
柏杨为文戏称曰:“‘乐普’是不是邪门,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如果大肆‘宫之’,似乎真要邪门矣。宫了中国同胞,因法律方面的代表人士是橡皮饭碗,只好自叹霉气。不过如果宫了洋大人,好比说,把肯尼先生宫了吧,恐怕就是把义和团大师兄请出正位,都收拾不起来摊子也。而且最糟的是,大师兄既然可以割掉提倡节育朋友的生殖器,一旦提倡节育的朋友,起而希圣希贤,也割掉大师兄的生殖器,好比说,把汤如炎先生生殖器也割掉啦,你说这场官司将怎么打法乎哉?”
卢崇善先生质询的内容是啥,手边没有资料,无法介绍,不过瞧他阁下“杀人于未生之前”的奇异论据,也属世间难得绝件。
廖维藩先生说:“今世人口问题之所以发生,实起于唯物主义之思想,无论共产主义或个人主义,无不出于此种思想。大地之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者已有五千年,何以五千年以来未尝发生严重问题,而独于百余年以前个人主义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后,岂其流毒作用以引起人口问题乎?又何以五千年以来,世界人口继续繁衍,人类不以为有问题,而独于百年以来,人口突飞猛进,而忽然发生人口问题乎?”
由人口问题拉上唯物思想,拉上共产主义,拉上个人主义,是帽子铺掌柜的飞帽办法,不是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人口问题和那些帽子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盖马尔萨斯先生于1798年发表《人口论》时,马克思先生还没有从他娘肚子里生出来哩,这又是一出“纽约城张飞战岳飞”的好戏,无怪他自鸣得意。
廖维藩先生的逻辑是,过去没有问题的,现在也不会有问题,将来更不会有问题。人口这玩艺五千年来都没有问题,而竟然成了一问题,不是“非愚即妄”是啥?五千年来人口是不是有过问题,我们不知道,但知道的一点是,即令五千年来从没有发生过问题,并不能咬定五千年后也不发生问题。盖某一个问题发生之前,该问题固从没有发生过。社会不断进步,旧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也不断产生。
廖先生最痛心的,是为“未婚而时有怀孕机会的年轻妇女”装置“乐普”,像妓女焉、酒女焉,廖先生之意,最好让她们不断生孩子。一个人往往有一个荒唐的时期,不过男人荒唐的危险少,女人荒唐的危险大。男人荒唐,一旦醒悟,改过自新,众人齐拍巴掌曰:“浪子回头金不换。”
而女孩子恐怕不这么简单,盖怀孕是她的大敌,一旦生了一大堆私生子,那就算等于报销。而妓女焉、酒女焉,廖先生既承认她们“势迫处此”,为啥又狠心让她们非生一大堆私生子不可?任何一个妓女酒女,她随时都可以也像臭男人一样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但如果她膝下有一大堆私生子,恐怕她这一辈子有苦受的。
廖先生可以端起嘴脸说:“那是她自作孽呀!”好吧,算她自作孽,但那些无父的孩子何辜?被作践、被歧视,轻焉者自己堕落,重焉者造成社会动乱,廖先生睡觉睡到半夜,难道不流汗吗?
反对节育,不过是时代的绊脚石;而反对大法官老爷,则成了自己的绊脚石矣,万一把大法官反对得恼了火,好吧,算你赢,双手一松,一个倒栽葱,头也破啦,血也流啦,钱也没啦,权也垮啦。仅只一松还不太严重,如果照着汤如炎先生的办法,手执钢刀,把法律方面的代表、诸位老爷的生殖器一一割之,恐怕全世界人士都得侧目而视。但他们对此却闭口不谈,而独向小民下手,要说其脑筋是一盆浆糊,谁能信呢?
然而,要说其脑筋一定不是浆糊,也疑问重重,廖维藩先生的质询中,不断地提“断子绝孙”,以致听众甚为紧张。为妓女酒女装“乐普”,呐喊曰:“欲令其灭绝后裔。”为生育年龄妇女装“乐普”,又呐喊曰:“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进而指着“无识之徒”的鼻子,祭帽子曰:“亡人之国,灭人之种。”
如果“乐普”真如此严重,不要说绊脚石反对,就是“无识之徒”也会反对。但廖维藩先生这位有识之徒踢腾了半天,恐怕还没弄清楚节育是啥,“乐普”是啥。我想用不着向外搬兵,就是另外一位有识之徒的王梦云先生,就先来了一个窝里反,在质询中便曰:“况使用“乐普”而仍受孕者,大有人在。”结结实实打了廖维藩先生一个耳光。实际上真正企图使人断子绝孙的不是节育,而是打算大动宫刑的汤如炎先生。人类已进化到20世纪,文明已达到废除死刑的境界,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度里,竟有代表提出法案,要乱割中外人士的生殖器,不啻老糊涂的胡言乱语。
“乐普”既不是汤如炎先生推广的“宫刑”,也不是扎住太太小姐的输卵管,而是可以随时取下,也可以随时装上的玩意,装上即行避孕,取下仍照样可以怀胎;而且即令装上,也并不保证不会再受孕。真不知道廖维藩先生怎么硬往“断子绝孙”上想。
然而,蒋梦麟及朝中的开明派为了弭平反对声音,于1966年7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合会)召开第一届“人力资源会议”之际,特意请孙科先生发表支持节育的演说,来化解“有违‘国父遗教’”的反对言论,会议中并由赞成节育的代表仲肇相发表“我们需要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台湾人口政策的历史形构”的专题演讲。综合讨论时则由李国鼎副主委与人力资源小组召集人董文琦共同主持,达成推广家庭计划、适当调节生育、早日制定人口政策等协议。内政主管部门一把手徐庆钟则应经合会之请,将1964成立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人口政策委员会,调整委员人选,并由中美基金支持部分经费。
同一年,蒋介石怕美援因人口政策不符美国政策遭停止,被迫签署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发表的《人口及家庭计划宣言》。在这之后,有关主管部门的反对声音逐渐减少,不过强硬者如廖维藩仍继续高分贝地质疑,“值此‘反攻复国’时期,台湾省卫生处处长公然违叛‘国父遗教’,在台湾全省推行节育运动”、“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蒋先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一再向行政当局提出质询,行政当局则对其中敏感的政治意识安抚地答复:“廖委员主张人口政策,应以全中国为对象,本部与廖委员之主张相同……其出发点适与廖委员之关切……相同,自无危害经济与减少生产之事实。”可见,台当局仍然投鼠忌器,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两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氛围保守,蒋梦麟已到了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时任经济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李国鼎与经贸方面的掌舵人严家淦、尹仲容等联袂晋见蒋介石,力主节育人口、家庭计划政策,终于用私人关系及专业知识,坦率地说服了蒋介石接受此项建言。
然而,蒋介石立场软化了,问题却出现了。社会风气保守,无人正面指出症结,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干,就是“节育”两字也有忌讳。于是,出生率成为危机的“根源”,而以妇幼卫生为名的家庭计划也就自然替换当局的节育政策,成为遮盖政治动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美援的公共卫生计划可以归纳为“示范中心”与“大计划”两种工作模式。在家庭计划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这两种模式的转换中,看到它的政策转变。
但由于经合会副主委李国鼎强烈希望加快实施节育以便控制消费,因此与美方协调,将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项下农复会所支助“加强村里卫生——孕前卫生计划”项目扩大为“家庭卫生计划”,援助经费也从30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但要卫生处将计划时间缩短一半,并提前实行。于是,不到一个半月,家庭计划旋即施行,而且更名为“扩大台湾地区家庭计划”,预计在五年内完成既定目标。
回顾这个过程,卫生当局所使用的名称虽然一换再换,从“妇幼卫生”到“人口研究”再到“家庭卫生”,但目的却一直是遏制人口增长的节育。而在此转变过程中,该计划也随美援的需要不断扩大编制与规模。另一方面,在冷战大环境下当局固然默认人口增加问题,并内化为“经济发展所以要控制生育”的逻辑,但这个目标却需要经由个人性节育来实现。因此,如何让台湾妇女不再多生,进而控制整体生育率的增长,是家庭计划的技术关键。
对此,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子宫内避孕器“乐普”(Lippes Loop)是执行大规模节育的利器。虽然它运用异物排斥反应来避孕,副作用不少,但对于卫生计划执行者来说,它成本低廉,不像口服避孕药或传统避孕法一样需要时时教育人民,装一次便可一劳永逸。
此外,对“大计划”卫生的模式来说,“乐普”的装置数是容易掌握的工作指标。于是,在纽约人口局提供“乐普”后,节育计划的架构大致确定。五年内使人口增加率降至18.6‰的政策目标,执行上转化成在五年内装设60万个“乐普”。此外,计划生育观念的倡导,也在操作中转化成劝导“乐普”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