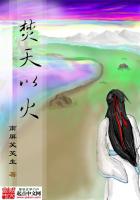就在这一年,我和王鼎成相识。王鼎成比我大一岁,他是个老地下党员,30年代曾是报社记者,笔名为应卫民、许明达等。1942年进入解放区,1944年他护送母亲回到上海,却无法返回解放区。他原是陈鹤琴先生的学生,便到女师工作了。当时陈校长正在实行“活教育”的实验,认为学生不能仅在课堂里学习,还得走出去了解社会,当年暑假便在土山湾开办了“儿童夏令营”。王鼎成是夏令营主任,活动的计划都由他制订。我以比德小学教师的身份参加夏令营的工作。活动开展近一个月,我们带了二十多个小学生,住在李家花园。土山湾是天主教的活动区域,周围有天主教办的圣母院、图书馆、孤儿院,还有一些工厂,我们每天就在这一带活动,冒着骄阳步行,一个点一个点跑。王鼎成是老徐家汇,他带领我们去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尤其要学生了解那些孤儿的生活,回来还要写心得体会。结束时我们还在女师组织了一次汇报演出。夏令营使我和王鼎成的生命有了第一次的交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地下党身份。
9月,因党的工作需要,以推广陈鹤琴“活教育”的名义,我到女师附小任教。我的课不多,只担任五年级的自然课,主要负责福利会的工作,实际是以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党的活动。福利会组织十分严密,有公开的理事会,请社会上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担任顾问,如陈鹤琴先生和一些大资本家都是我们的顾问。会员不交会费,资金主要从社会各界募集,也有许多同志无私捐赠。福利会办有专门的报刊《福利消息》,前后出了三十期,由王鼎成担任主编。每期刊物出版,各区联络员都到福利会来领取,然后将该刊发给每个会员,再通过他们发送到各个学校。这个刊物对福利会的发展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原来我们家保存有全套的《福利消息》,后来一部分捐给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恐怕他们也没好好保存。
我与王鼎成成为同事兼战友,共同主持福利会的工作,并住在同一幢宿舍楼里,两人的接触就更多了,可以说是地下工作让我和他越走越近。他生性开朗,和不认识的人也能一下接近,女师的学生和教师都喜欢到他那去,所以他的房间总有许多人在谈笑风生。听说他结过婚,太太思想也挺进步的,我认识他之前,她就生肺结核过世了,所以并没有见过。他母亲也参与革命工作,许多事情都是通过她来进行联络的。周围的同事也看出我们之间的感情变化,我们两人的上级陈育辛曾警告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不要太明朗。所以尽管彼此心里都明白对方的心思,但一直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们这个福利会只管市立学校,斗争的对象是国民政府;而私立学校还有“私校教联”,斗争的对象是老板。后来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并称为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教师运动的三大进步教师团体。其实当时地下党的活动十分活跃,组织一般是分条联系的,大学有学联,工厂有工会,都以公开的名义团结群众,背后却是政治斗争。解放后我们才知道,上海的地下党力量有多强,所以上海解放时没受什么损失。
为不引起当局的注意,福利会的活动政治性不是太突出,主要通过会员联络广大教师,代表他们向当局提出经济要求。当时有的学校无故解聘教师,导致许多人失业,于是地下党发起“保障职业运动”。如有人被解雇,我们会帮他与校方理论,以维护教师的工作权利。后来物价飞涨,国民生活水平低下,又团结教师向校方要求提高工资等。职业保障和提高待遇成为福利会的两大奋斗目标,经过我们的斗争,一些被解聘的教师重新得到工作,许多群众得到实利,更看到我们的力量。我们组织过许多活动,如不时到各校去与教师座谈,开展览会或音乐会,开办廉价商品义卖,举行戏曲表演,请教师演讲,或开办时局讲座,等等。当然也曾组织游行,一般都是到教育局或市参议会去请愿,比如保障就业组织过一次,后来马叙伦马叙伦(1885—1970),字夷初,浙江余杭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等十一人作为上海各界的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是“反内战、要和平”,当时我们也组织去送行。游行回去,参加者都会晒得脸色黑红,校长一看就知道哪些人参加游行了。有的校长会进行压制,有的就睁只眼闭只眼。福利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也因为这个组织的色彩比较平和,会员日益增多,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千人,如比德小学百分九十的老师后来都成为福利会的成员,并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我们也利用一些突发事件来开展斗争。1947年初,陕西北路国民小学发生校长潘文珍打伤并解雇教师陈素云事件。为团结广大教师,我们又成立了斗争性更强的上海市维护市校教师权利联合会,简称护权会。其成员大多是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的会员,创建这个团体既是为了适应更为尖锐的斗争,也是为了掩护福利会。这两个组织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前者侧重于斗争,后者主要从事福利活动。那时我担任护权会的党组书记,但为不暴露身份,还有两个同志配合我工作,对外活动几乎都由他们出面。为争取社会的支持,护权会首先大造舆论,召开了几次记者招待会,印制并散发小册子《上海市立陕西北路国民小学校长潘文珍殴打陈素云事件真实录》,然后派代表前往教育局请愿。最终赢得胜利,殴打陈素云的校长被革职。
为纪念抗战十年,1947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新的“七七宣言”指1947年《中共中央发布七七时局口号》。,主旨是争取广大群众,建立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为扩大影响,组织要求我们散发给广大群众,但散发这种共产党的文件在当时是很危险的,我们只能通过邮局寄匿名信。地下党员负责发信,邮件寄给各校全体教师,中间人士甚至国民党校长都会收到,这样既可扩大宣传又可掩护进步教师。刚收到这个文件,有的教师很害怕,但问下来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他们才放下心来。“七七宣言”的成功宣传,使群众看到党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进步人士。
一系列的斗争取得胜利,使大家看到希望,社会上对我们的关注也越来越多,随之影响也越来越大。斗争中有不少人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有的人来接近我们,有的人积极参加活动,我们便物色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特别好的苗子可以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开始时地下党员不多,后来一个一个发展,最后每个市立学校都有党组织了。为保护组织,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即一个老党员联系一个人,这个人负责一个党小组,一个党小组一般只有两三个人。当时我负责六个党小组。女师的地下党后来发展挺快的,有不少学生、教师成为党员,但我并不与她们来往,我只负责女师附小的两个党员。另外,我还要联系西区与南区的各两个党小组,本区一个学校有两个可发展的男士,也归我联络。传达指示都是当面进行,通常以福利会的工作为掩护,一般到学校或党员家里,而不会到娱乐场所。那时交通不发达,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我又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每次都必须走过去。我时常一次找两个人谈,比如我到晋元小学找大毛、小毛,多数在晚上去。为防止暴露,这次碰头就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每次见面的地点不相同,也必须精确把握时间。约会时既不能迟到,也不能早到,因为早早在该地徘徊会引人注目。如果错过时间只能取消这次见面,再通过电话约好再见面。我们从来不用信件联系,电话号码也不能写在纸上,而必须背出来,当时上海的电话是六位数,我一度能记几十个电话号码,所以现在孩子们的电话号码我仍能背下来。
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组织也曾对我们进行气节教育。首先要加强防范,防止暴露,万一被捕则要做到三条: 一不暴露党员身份,二不讲出任何上下级关系,三不写悔过书。我们也认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可以牺牲一切。
五、 残酷的考验
1947年9月,福利促进会拟组织一个请愿活动,我们委托富通印刷所印制一些宣传文件。富通印刷所位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587号,那是一幢三层的小楼,印刷所店面在二楼,编辑组在三楼,一楼是生活书店,卖些进步书籍。后来我才知道,富通印刷所就是我党的联络机关,有不少员工是地下党员,我们的《福利消息》和“七七宣言”都是在那里印的。现在想来,进步刊物过于集中在那里印刷,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警觉。
本约定 9月18日去印刷所取文件,但我认为9月18日是抗战纪念日,那一天比较敏感,所以决定延迟一天即9月19日再去取。第二天下午,陈南如老师要去该所取文件,她告诉另一个老师,叫我不要去了,但那个老师却忘了通知我,等到她想起来,我已离开学校了。晚7点左右,我踏进印刷所大门,顿时感觉不对劲,屋里有许多人,从外表看有的像学生,有的像工人,包括我的同事陈南如,但他们一个个面色呆滞,谁也不吭声。原来特务已破获这个机关,自当天下午就埋伏在里面,进来一个抓一个,到我进来时已抓了不少人,当然许多人并不是地下党员,有的进来买书,有的偶然来印印东西。特务劈头就问:“你来找谁?”我急中生智,随便指一个印刷所职员。特务又问我来做什么,我当然不能说取福利会的文件,就说:“双十节双十节,又称“辛亥革命纪念日”。1911年10月10日(即清宣统三年辛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最后推翻清朝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9月,民国政府将此日定为“国庆日”。要到了,我们教师打算开联欢会,我是来请他们印请帖的。”特务当然不信,夺过我的手提包搜查,从里面搜出一份“七七宣言”,特务如获至宝,逼问这个文件从哪里来的,我说:“这是邮局寄过来的,我们学校许多老师都收到的,我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当时我们发送“七七宣言”,的确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收到的,这便成为我的口实,当然他们仍不会相信。过一会,便听到那些特务向机关打电话说:“抓到一个女共党。”当晚特务叫来小汽车,将印刷所全体员工及那天到场的所有人都抓进看守所,这就是所谓的“富通事件”。
其中我们六个人被认作共产党重要嫌疑犯,分别送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中统特务机关进行特别审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形。我被单独塞进一辆囚车,一进亚尔培路2号的大门便被带到二楼,转角处有个立式大钟,我瞥了一眼,时针正指着9点。一个特务叽叽咕咕地嘟囔:“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啊!这里有三十六种大刑,七十二种小刑……”这时我意识到最严酷的考验来了,我没有想太多,唯一的念头就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主审的中统特务十分凶狠,瘦瘦长长的,操北方口音,后来才知道他叫苏麟阁苏麟阁,又名苏君平。时任上海中统局特务机关审讯组特务组长、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组组长,参与“《文萃》事件”和“富通事件”,上海解放后潜伏在大陆,1951年被判处死刑。,20年代曾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变,在中统机关专门审讯知识分子,旁边还有两个专门动手的小特务。苏麟阁首先问我是否共产党,我当然不能承认,当时相当镇定。当天晚上他们动用了五种酷刑。先是将方棱形的竹筷夹在我十指之间,再死劲地绞,指缝立即皮绽肉裂,双手淌血。接着用布条缠在我头上,特务一边用棍子使劲绞布条,一边恶狠狠地说:“绞死你!”布勒进肉里,头疼得几乎裂开。然后又强迫我跪在地上,将大木棍压在我的小腿上,两个小特务踩在上面来回滚动。他们的花样太多了,到后来随便他们怎么弄,我再也不开口了。苏麟阁一边用力拽我脖子上的淋巴,一边说:“你还不承认呀?再下去肯定要终身残疾了,你不要命啦!”最后是老虎凳,他们把我的腿紧紧地绑在一条长凳上,在小腿处塞入一根竹杠,两个小特务将我的双手向后拽住,然后在我的脚跟处放进一块棱角锋利的砖块,边加边问,没有回答又继续加砖,最后加到五块。疼痛使我晕过去,那些人再口含凉水喷在我脸上,我被弄醒又晕过去,晕过去再被弄醒……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多,我的膝关节已完全脱臼,特务把我的小腿推上去,我已无法行走,他们就一路拖着我,将我扔在楼下的临时监室。一位难友过来说:“快起来走走,否则以后终身不能走路了!”两个人把我拖起来,搀着我忍痛走了好久,这时天已大亮。过了好长时间我只能扶着墙慢慢走,而脚后跟的伤口一直溃烂难愈,鞋也无法穿上。当时年轻力壮,总算顶过去了,但以后阴天下雨往往隐痛,现在年纪大了更是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