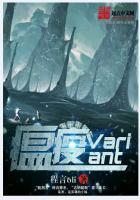他的愉快看来也不是全然来源于他从对同伴们的同情中所获得的快乐,而他的痛苦也不是来自当他渴望这种愉快时,他没有获得同伴的同情所产生的失望,尽管这两者无疑地要起某种程度的作用。我们读完一本书或一首诗时,经常是我们自己再读就没有什么乐趣了;然而我们却仍然能够在把它读给同伴听时找到乐趣。对于他来说,那本书(或诗)充满了新奇的魅力。我们分享那本书在他心中自然激起的那种惊讶和赞叹,然而那种惊讶和赞叹却是它再也无法在我们的心中激起的了。我们这时更多的是用他的眼光,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所有思想。这样我们以对同伴的乐趣(他使我们感到快活)的同情而自娱。相反,如果同伴显得从中没有得到什么乐趣,我们将十分懊丧。我们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乐趣念给他听了。这里就正是这种情况。同伴的欢乐无疑激活我们的欢乐,他们的沉默无疑使我们失望。不过,虽然这个对我们从前者得来的快慰和从后者得来的痛苦有一定的作用,但它绝不是任何一者的唯一的原因;别人的情感与我们自己的情感相一致是我们愉快的一个原因,但不能就以这一点来说明产生愉快和痛苦的原因,我朋友对我的快乐所表示的同情,诚然通过激活我的快乐可以给我愉快;然而他们对我的忧愁所表示的同情,如果说它只是能激活我的忧愁的话,就并不能给我什么了。不过同情可以激活愉快,减轻忧愁。它通过提供另一种满足的源泉来激活快乐,通过把在当时几乎唯一可能接受的令人愉快的情感悄悄地输入心田而减轻我的忧愁。
因而必须看到,我们把不愉快的情感传达给我们的朋友,要比我们把愉快的情感传达给朋友们的心情急切得多。我们从朋友们对前者的同情中比对后者的同情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满足,而且会由于得不到它而感到更加愤慨。
当不幸的人们找到了一个能够向他倾诉自己的悲痛的人时,他们感到是多么宽慰啊!他们仿佛把他们痛苦的一部分分给了他对自己的同情:可以恰当地说,他与他们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不仅感到了一种与他们所感受的相同的痛苦,而且他仿佛从中分了一部分出来给自己,他的这种感受仿佛减轻了他们所感受的重压。而且通过讲述他们的不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记起他们的悲痛。他们在自己的记忆中唤起他们对引起那些苦恼的情况的回忆。于是他们的泪水流得比以前更快了,他们只想尽情地大哭一场。他们在这一切中得到快慰,而且他们明显地感到通过这一哭轻松了许多。同情的甜蜜远远补偿不了悲伤的痛苦,他们之所以重新提起那些悲痛,只是为了激起这个同情。相反,对不幸的人们的灾难表现冷淡是对他们所能给予的最残酷的打击;而对我们同伴的快乐置若罔闻则只不过是没有礼貌;当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痛苦时,而不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则是真正的十足的非人道。
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情感,愤恨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情感。因而,我们对朋友们会不会接受我们的友谊的担心远不如对他们能否分享我们的愤恨的担心。虽然我们能够原谅朋友们,对我们可能得到的宠爱显得无动于衷,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对我们所可能得到的伤害表现冷漠。我们对他们不能分享我们的感激之情的恼怒远不如我们对他们不同情我们的愤恨的一半。他们可以不成为我们朋友的朋友,但他们必须成为与我们不和的人的敌人。他们与我们的朋友不和,我们不大会愤恨,尽管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时要装模作样地同他吵一吵;但是如果他们与我们的敌人友好,我们却会认真地与他们争吵。令人愉快的爱和欢乐的情感无需其他乐事就可使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和感到支持。忧愁和怨恨的痛苦情绪则更加强烈地要求同情的安慰。
由于在任何一个事件中主要当事人都高兴能看到我们对他的同情,而得不到我们的同情就感到受了伤害。所以在我们能够给予同情时,我们也显得高兴;而不能给予同情时,我们也显得受了伤害。我们不仅爱向成功者祝贺,而且也乐于安慰受折磨的人。我们从与内心情感上我们完全同情的人的谈话中得到的乐趣,似乎远远补偿了我们在看到他的处境时所给我们的悲伤的痛苦。相反,我们还总是会因为不能同情他而感到不快。而且我们并不会因为免除了这种同情的痛苦而感到高兴,反而因为我们不能与他分享痛苦而感到受了伤害。如果我们听到一个人为自己的不幸而大声痛哭,当我们设想如果那件事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它对我们并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时,那么我们就会对他的悲痛感到惊讶;而且因为我们不能分享他的这种感情,我们就会把他称作卑怯和软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到另一个因为交了极小一点好运就高兴得不得了,或者是我们所称作的欣喜若狂,他就会使我们反感。我们甚至对他的高兴表示不满;而且由于我们的情感不能相通,我们甚至称他为轻浮和愚蠢。如果我们的同伴对一个笑话大笑或笑个不停超过了我们认为应有的程度,也就是超过了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所能笑的程度时,我们甚至反而还会感到讨厌。
(第三章)论我们通过别人的情感与我们自己的情感是否相通来判断别人的情感是否适宜的方式
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与旁观者的同情完全一致时,在这个旁观者看来它必然是恰当而适宜的,而且适合于它的对象。相反,在旁观者深切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他发现当事人的那些情感并不与他所感受的相吻合时,那么对于旁观者来说,它就显得不恰当和不适宜了,因而也不符合于引起那些情感的原因了。这样一来,赞同别人的激情、认为它们与其对象相符与声称我们完全同情他们是一回事。而不赞同它们、不认为它们与其对象相符也就与声称我们不完全同情他们是一回事了。一个对加害于我的人表示愤恨的人见到我完全同他一样愤恨那些伤害,必然赞同我的愤恨。一个及时同情我的悲痛的人不能不承认我的伤心是合乎情理的。一个与我完全一样赞赏同一首诗或同一幅画和同样赞赏它们的人必然就会承认我的赞赏是恰当的。一个同我一道对同一个笑话发笑,而且同我一起笑的人绝不可能否认我的发笑的恰当性。相反,一个在上述不同场合感觉与我不同的人,或者感觉与我不相符合的人,必然会由于我的情感与他的情感不能发生共鸣而不赞同我的情感。如果我的仇恨超过了我的朋友的义愤所能接受的程度,如果我的悲伤超过了他的最亲切怜悯所能给予的程度,如果我的赞赏过高或过低不能与他的相符,如果在他仅仅是微微一笑时,而我却从心底里发出高声大笑;或者反过来,当他开怀大笑时,我却仅仅是轻微一笑。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他对引起发笑的对象进行了思考,他就可看出我是如何被它所感染。于是根据他的情感与我的情感之间或多或少的差异,我必然会引起他的或多或少的不赞同。在所有这些场合,他自己的情感就是他用来判断我的情感的标准和尺度。
赞成别人的意见就是采纳那些意见,而采纳它们也就是赞成他们。如果使你信服的那些论点同样也使我信服,我必然赞同你的定论;如果使你信服的那些论点不能使我信服,我必然不赞同你的定论。我不能设想我会信服你的论点,而又不赞同你的定论。因而,人人都承认赞同或不赞同别人的意见就是表示他们的意见和我们自己的意见一致或不一致。我们对他人的情感或激情的认可与否也是这样的情况。
诚然,在某些场合,我们好像赞同,然而又没有任何同情或相应的情感。因而在这种场合,认可的情感就将显得与这种一致的感觉不同。不过,稍加留神我们就会相信,即使在这些场合我们的认可也完全是建筑在这种同情或与其相应的情感上的。这里我将举一个无关轻重的小事作为例子,因为在这些小事上人们的判断反而不大容易受到错误体系的曲解。我们可能常常欣赏某一个笑话,认为同伴笑得对,笑得恰当,尽管我们自己因为情绪不好,或者碰巧我们当时正在注意另外一些事情而没有笑。然而,我们根据经验知道在绝大多数场合什么样的愉快可以使我们发笑,同时我们觉察到这就正是那种愉快。所以,我们赞同同伴的笑声,而且觉得那是对事物的自然而恰当的反映。因为,虽然在我们目前的情绪下我们不容易接受它,但我们意识到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我们是会很乐意参加进去的。
关于其他的激情也常有这种情况。一个陌生人在街上从我们身边走过,带着一脸的极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们得知他刚刚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在这种场合,我们不可能不赞同他的悲痛。时常还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悲伤,我们也不想对他的这个举动有什么关怀,然而这并非是我们缺乏人性的表现。也许,他和他的父亲和我们完全不认识,或者凑巧我们正忙于其他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象使他感到悲伤的各种情况。不过,我们根据经验知道什么样的不幸才自然会引起这样强烈的悲痛。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花时间去充分而全面地考虑他的处境,无疑我们会极端真诚地同情他。即使在那些场合,在我们的同情并没有真正产生的那些场合,我们对他的悲痛的认可也是基于这个有条件的同情的意识上的。我们用根据从前对于什么样的情感通常能够与我们的情感相一致的认识的经验所得出的一般规则,就像在许多其他的场合纠正着我们当时不适当的情绪一样纠正着这一次的情感。
对于产生各种行为和根本上决定行为善恶的内心情感或感情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或两种不同的关系来进行考察。首先,从产生行为的原因,或者说产生行为的动机;其次,从行为提出的目的,或者说行为欲产生的效果。
情感与激起情感的原因或事物间所形成的关系相称抑或不相称,恰当抑或不恰当,就构成了随后行为的恰当与否,光彩或不光彩。
情感所要达到的或倾向于产生的效果的性质有益或有害,构成了行为的优劣,构成了应该获得褒奖或惩罚的品质。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主要考虑情感的倾向,而忽视了它们与激起它们的原因之间的关系。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判断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时,以及对这种行为的情感时,我们总是把它们放在这两个方面来考虑的。那就是当我们责备某人的爱慕、悲伤和愤恨过度时,我们考虑的不仅是这些情感倾向于产生的毁灭性的后果,而且考虑了引起这些情感产生的细小的原因。也许,他喜欢的人的功劳并没有如此伟大,他的不幸并没有如此可怕,激怒他的原因并非如此异乎寻常足以证明他有必要如此激动。如果引起激情的原因在各方面都与其激情相称,那么,我们就应该放纵自己,也许应该赞同他的激烈情绪。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任何情感与激起它们的原因是否相称的时候,我们除了使用和我们的自身相应的情感外,几乎不可能采用任何其他别的尺度。如果我们在心里把事情完全当作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发现它所引起的情感与我们自己的情感偶合和相符,我们就必然会认为它们与引起它们的对象相称和适当。如果我们发现情形相反,我们必然会认为它们过于夸张和不成比例。
一个人的各种官能就是他判断别人的类似官能的尺度。我用我的视力判断你的视力,用我的听力判断你的听力,用我的理性判断你的理性,用我的愤恨判断你的愤恨,用我的爱心判断你的爱心。我没有别的,也不能有别的任何其他方法来判断它们。
(第四章)同一题目的继续
在两种不同场合,我们可以用别人的情感是否与我们自己的相通来判断别人的情感是否恰当。首先,把引起那些情感的对象放在与我们自己或我们要判断的那个人的情感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情况下进行考虑;其次,把它们放在对我们的这个或那个情感有特殊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考虑。
关于那些被认为与我们或者与我们判断的情感的人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对象,在他的情感与我们自己的情感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趣味很高、有良好的鉴赏力的人。平原的美丽、山岳的雄伟、建筑物上的饰物,一幅画的表现方式、一篇文章的构思,第三者的行为,不同数和量的比例以及宇宙这部伟大机器用它神秘的齿轮和弹簧生产出来的和永不停息地向我们展示的各种各样的表现;科学和鉴赏力的所有这些命题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同伴视为与我们谁都无特殊关系的东西。我们和我们的同伴都是从同一观点在看待它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对上述一切情感与感情上的完全和谐一致表示同情,换句话说,也不需要去幻想从它的出现以及产生所发生的情况的变化。如果我们常常受到的影响不同,那是由于我们注意的程度不同,而这种不同又抑或是由于我们的不同生活习惯,使我们容易对上述复杂的对象的不同部分给予不同的关注,抑或是由于它们作用于我们心理官能的自然敏锐度不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