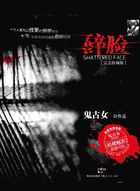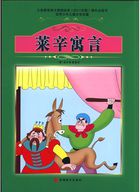“当然是你来演伊莱恩了,安妮。”戴安娜说,“我根本没勇气漂到那儿。”
“我也没有。”鲁比·吉利斯哆嗦一下,说,“要是我们两三个人一起上船,坐得稳稳当当的,我倒不怕漂下去,那样还挺好玩的。但是躺下来装死——不行,我会吓死的。”
“那当然浪漫了。”简·安德鲁斯承认说,“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一动不动。差不多每隔一分钟我就会跳起来看看漂到了哪儿、是不是漂得太远了。你知道,安妮,这可会破坏效果啊。”
“但伊莱恩长着红头发也实在太荒唐了。”安妮哀叹说,“我倒不害怕漂流,也很乐意当伊莱恩,但这还是很荒唐。鲁比应该当伊莱恩,因为她的皮肤那么白,还有那么好看的金色长发——你们知道的,伊莱恩的‘那头金发瀑布般垂下来’。伊莱恩是百合少女,喏,红头发的人不能当百合少女。”
“你的肤色跟鲁比一样白。”戴安娜真诚地说,“你头发的颜色比剪之前深了许多呢。”
“哦,你真的这么认为?”安妮惊呼,高兴得脸都涨红了,“有时我自己也这么想——可从来不敢问别人,害怕人家说不是那回事。你觉得现在能说它是茶色的吗,戴安娜?”
“能,我还觉得它真的很好看。”戴安娜赞美地看着安妮那一头浓密光滑、柔软卷曲的短发,一条漂亮的黑丝绒发带恰到好处地束在上面,还打着蝴蝶结。
她们站在果园坡下面的池塘边,那里有一片从岸边突出去的陆岬,周围环绕着桦树。陆岬的顶端有一个架在水面上的小木台,方便渔夫和猎鸭人出入。鲁比和简与戴安娜一起打发这个仲夏的下午,安妮过来跟她们一起玩。
这个夏天,安妮和戴安娜在池塘边消磨了大部分时间。爱德怀德已经是过去式了,春天的时候,贝尔先生残酷地砍下了他牧场上的那一小圈树木。安妮曾坐在树桩间痛哭了一场,却并没有忽视这种行为的浪漫情调。不过她很快就想开了,像她跟戴安娜说的,她们毕竟是十三四岁的大姑娘了,再玩游戏房这么孩子气的游戏已经不大合适了。在池塘附近可以找到更有趣的事做。在桥上钓鳟鱼就很有意思,两个女孩还学会了自己划船,她们划着巴里先生打野鸭的平底小渔船四处转悠。
排演伊莱恩的戏剧是安妮的主意。去年冬天她们在学校学了丁尼生[丁尼生: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肄业于剑桥大学。诗作题材广泛,想象丰富,形式完美,辞藻绮丽,音调铿锵。曾获桂冠诗人称号。其诗作《国王叙事诗》讲述了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诗中有下文中提及的百合少女、兰斯洛特、吉娜薇、亚瑟王等人物。]的诗歌,教育总监将之纳入爱德华王子岛学校的英文课程。她们把诗掰开揉碎,又是分析又是研究,如果还残存她们没能发掘出来的意义,那简直是奇迹。不过,至少美丽的百合少女、兰斯洛特、吉娜薇以及亚瑟王在她们脑海里已是活生生的人物了。安妮暗地里对自己没能生在卡米洛而倍感遗憾,她说,那个时代比现在要浪漫得太多太多了。
安妮的计划受到了热烈的呼应。女孩们发现,如果把平底船从岸边推出去,它会顺水流漂到桥下,最后自己停泊在池塘拐弯处的另一块岬地上。她们经常这样漂下去,排演伊莱恩的戏剧再方便不过了。
“好吧,我演伊莱恩。”安妮迟疑地让步了。尽管她很乐意出演主角,但她的艺术品位要求选角合适,而她的局限使她无法胜任主角。“鲁比,你演亚瑟王,简是吉娜薇,戴安娜当兰斯洛特。不过你们要先扮演那对兄弟和父亲。我们不能要那个老哑仆了,要是船里躺着一个人,就盛不下更多的人了。我们还要把船从头到尾铺上深黑色的锦缎。你妈妈那条黑色的旧披肩正合适,戴安娜。”
黑披肩弄来了,安妮把它平铺在船上,然后躺在船底,双眼紧闭,两手交叉放在胸前。
“啊,她看起来真像是死了。”鲁比·吉利斯看着摇曳不定的桦树影子下面那张宁静白净的小脸,紧张地低语,“这让我害怕,姑娘们。你们认为这样表演真的好吗?林德太太说演什么戏都极其可恶。”
“鲁比,你不应该说起林德太太。”安妮严肃地说,“把效果都破坏了,因为现在是林德太太出生几百年之前。简,这事你来处理,伊莱恩死了还要说话,真是太荒唐了。”
简确实负起了责任。她们没有金黄色的布单,不过一条黄色日本绉纱钢琴罩布就是绝佳的替代品。眼下还没有白色百合,不过有一枝颀长的蓝色鸢尾花放在安妮叠放的手里,效果无比的好。
“好了,她准备好了。”简说,“我们要亲吻她平静的额头,戴安娜,你说,‘妹妹,永别了’。鲁比,你说,‘永别了,亲爱的妹妹’,你们两个要尽量表现得悲痛欲绝。安妮,看在老天的分儿上,稍稍笑一笑吧。你知道伊莱恩‘躺着,仿佛在微笑’。这样好点儿了。现在,推开小船吧。”
于是小船被推开了。水里埋有一根旧木桩,小船在木桩上重重地擦了一下,漂了过去。戴安娜、简和鲁比一看到船顺着水流朝小桥漂去,就拔腿飞奔,跑过树林,穿过大路,抵达下游的低岬地。在那里,她们变成兰斯洛特、吉娜薇和国王,做好了迎接百合少女的准备。
有那么一会儿,安妮缓缓地漂流而下,充分享受着这份浪漫。然后,不浪漫的事情发生了,平底船开始漏水。就在一瞬间,伊莱恩不得不飞快地爬起来,抓起她的金黄色布单和深黑色罩布,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船底的那条大裂缝。河水从裂缝中咕嘟咕嘟地涌进来。木台附近那根尖木桩划破了钉在船底的毡条。安妮不知道这个情况,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水漏的速度这么快,不等漂到低岬地小船就会灌满水沉下去了。桨在哪儿呢?落在木台上了!
安妮发出一声轻微短促的惊叫,根本没人听见。她的嘴唇都吓白了,但还没有失去自制,有一个求生机会——只有一个。
“我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天她告诉阿伦太太,“小船漂向小桥的时候,船里的水不停地往上涨,那会儿就像是过了好几年。我祈祷了,阿伦太太,最真心实意地祈祷了,不过没有闭上眼睛,因为我知道上帝救我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小船漂到靠近桥桩的地方,让我爬到桥桩上。你知道桥桩不过是些老树干,上面残留着许多树结和树杈头。祈祷是应该的,不过我还得留神观察、抓住时机。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亲爱的上帝,请把船靠近桥桩吧,剩下的我来干’。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想把辞藻弄得很华丽。不过我的祈祷应验了,小船正好撞到了一根桥桩,还在那里停留了一小会儿。我把围巾和钢琴罩甩到身后,攀到一个大树结上,那真是天赐的树结啊。阿伦太太,我就困在那里,抱着滑溜溜的老树桩,上不去下不来。那姿势可真够不浪漫的,不过那时我也顾不上了。要是你刚刚从水底坟墓逃脱出来,你是不会考虑浪漫不浪漫的问题的。我马上做祈祷表示感恩,然后就集中精力牢牢抱紧桥桩,因为我知道,想重新回到陆地,也许只能指望凡人的帮助。”
小船漂到了桥下,很快沉没在激流中。在下游低岬地等候小船的鲁比、简和戴安娜亲眼目睹了它的沉没,确信安妮也跟着沉了下去。一时间她们动弹不得,脸色惨白,被这幕惨剧吓得呆若木鸡。接着,她们放声尖叫,发疯般跑过树林,经过大路时根本没有稍作停顿看一眼小桥那儿。安妮死命地抱着那根珍贵的救命桥桩,看着她们飞奔而过,还听到了她们的尖叫。很快会有人来救她,不过她的姿势可真够难受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对苦命的百合少女来说,每一分钟都像一小时那么长。怎么还没人来呢?姑娘们跑哪儿去了?假如她们晕了过去,全都晕了过去,该怎么办!假如没有人来该怎么办!假如她累得抽筋抱不住桥桩该怎么办!安妮看着下面可怕的绿色深渊,水面上还摇曳着细长而顺滑的树影,不由哆嗦了起来。她开始想象所有那些悲惨的结局。
她的胳膊和腰已经酸疼得无法忍受了,就在此时,吉尔伯特·布莱斯划着哈蒙·安德鲁斯的小船到了桥下。
吉尔伯特抬眼一看,大吃一惊,他看到一张满带轻蔑的苍白小脸,那双朝他看下来的灰色大眼睛虽然惊恐万分,却同样充满了轻蔑。
“安妮·谢利!你究竟是怎么跑到那儿去的?”他喊道。
不等安妮回答,他就把船靠近桥桩,向安妮伸出手。别无选择了,安妮只好抓住吉尔伯特·布莱斯的手,爬下桥桩来到船上。她坐在船尾,满身泥泞,怀里抱着湿漉漉的围巾和钢琴罩,郁闷恼火之极。这副模样要想保持尊严可真不是一般的困难。
“出什么事了,安妮?”吉尔伯特举起船桨问。
“我们在演伊莱恩。”安妮冷冷地解释,甚至看都不看救命恩人一眼,“我得乘着那条驳船——我是说平底船漂到卡米洛。小船漏水了,我爬到了桥桩上。姑娘们求救去了。你能发一下善心把我送到木台那儿吗?”
吉尔伯特热心地划船到了木台,安妮不屑于他的帮助,自己敏捷地跳到了岸上。
“非常感激你。”她傲慢地说了一句,转身就走。然而吉尔伯特也从船上跳上岸,一只手抓住安妮的胳膊拦住了她。
“安妮,”他急促地说,“听我说,我们不能做好朋友吗?我非常抱歉那次取笑你的头发。我不是故意气你的,只是开个玩笑。再说,这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觉得现在你的头发非常漂亮——我确实这么认为。我们做朋友吧。”
安妮犹豫了片刻。在她愤怒的尊严之下,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刚刚被唤醒了,那就是,吉尔伯特那淡褐色眼睛流露出的半是羞怯半是渴望的神情真是挺好看的。她的心奇特地怦然一跳,但是宿怨的痛苦立刻坚定了她正在动摇的心。两年前的那一幕清晰地闪回在她的记忆中,鲜明得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吉尔伯特叫她“胡萝卜”,让她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人现眼。别的孩子和大人可能会认为她的怨恨非常可笑,就跟造成这怨恨的起因一样可笑,但它好像根本不能随时间流逝而有所减轻或平息。她恨吉尔伯特·布莱斯!她永远不能原谅他!
“不行。”她冷冷地说,“我绝不跟你做朋友,吉尔伯特·布莱斯,我也不想跟你做朋友!”
“好吧!”吉尔伯特跳进小船,一脸怒气,“我再也不会要求跟你做朋友,安妮·谢利,我也不在乎!”
他挑衅般地飞快划着船桨离开了。安妮走上枫树林中那条苔藓遍布的陡峭小路。她高高地仰着头,心里却冒出一丝奇怪的后悔的感觉。她几乎希望自己答应了吉尔伯特。当然了,他曾可恶地羞辱过她,不过仍然……总之,安妮觉得坐下来痛快哭一场会是种解脱,她真的已经很虚弱了,因为惊恐,也因为紧抱桥桩累的。
半路上她遇到了匆忙跑回池塘的简和戴安娜,两人就像是疯子一样。她们在果园坡没有找到人,巴里夫妇都不在家。于是鲁比·吉利斯开始陷入歇斯底里,只好把她留在那里尽量恢复平静。简和戴安娜飞奔过鬼魂树林,越过小溪,跑到绿山墙。在那儿她们也没有找到人,玛瑞拉去了卡莫迪,而马修在后院整干草。
“哦,安妮。”戴安娜喘着气,紧紧搂住安妮的脖子,流下了宽慰喜悦的眼泪。“哦,安妮……我们以为……你已经……淹死了……我们觉得自己像是杀人犯……因为我们强迫……你演……伊莱恩。鲁比歇斯底里了——哦,安妮,你怎么逃出来的?”
“我爬上了一根桥桩。”安妮有气无力地解释,“吉尔伯特·布莱斯划着安德鲁斯先生的小船路过,把我送到了岸上。”
“哦,安妮,他太棒了!哎呀,好浪漫呀!”简终于能够说话了,“以后你当然会跟他说话啦。”
“我当然不会。”安妮又恢复了老样子,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想再听到浪漫这个词,简·安德鲁斯。姑娘们,我很抱歉把你们吓成这样子,都怪我。我真觉得我的生辰八字不好,每做一件事,不是自己倒霉,就是给最好的朋友惹来麻烦。我们划走了你爸爸的船,还弄丢了。戴安娜,我有预感,大人们再也不会让我们在池塘里划船了。”
事实证明安妮的预感不是一般的准。这天下午的事件传出去之后,巴里家和卡斯伯特家都惊恐万分。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儿脑子呢,安妮?”玛瑞拉哀叹。
“哦,能,我想我能,玛瑞拉。”安妮乐观地回答。她已经独自在东厢房大哭过一场,紧张的神经已经放松,又成为往常那个快乐的安妮了,“我认为现在我变明智的希望比以前更大了。”
“我可没看出来。”玛瑞拉说。
“哎,”安妮解释说,“今天我得到了新的宝贵教训,自从来到绿山墙,我就一直在犯错误,每次错误都帮助我克服一个大缺点。紫水晶胸针事件让我不再乱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鬼魂树林的错误让我不再乱用自己的想象力。止痛剂蛋糕事件治好了我做饭时的粗心大意。染头发事件治好了我的虚荣,我再也不去想自己的头发和鼻子了——至少,不经常想。今天的错误会让我不再过分追求浪漫。我总结过了,在艾文利想浪漫是不可行的。在几百年前城堡高耸的卡米洛可能很容易浪漫起来,但是现在没人欣赏浪漫了。我坚信你很快就会看到我在这方面的巨大进步,玛瑞拉。”
“我确信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玛瑞拉不无怀疑地说。
但是,等玛瑞拉出去后,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的马修把一只手搭在安妮肩上。
“别完全放弃你的浪漫,安妮。”他腼腆地低声说,“有一点儿浪漫是好事——当然,不要太多——但要保留一点儿,安妮,保留一点儿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