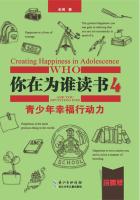我见过那么多女性为了显然对她们毫不在乎的男人而死心塌地,我见过那么多女性为了些许安慰就满意无比。但我现在知道了,一段建立在真正爱情基础上的恋情感觉是那么美妙。那应该给你带来欢愉——不仅仅是偶尔可以,而是大部分时间都这样,它从来不该让你丧失主见、丧失自我或尊严。不管你是25岁还是65岁,爱都应该是全身心投入,然后当你离开时,你能得到更多。
浪漫爱情不是唯一一种值得去追求的爱。我遇到的很多人都渴望着能爱上某个人,能有人把他们从每日的琐事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浪漫的极乐。围绕着他们的有孩子们、邻居们、朋友们,和同样渴望能跟人建立起羁绊的陌生人。环顾四周,注意他们,可能性无所不在。
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就这么让自己敞开心门一下子跳到“爱”上面有点儿压力太大的话,那就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展现你的同情心。不久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地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再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够为他人提供理解、同理心、关切和我坚信的爱。
在危急关头,我总会惊讶地发现人们会用鼓励的话语来支持我。我曾经历过人生的真正绝望——大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绝望,但因为朋友们的爱与恩情,我撑了下来。朋友们问我:“我能做点儿什么来帮你啊?”却并不知道,他们这么问就已经是帮忙了。那些我很熟悉的,甚至跟我素未谋面的人,都曾在我的艰难时刻为我建造了一座支持的桥梁。
我永远无法忘记,当几年前我碰到特别艰难的情形时,我朋友贝贝·怀南斯[18]意外到访。“有些事情我要来告诉你。”他说。然后他便开始唱起我最爱的那首灵歌:“我奉献所有,奉献所有,将所有奉献给您,赐予我的救世主,我奉献所有……”
我静静地坐着,闭上双眼,敞开自己的心去接受这一爱与歌的礼物。他唱完后,我便感到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出来,我就这么满足地待着。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纯然的安宁。
当我睁开双眼擦干泪水时,贝贝正满脸笑容。他开始大笑起来,是那种标志性的“哈,哈,哈哈哈”的笑,然后紧紧抱住我。“妹子,”他说,“我只想来提醒你,你不用孤单一人背这么重的包袱。”
知道人们在乎你的情况,即使你干得并不太好——这就是爱之真谛。能够坚信这一点,我很幸运。
我以为自己很懂友情,直到我跟盖尔·金恩一起开着辆雪佛兰羚羊车花了11天横穿美国。我们从20岁出头时就一直是好朋友,帮助对方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刻,一起度假,一起办我的杂志,但还是能学到关于对方的新东西。
2006年阵亡士兵纪念日上,我们“开着雪佛兰去见识美国”。还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广告吗?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当我们从加州我家的车道出发时,我们大声唱着小曲,还加上颤音,搞得自己笑死。三天后,在亚利桑那州的霍尔布鲁克,我们就只是哼哼两句了。到第五天,在科罗拉多的拉尔马,我们干脆停止了歌唱。
这场旅途非常令人疲惫,每天先是开六个小时的车,然后是八个,然后是十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只有延伸向前方的路。盖尔开车时坚持要一直播音乐,而我想要宁静。“跟我的思绪独处一下”变成了我们的小笑话。当她充满活力地跟唱时,我才意识到她什么歌都会唱。(她几乎把每首歌都称为她的最爱。)这让我神经紧张,就像我开车时的一片寂静会让她神经紧张一样。我学会了要有耐心,当耐心越来越少时,我就买了耳塞。每天晚上,我们抵达一间不同的酒店,筋疲力尽,却还是能大声自嘲。我们嘲笑着我并道的焦虑、我在跨州公路的焦虑、超车的焦虑。哦,还有过桥的焦虑。
当然,盖尔会告诉你我可不是个好司机,而她自己则是个高手,在宾州收费高速上平滑又稳稳地拐着弯,领着我们一路向纽约行进。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进了宾州后,她的隐形眼镜因戴的时间太长,眼睛开始疲惫。我们开进了乔治·华盛顿大桥,正因为总算能结束这场充满了加油站买的奇多和猪肉干的旅行而开心时,暮色降临,夜幕迅速压下来。盖尔说:“我不想告诉你这个,但我看不清了。”
“你说看不清是什么意思?”我试着冷静地问。
“所有的车前灯都有光晕,你看着有光晕吗?”
“不,灯没光晕。你能看到路上画的行车线吗?”我这时已经开始大叫起来,想象着报纸标题:朋友之旅以华盛顿大桥车祸而终结。没地方能靠边停,路上的车都快速超越了我们。
“我对这座桥非常熟悉,”她说,“这能救我们的命。我有个计划,我们开到收费站,我就靠边停,然后摘下隐形眼镜,把框架眼镜戴上。”
收费站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我能做什么?”我几近惊惶地问,“你想要我来掌握方向盘吗?”
“不,我就靠着白线开。你能帮我把隐形眼镜取出来再戴上框架眼镜吗?”她开玩笑地问,至少我觉得她是在开玩笑。
“那样既危险又不可能。”我回答。
“那就把空调开大点儿,我在冒汗。”她说。
我们俩在开车去收费站的过程中都在浑身冒汗,然后我们安全地开进了纽约。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印好了T恤“我活过了公路旅行”。
我坚信的是,如果你能11天跟一个朋友在拥挤的空间里待着,最终都活了下来还能大笑,你们的友谊就是真挚的。
我挚爱的小狗萨蒂如何进入我生活的故事值得一直讲下去。在芝加哥的一个宠物救助站,她抱住了我的肩膀,舔了舔我的耳朵,然后轻声“汪汪”着,似乎在说:“请带我回去吧。”我能感到她把新生活的赌注全部押在了我身上。
我立刻就感到跟她有种羁绊,但想要让我不只是因为狗狗太可爱而一时冲动买下她,盖尔建议:“何不等到明天再看看呢?”所以我决定等上24个小时。第二天,芝加哥有一场大暴风雪——可不是带狗狗回家的好日子,我想着,特别是如果你住在高楼里。即使大太阳天,也很难在77楼训练狗狗——小狗狗刚开始学习何时何地拉屎时需要出去遛很多次。
尽管如此,斯泰德曼和我还是穿上了冬天的大衣,开着大车横跨了整个城,只为“再看一眼”,我如此发誓。萨蒂作为一窝里最小、最孱弱的狗仔深得我心,我最容易被弱者征服了。
一小时后,我们就已经在宠物店了,买了狗窝、尿垫、狗项圈、狗绳、小狗的食物和玩具。狗窝一开始放在床边,就在房子中间,好让她能清楚地看到我——我愿做任何事,只要她离开兄弟姐妹的第一晚不会有分离的焦虑。但她哼哼着、抱怨着,然后开始轻吠。所以我把她从狗窝里抱出来,让她睡到我枕头上。我知道训练狗可不能这样,但还是这么做了,甚至让萨蒂都以为我是她的兄弟姐妹之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已经挤到了我肩膀边,这是她睡觉感觉最舒服的姿势。
在带她回家五天之后,我把理智抛至脑后,被人说服我领养了她的哥哥伊万。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人生是那么美妙:伊万成了萨蒂的玩伴,她就不需要我了。(能从“我扔她捡”和橡胶小兔玩具游戏中解脱真是太好了。)伊万一整天都和萨蒂以及我的两只金毛寻回犬卢克和莱拉一起在阳光下嬉闹。然后他拒绝吃晚餐,接着就开始腹泻,跟着是呕吐和更严重的腹泻。那是周六,到周一晚上,我们都知道他染上了可怕的细小病毒。
我在13年前经历过这个,我的褐色可卡犬所罗门也染上了这个病,那病毒差点儿害死他,使得他在宠物医院住了20天院。得这个病时,他有一岁多,而伊万才11周大,他的免疫系统还没强壮到可以抵御细小病毒。我们把伊万送去急救,四天后,他就死了。
那天上午,萨蒂拒绝吃东西。即便她之前检查是阴性,我还是知道她也染上了细小病毒。于是,便开始了拯救她的尝试。给她输血、注射抗生素、服用益生菌,以及每天探视。我希望美国的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这只小狗得到的医疗条件。前四天,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某个时刻,我告诉兽医:“我已经准备好了让她安乐死,她不用这么努力地与病魔抗争。”
但她却抗争着,接下来的那天她的白细胞数量开始增加。又过了两天,她就开开心心地小口吃着鸡肉了。
又过了几天,萨蒂回了家,虽瘦骨嶙峋、脆弱不堪,但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生活了。最终,她完全康复了。
她和伊万住院期间,我担心极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睡不着觉——就跟任何家庭成员生病时我会有的情况一样。我确信,这就是宠物在我们人生中所代表的一种牵挂——让你会无条件地爱护它们,它们也会无条件地爱你。
狗狗之爱,无与伦比。
你要是把爱他人当成你的人生故事,就永远不会有完结的一章,因为你的遗志会延续下去。你把光借给了一个人,他或她会用它再照亮别人,别人再传递给别人,以此类推。我坚信的是,当我们最终分析自己的人生时、当待做事项已经不再存在、当狂乱已经结束、当我们的电邮收件箱全空了的时候——还能继续有价值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否爱过他人,他人是否爱过我们。
[16]玛丽安娜·威廉森(Marianne Williamson)美国作家,《发现真爱》一书的作者。
[17]拉尔夫·瓦尔德·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美国19世纪思想家。
[18]贝贝·怀南斯(Bebe Winans),美国说唱和灵歌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