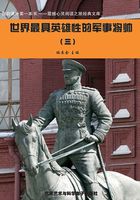“你唯有懂得更多,才能做得更好。”
——玛雅·安吉洛
不论何时,只要我听到保罗·西蒙[42]的那首《生逢其时》的歌,我总觉得他肯定是在唱我。我1954年出生于密西西比州——那个州比联邦其他任何一个州的私刑都要多。我出生时,一个黑人走在大街上什么都没干,就可以让他变成某个白人谴责的对象或某种古怪念头的承担者。在那时,有份好工作意味着为一个“好心”的白人家庭工作,他们至少不会当面叫你“黑鬼”。在那时,《黑人隔离法》大行其道,种族隔离成为主流,黑人教师自己本来就没接受过多少教育,还必须得用白人学校不要了的破破烂烂的教材上课。
然而就在我出生的同一年,改变开始了。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判决黑人有权享有平等的教育。这一判决给了我们一丝希望,所有黑人的人生也许能变得更好些。
我一直都相信自由意志是人类天生的权利,也是宇宙设计我们的一部分。我还知道,每一个灵魂都渴望自由。1997年,当我为扮演《宠儿》里的塞丝做准备时,我安排了一段沿着地下逃亡铁路线[43]的短途旅行。我想要体验一下身为奴隶,在树林里游荡,一步步向着北方、走向冲破了奴隶身份的人生的感觉——这种人生里的自由,在它最基本的程度上,意味着不再有主人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但当我被蒙上双眼带进树林里,然后被孤零零地丢在那儿,自己琢磨到底从哪个方向才能找到下一个“安全的房子”时,我第一次明白过来,自由并不是不再有主人,而是拥有了选择权。
在电影里,塞丝解释着如何成功地完成通往自由的跋涉:“就好像在那之后我更爱(我的孩子们)了,”她说,“又或许是我知道,只要我们还在肯塔基州……他们就不能让我来爱……有时候,我听着我的儿子们,听着他们大声笑着,我从来没听过的那种笑声。起先,我很害怕,害怕有人可能会听到他们的笑声,并因此生气。然后我记起来,如果他们笑得肚子疼,今天他们也只会有这一种疼痛。”她还说,“我会一大早醒来,然后为自己决定今天要干什么。”就好似在想:想象一下,我来决定。
在电影拍摄期间,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这些台词,感受着它们所携带的威力。自那之后的年月中,塞丝的这些话一直伴随着我——我每天都会在这些话中充满喜悦。
有时,它们会是我起床前的第一个念头,我能一大早醒过来,然后自己决定今天要干什么——想象一下,我来决定。那是个怎样的礼物啊!
我坚信,我们都要珍惜这份礼物——要为这份礼物狂欢,而非把它当成理所当然。在我听过全世界那么多残暴行为之后,我知道,如果你是个出生在美国的女性,你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性之一了。攥紧你的好运气,然后将你的人生提升到最高点。你要明白,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就是一种神圣的荣耀,利用好它,栖身于各种可能性中。
我一直都是个很宅的人。我知道,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一点,因为我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但我通常只要一下班就赶紧回家,在7点前吃完晚饭,然后在9点30分前就已经上床了。即使是周末,家里也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正因为我成年后的很多时间都处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对我而言挖出个私人空间就特别重要了,一个庇护所,一个安全屋。
多年前,歌蒂·韩[44]告诉我她创造出了自己的避风港:宣布自己的家是流言蜚语禁入区。作为她在全国性的致力于消除语言暴力的组织“言语可以治愈”工作的一部分,她和家人保证要用鼓励和建设性的语言取代贬低性和伤害性的语言。她选择用能让人提升的语言,与玛雅·安吉洛曾告诉我的一个真理的想法相通,“我很相信负面也有力量——如果你允许它待在你的家里、你的脑子里、你的人生中,它就会控制你,”她说,“那些负面的词语会爬进木制品中、家具中,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它们附着在你的皮肤上。负面的话就是毒药。”
我本人亲身经历过负面语言的巨大杀伤力。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小报开始报道关于我的很多不实之词。我为此绝望极了,觉得自己完全被误解了。我浪费了很多能量去担心人们会不会相信这些谎言,我得努力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才不打电话给那些中伤我的人来保护自己。
这是在我还不知道现在所坚信的这一点以前:当有人散播关于你的谎言,其实重点根本就不是你。从来都不是。流言蜚语——不论是横扫全国的谣言,还是朋友间的牢骚话,都只反映了那些造谣者自己的不安全感。通常,当我们在别人背后做出对他们的负面评价时,都是因为我们希望能感到有力量。而这,又通常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觉得毫无力量、毫无价值、没有勇气去坦诚相见。
伤人的话会发出这样的信号——既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我们分享流言蜚语的人——我们不值得相信。如果有人很愿意把一个“朋友”说得一无是处,她又为什么不会贬低另一个呢?流言蜚语说明我们还不够勇敢,能够直接跟我们看不顺眼的那个人对话,所以我们便贬低他们。剧作家朱尔斯·费弗[45]把它称作犯了小小的谋杀:流言蜚语就是胆小鼠辈的刺杀行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沉迷于流言蜚语的文化中:谁穿着什么衣服,谁在跟谁约会,谁被搅进了最新的性丑闻……如果我们把家庭、人际关系和人生都变成流言蜚语禁入区,那将会怎么样?我们大概会很惊讶这让我们有了多少时间去做最重要的工作——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不是毁掉他人的。我们会往家里注入真实的精神,让客人们想要踢掉鞋子多待一会儿。而我们会记起,虽然言语有摧毁的力量,但是它们也有治愈的力量。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讽刺,因为我一直都不怎么喜欢看电视,在《玛丽·泰勒·摩尔秀》停止播出后,除了《格里菲斯秀》的重播之外,我基本上不会按时追看喜剧片了。在家里,我跳过晚间新闻,因为我不想在睡觉之前接收所有的那些负面能量。而在度假时,我房间里很少有电视。在我拿着遥控器换台的那些时候,也几乎能肯定可以找到至少一个节目正在讲针对女性的性剥削或暴力。
在我开始主持电视节目时,我的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些毫不负责的节目——一切都以“娱乐”的名义。有一天,工作人员和我安排了对一个淫秽丑闻被爆出来的丈夫的采访。就在我们的舞台上,在数百万观众的注视下,他妻子第一次得知自己的伴侣对她不忠。那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刻:那女人脸上的耻辱和绝望令我自觉惭愧,我不该让她身处那样的位置。那时那刻,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要成为一个会降低别人人格、羞辱或贬低另一个人的节目的一分子。
我坚信,我们老想着的内容就是我们会变成的样子——一个女人思考着,她便存在着。如果我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吸收那些不能反映我们之出色的形象和信息,难怪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机和活力被抽干了呢。如果我们每周都看着几十种不同的残忍行为,也就难怪孩子们会把暴力当成一种可行的手段来解决冲突。
成为一个你想要看到的改变了的人——这就是我的人生信条。不要贬低,要提升;不要摧毁,要重建;不要误导,要照亮前路,这样我们所有人才能站到更高的境界。
我坐在胡珀先生的五年级算术课上,为即将来临的小测试担心不已。突然,校内广播通知大家去小礼堂听一个特别嘉宾的演讲。“太好啦!我得救啦!”我告诉自己,琢磨着今天总算不用再听算术啦。
当我和同班同学排成一列走进礼堂时,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成功脱身。我坐在椅子上,准备在又一个集会里被闷到睡着。但他们介绍的嘉宾是杰西·杰克逊牧师,他是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时正站在他身边的人权领袖。我坐直了身子。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会听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
那是在1969年,因为我的成绩还不错,便以为自己了解了要尽全力做到最好的重要性。但那天,杰克逊牧师在我心中点燃了一把火,让我改变了看待人生的方式。他的演讲内容是那些为我们所有人——不论我们的祖先来自何处——做出的个人牺牲。他谈到那些我们之前逝去的人,那些人为我们铺就了道路,让我们能坐在纳什维尔一个不分人种的高中里。他告诉我们,我们欠自己的,是卓越。
“卓越就是最有效阻止种族歧视的方式。”他说,“所以,要追求卓越。”
这一切我都记在了心里。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就找到了一些纸张,然后做了个写着他名言的海报。我把海报贴在镜子上,它一直都留在那儿,直到我读完大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格言——“想要成功,你就得卓越。”“如果你想要世界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那就为世界奉献最好的你。”
这些话语帮我克服了很多障碍,甚至是无须卓越就能做成的那些事。直至今日,卓越都是我的目标,在我的馈赠中卓越,在我的和蔼中卓越,在我的努力中卓越,在挣扎和麻烦中卓越。对于我来说,卓越就意味着永远做最好的自己。在堂·米格尔·路易兹的《四个约定》这本书中,最后的约定就是这个——永远都做最好的自己。我坚信,这就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最好道路。“最好的你每天都不一样,”路易兹说,“一切取决于你感觉如何。”但无论如何都要以最好的你来面对不同的情况,这样,你就没有理由批判自己,并制造出内疚和羞愧了。好好活着,这样每一天结束时,你就能说:“我做到了最好。”这就是卓越的真意,在活出你最好的人生这项伟大工作中的真意。
我父亲教导我,欠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我们家里,这几乎算得上是人格缺陷了,跟懒惰和他所谓的“轻浮”差不多。所以,当我离开家自己住后一年就欠下了1800美元的债务时,我觉得自己失败了。我从来没告诉自己的父亲,更不会有胆量找他借钱。
于是,我以21%的高利率借了一份综合贷款,吃了很多葡萄麦麸当晚餐,买了自己能付得起的最便宜的车——安了轮子的桶,我以前曾这么叫它,但它能送我上下班。我交了10%给教会,然后一年只买一次衣服。
还完了那1800美元之后,我便发誓再也不要制造自己负担不起的账单,我真的恨死了花太多钱的感觉。
我父亲存钱买一切真正重要的东西:一个洗衣机、一个烘干机、一个新冰箱。在我1976年离开位于纳什维尔的家时,他都还没买电视机,他说他的“钱不太对”。当《奥普拉脱口秀》全国播映时,我给他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现金付款的一台彩电。
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活在债务中,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对上了我节目的夫妇,他们谈到了他们的经济困境。才结婚九个月,他们的婚姻便已经因为巨大债务的重压而摇摇欲坠。他们海滩婚礼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墨西哥,为有些客人付酒店的房钱和水疗费用、婚礼晚餐上的龙虾和特等菲力牛排,还加上大量酒水。在这个充满祝福的婚礼背后是高达5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这还不算丈夫从自己的养老金里面拿出来买订婚戒指的9000美元。对童话周末的追求让他们陷入了一场将会持续数年的噩梦中。
我坚信,如果你用你能得到的东西来定义自己,而不是去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才能开心满足,你不仅是超过自己的限度活着,或过度拉伸自我,你其实是活在谎言中。
可见,背着账单的重负是多么痛苦。因为你对自己不够真诚,当你把自己从债务中解放出来,便创造了空间让你能带着目的去购物——为你的人生添加有意义的事物。
我直到现在买东西前都会三思。这东西跟我已经有的搭不搭?我是不是一时冲动?这玩意儿是不是真的对我有用,还是只不过挺好看的?我仍然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在一家古董店里,店主给我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18世纪的梳妆台,带着镜子和隐形抽屉。它被打磨得那么闪亮,那樱桃木看着就像在震动。我站在那儿,考虑着到底要不要买它时,我跟那人说:“你说得对,它真漂亮极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但我真的不需要一个花里胡哨的梳妆台。”他装模作样地倒抽一口气回答道:“夫人,没人在这里买东西是因为他们需要它,这是用来享受的财宝。”的确如此。好吧,让我回到“必需品”店里,我想,因为我真正在寻找的是壁炉用具。我不仅不需要一个梳妆台,也根本没地方放它。
公平地说,店主先生说得没错——有些东西就是用来享受的财宝。
但我坚信,只有当你没有太过挥霍时,才会更加享受一切。以下就是何时你会知道自己买东西很明智:你买回家一件东西,一点儿也不后悔,不管你买的是什么,买回去十天之后,你比刚买的时候还为这东西高兴。
1988年,我在蒂芙尼店里想要决定到底买哪个花纹的瓷器。我犹豫不决了很久,最后,陪我购物的人说:“你干吗不两套都买啊?反正你买得起。”我还记得自己想着:“老天啊……我买得起,我买得起,两套我都买得起!”我就在店里好像中了大奖似的开心得蹦蹦跳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