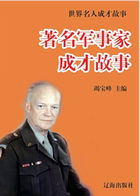/陈依妮
(一)
第一次见老鼠的时候,她还留着长头发,长得匪夷所思。她在讲台上煞有介事地做自我介绍时,半米长的马尾随着丰富的肢体动作左右摆动,让我不禁联想到骨瘦如柴的老道士手里那根装模作样的拂尘。
她用带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普通话自我介绍说:“各位同学好,我叫卢晟,然后因为我很黑,你们可以叫我老鼠。”尽管那时的我一直纠结于“黑”和“老鼠”之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因果关系,但我觉得她挺酷的。不仅仅是因为在那个女孩们都开始用洗面奶,希望自己看上去更天生丽质的特殊时期,她对于“黑”这件事表现得相当坦荡。更重要的是,虽然同为十七岁根正苗红的好青年,但显然她在身高上开了外挂,所以这种仰望的特殊视角让我每次看她的时候都会觉得格外神奇与自在。
(二)
和老鼠成为好朋友是挺偶然的事。
班里那时有个姑娘叫周洁,长得算不得漂亮,但莫名地招人喜欢。班上一半的男同学都在暗地里喜欢着同一位女孩。当时她跟我关系最好,但说真的,我打心底里恶心她。在别人眼里恰到好处的礼貌和慰问常常在我这儿成为厌恶的根源。但我这人特没主见,每次周洁温柔地拍拍我的肩膀细声细语地说:“程遥,咱们一起去食堂吧。”我就会马上为自己阴暗的想法内疚到不行。但谢天谢地,估计是老天爷也不想再让我憋屈下去了,他特地派班主任把周洁喜欢的男生调到了我的座位后面,而就在那个男生试图用“日久生情”这一说法来感动我的同时,我与周洁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
只记得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回的寝室,走到半路时,身后传来风风火火的脚步声,还有双肩包里课本胡乱碰撞的声响。我回过头,看到老鼠咧着嘴巴向我挥手示意。我一直觉得她是那种出场自带背景音乐《上海滩》的人,说白了,就是那种又土又嚣张的感觉。她跑到我身边后,一把勾过我的肩膀:“程遥,就算全班人都跟周洁一样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说话间握着我肩膀的手用了用力。我抬头看她,就算在灯光下她还是黑得无可救药,但厚刘海下的那对小眼睛却闪烁着理性正义的光辉,大概为了显示自己的真诚,她特地冲刚经过的周洁翻了个巨大的白眼,那一刻我觉得她更酷了。
为了回应老鼠的表白,当天晚上熄灯后我向她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于是我们在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床上艰难又艰难地度过了一夜。我们从周洁体育课上露出的白色背心带子聊到英语老师枣红色的碎花打底裤;从学校食堂最难吃的小黄鱼再聊到柏原崇粉红的嘴唇。在短短几小时内以不可置信的速度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要非得给那个夜晚来点传奇色彩的话,一定得是窗外的天空。我的床位正靠近窗口,又因为是上铺,一侧身就可以看到半边天和学校尚未修建好的塑胶跑道。那是记忆里少有的漫天繁星的夜晚。总觉得每颗星星之间的距离都是恰到好处的,光亮由无数的小光点汇聚起来,流淌,一直流到夜色最浓处。细碎温暖的光点闪亮在天边,水泥地上,老鼠的睫毛上弯。她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枕着星光入睡,显示出少有的可爱。我掖紧了被子,艰难入睡。半夜依稀觉得有人抚弄我的刘海,许是做梦了。
(三)
和老鼠成为好朋友不久,她剪了短头发。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喜欢上了技校一个姓王的男孩,那个男孩高高瘦瘦,留着刘德华式短发。总之,都恰巧避开了我的特质。我对于她口中不明所以的王小伙以及忽然剪短发的行为一致报以不看好的态度,而她每次都会将那头短得难以置信的头发甩得更用力作为对我的控诉。我在洋溢着薄荷味洗发水的空气里翻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白眼。
老鼠剪完头发没多久,冬天就来了。这个冬天以势不可挡的架势侵袭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老鼠患有严重的鼻炎和关节炎。所以一整个冬天她都在不停地接热水,喝热水,吸鼻涕,擤鼻涕中度过。我偶尔回过头看看她,就会发现她蜷缩在厚重的橙色羽绒服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脑袋。大多时候她都呈放空状,只有少数时候会冲我摆摆手,为了证明她没有被这恼人的冬季杀死。
好在这个冬天虽然气势汹汹却十分短暂。虽然我过得比老鼠好不到哪里去,然而脱下冬季校服时仍有种意犹未尽的滋味。气温开始回升,英语老师早早地换上了大红色开衫和嫩绿色碎花小短裙,随着窗外吐绿的新芽,老鼠也渐渐恢复了生命力。最起码她能一边擤鼻涕一边用奇形怪状的词汇形容她一整个冬天不堪回首的遭遇。她时常俯下头趴在我肩膀上有气无力地说:“程遥,等我感冒好了,带你去拯救世界。”这个时候我往往会一把把她的头推开:“滚。”
令我没想到的是,在某个不起眼的放学后,她兴冲冲地拽着我抄小道溜出学校,从五里巷的汽车维修铺子里推出一辆苟延残喘的摩托车,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表情,扬扬得意道:
“敢不敢?”
“疯了吧你,晚上班主任驻班!”
“靠,你怎么什么都不敢啊。”
于是我的大脑在那几秒内进行了几百万次的高速运转,分析了各种利弊突发状况以及可能的后果之后,我快速地跳上了摩托车后座:“你他妈赶紧的!”
(四)
后来我每每回忆起那个原本无聊到让人生厌的下午,老鼠带着我穿行在白川的巷子里。我把头趴在她背上的时候才发现她是真的很瘦,我甚至怀疑透过那层薄薄的皮肤就可以听到她血液里流淌的不羁与悲伤。风钻进她的校服里,吹得胀胀的,让她看起来像一根蓝色的真知棒。我从后视镜里看她,额前稀疏的刘海在空气里无助地飘摇。因为鼻炎未彻底痊愈,她一下一下地吸着鼻涕。鼻头泛着羞怯的红色。这个时候把画面交给王家卫就好了,他一定比我更懂怎么把光线和老鼠的脸柔和地融在一起,或者给她鼻梁投下的阴影和紧抿的嘴唇来个特写,怎么说都有种世纪末的悲怆味道。
她带我到了普江。
那个时候普江还只是白川最南端一个静谧遥远的存在。政府刚下达政策,准备大刀阔斧地改造这一带,发展成为白川最具特色的商业中心。然而现在她只是被一些没有人情味的警示牌重重叠叠地包围着,依然散着沉着婉转的美好。灌了几十分钟的风后,我有些头昏脑涨。彼时天已经义无反顾地黑了下来,只有江上的汽船在亮着疲惫的灯火。
老鼠从摩托车后座下面抽出两听啤酒和一袋麻辣凤爪,拉着我穿过警示牌,坐在江边的堤坝上。
“要不要?”
她摇了摇手里的啤酒,我接了过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酒。黄色新鲜的气泡在口腔里爆炸,泡沫在唇齿间流转后混着唾液奋不顾身地淌进胃里。金属罐的冰凉透过皮肤混到血液之间,特别冷。说真的,太难喝了。但为了不让老鼠扫兴,还是干完了半瓶。
“别光顾着喝啊,吃,我的最爱!”说话间她就抓起一只凤爪直往我嘴里塞。
就着半江的月色,和着啤酒与清风以及粗糙的麻辣凤爪,不一会儿我就饱了。
转过头看老鼠,她在略带寒意的春风里一边咕噜噜地喝着啤酒,一边猛烈地吸鼻涕。还不时在颤抖间吐出几个“爽”字。总算喝完后,她意犹未尽地咽了一口口水,手里把玩着空啤酒罐,然后呆呆地望着江面,也不说话,像消失了一样。
我看到红的黑的黄的灯,空气里流转的告别与不安,普江里翻腾的春意,都一齐撞碎在她的眼睛里。我这时才发现,她一直比谁都孤单。
“程遥,你过来一下。”
我把头凑了过去,没想到她在我的脸颊上飞快地留下了略带醉意的吻。
“靠,有病吧,干吗亲我!”我一拳打在她的背上,她被猝不及防的袭击吓得直咳嗽,又冲我翻了个白眼:“不至于吧。”我没理她,望着自己有气无力地耷拉的脚发呆,老鼠揉了揉自己的后背,也陷入了沉默里。
“老鼠,这种时候要是有热牛奶喝就好了,小时候那种,橡皮塞,玻璃瓶。”我转过头,呆呆地望着她头顶的灯火。
“神经病。”她说。
回去后可想而知,一向对我器重的班主任第一次在我面前说出那些让人尴尬的词汇。而老鼠则一个劲地道歉,仿佛这件事是我被逼无奈一样。原谅那时的我自私又怯懦,于是把过错也顺理成章地推到她的身上。回宿舍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直到熄灯后,老鼠悄悄钻进我的被窝里:“程遥,你别不理我。”
后来我们也有很多的争吵。我对成绩的在意以及处事的圆滑常常惹来老鼠的鄙夷。而每当她兴致勃勃地跟我说起她校外的朋友们以及他们彻夜地喝酒和飙车时,我也会大发雷霆。但我们每次都会和好。我们彼此撕扯又抚慰对方的伤口。最后在每个闪亮沉默的夜里相拥入眠。
(五)
高三以后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几乎与英语老师的换衣频率成正比。
交好的同学间开始互相交换理想的大学,再彼此加油打气。空气里多了些焦虑和凝重,光看着作业栏上的习题量就让人瞠目结舌了。每个人习惯性地故作轻松地开玩笑,却都在暗地里努力复习。除了老鼠。
她照例在每个没有老师的晚上溜出学校在白川的各条街上游荡,和她的朋友们谈笑,说着低俗的荤段子,灌下一杯又一杯的酒精,她管这叫自由。因为家底厚,任课老师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英语老师毫不买账。在一次她抛出一个连我都不会的英语翻译后,从容地说:“卢晟,你起来回答一下。”老鼠表现得相当坦然,她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后,一字一顿地说:“我不会。”“不会?不会你上课都在干什么,叫你到学校里是让你玩的啊,你这人有没有羞耻心啊?…….”终于在英语老师吼出那句“要上就上,不上就滚”后,老鼠摔门而出。只留下兴奋的英语老师骂骂咧咧地没完没了,我捂着心脏,觉得它随时都会从我口腔里跳出来。
在那之后我就没见过老鼠,她就像一年前忽然转学到我们班一样,而现在,她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座位上的书还是老样子,我一度觉得有一天老鼠会忽然从后面跑上来,从容地勾过我的肩膀,用她毋庸置疑的自信口吻说:“程遥,吃饭去。”
再见到老鼠就是两个月后的事情了。那天我在校门口的光荣榜看月考排名,正为自己不尽如人意的成绩暗自难受时,听到校门口传来“程遥程遥”的呼唤声。接着我就看到了老鼠。她示意我轻点过去,我望了一眼正在打盹的门卫,心领神会。然而我看着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从包里掏出一瓶牛奶,塞到我手里。
“程遥,我刚刚还准备抄小道溜进来,结果发现居然封了,想试试运气,没想到咱俩心有灵犀啊,哈哈。”“其实我早就不想读了,还要谢谢英语老师呢,对了,我现在在普江,就以前咱俩去过的那里,在旁边的一家店打工,闲职,反正我家有钱,就当玩。”“不过我最舍不得你了,你看你这么矮,抢饭怎么抢得过别人……”
阳光里我看到她穿了一双黑色的高跟鞋,闪着廉价细腻的光泽,头发虽然还是这么短,却染成了暗红色,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她依然那么瘦,又或许比以前更瘦了,我不太清楚。
“喂!那边的,在干吗?”门卫指着老鼠,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老鼠作势要开溜,她加快了语速:“程遥,有空,哦不对,高考,高考后来普江找我,我带你玩遍白川所有好玩的。”她向我挥了挥手臂,最后踩着高跟鞋,迈着那样熟悉的步伐,在无数次的回头后,最终消失在了浓重的夕阳里。
“那个女同学,把你手里的东西拿来,校外人员的东西不能拿。”年老的门卫用半带威胁的口气说道。我死死攥着,不忍脱手。“跟你说呢,快点。”说着就要夺过,我试图护着那瓶牛奶,牛奶瓶却在争夺间脱手,撞在地上,粉身碎骨。“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门卫恶狠狠地瞪着我,念叨着转身去拿扫把。我望着白色的液体渐渐濡湿那一片水泥地,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很久以前,老鼠也在夕阳里留给我过一次挥手。那是一次我最痛恨的八百米测试。老鼠一直遥遥领先,却在最后关头停住,她在夕阳里冲我挥了挥她的长手臂:“程遥,快点!”我抬起头想捕捉她的身影,却被阳光刺痛了双眼。
(六)
高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弥漫着绝望和新生的气息。
走出考场的时候还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我闭上眼揉了揉太阳穴,想着等会儿搭11路车去普江,不知道那里的夏日是不是也这么美丽又倦怠。
再睁开眼却看到了柏油路对面的一个女孩儿,她就这么站着,自由又美好。然后她冲我挥了挥手臂:“嘿,程遥。”
说真的,我觉得我们从未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