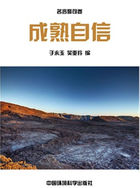铜剑、铜矛上的巴蜀符号
铜鍪盖上的巴蜀符号
六七十年前,自从这种神秘的图符现身以来,它在考古人员的视野中就频繁出现。这种图符几乎伴随每一项巴蜀考古的新发现,充斥着各种不同的铜器和漆器。起初,这些图符仅被当做美化器物的图案,它的意义也仅限于装饰而已。随着新发现越来越多,巴蜀图符的种类愈益丰富,渐渐地,人们被图案所蕴涵的丰富意义所震惊,这些图案展现了多彩的古代巴蜀精神生活。
考古学家们指出:弯曲的图符不同于通常所见的装饰纹饰。因为纹饰是已经演化成了抽象的、规范化了的图像符号,可以令使用和观赏者产生美的感受。而那些堆积成“巴蜀图符”这座金字塔的众多构成分子,对称、均衡、节奏、韵律、连续、重叠、反复、一致等纹饰组合中常见的形式规律,在这里基本被摒弃。巴蜀图符侧重于体现古人的观念和想象,其组合往往不讲究构成美的通行法则,人们观感中的初步印象往往是杂乱无章,无主从疏密,无变化节奏,与同一时期的中原纹饰迥然异趣。正因为如此,这些图案被有的学者称为“巴蜀符号”。
但是另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巴蜀图符是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自己语言的工具!还有人甚至认为,巴蜀图符不仅是文字,而且是已有音符或意符之分的进步文字!因此,这部分学者给巴蜀图符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巴蜀图语”。
在巴蜀图符中,虎、鸟等动物以及其他植物,甚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品等形象,经过一定的艺术化处理,都成为进入这个体系的元素,总之,那些图案中的大多数是象形的,但许多又仅略具其意,要真正确定它的摹仿对象又是很难的。巴蜀图符,就在像与不像之间,带给了我们太多的疑问、思考和想象!
巴蜀图符大多存在于春秋晚期至战国,自那以后,这些图符随着巴蜀古族的消亡和汉化而突然消失,失去了踪影。二千年后,当它们再度显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再能认得它,有的只是揣测和联想。而近几十年来,巴蜀图符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对于它的意义,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赞同。看来,巴蜀图符之谜还需要寻找一条通往谜底的路径。这条路径在哪里呢?
汉字被称为象形文字的代表,大多数字都有自己的音、形、意。然而我们追溯汉字的起源,则发现它虽然也有象形的对象,但已高度抽象了。在目前所见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中,像巴蜀图符这样的图画式文字几乎不见。古文字专家说,甲骨文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看来,要从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汉字来解读所谓的“巴蜀图语”是死路一条。
与巴蜀图符相像的文字,在远隔几万公里远的古埃及被发现。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有了文字,他们的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古埃及的文字就像一卷连续不断的图画,人们在阅读时,根据那些飞鸟走兽、山川日月等形状的图案就能大致知其意义。古埃及人非常重视文字的功能,他们把咒语、誓词、赞歌以象形文字的形式涂刻在墓葬内,并相信这些文字就具有它们所承载的内容的力量。但是,古埃及文字就像巴蜀图符一样,在使用了上千年后,也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代的人们之所以能够释读古埃及的天书,得益于一把打开迷宫大门的钥匙罗塞达碑。这块碑是1799年法国入侵埃及时在尼罗河三角洲发现的,当泥土拂去后,上面刻写的三种文字浮现出来。其中前两种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俗体字,第三种是古希腊文。当时,法国有一个青年学者叫商博良,他是专门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和文化刻写于公元前2世纪,上面写着为埃及国王歌功颂德的赞歌。但是,要问那些埃及象形文字怎么读法,他可一筹莫展了。后来,商博良发现,古代埃及人书写国王名字的时候,都要加上方框,或者在名字下面画上粗线。罗塞达石碑上,也有一些用线条框起来的文字,这是不是国王的名字呢?又经过一番探索,商博良对照希腊文,从象形文字中认出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和王后克娄巴特拉这两个人名。这样,他就知道了12个象形文字的读音。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商博良继续努力,终于在1822年揭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原来,这种文字中,有的符号代表的是一个词,有的表示一些字母的结合。还有24个符号,具有现代字母的意义。全部符号有700多个。
从商博良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或许能够启示我们,如何去寻找一把让“死亡文字”再生的钥匙。但是,巴蜀图符毕竟不能和相隔万里的埃及文字相比拟,巴蜀图符的“罗塞达碑”迄今亦未发现。
虽然巴蜀考古学家们似乎没有做商博良那样的探谜者的机会,但是商博良的故事提醒他们,从活文字入手,是解读死文字的关键!
经书、春联、条幅上的冬巴文
有的研究者似乎寻找到了与巴蜀图符相关的活文字的蛛丝马迹。我国云南的纳西族至今仍在使用着一种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主要是由东巴教的巫师们所掌握,故被称为“东巴文”。东巴文很接近巴蜀图符,它是用“图组”提示,由巫师念诵的“图画韵语”。
研究者十分惊奇地发现,在简单而为数不多的东巴文字中,竟有20个单符与巴蜀图符相同,加上一些相似的图符,这样的比例是很高的。这似乎不能用巧合来解释,研究者铜钺上带“王”形的巴蜀符号,有人认为这是巴人上层贵族的标志推测,两者之间可能具有某种联系。在历史上,纳西族、彝族和古代巴人、蜀人的祖先当中,都混合有一定的西部氐羌成分,或许这样一种文化血脉联系,是造成他们文字相似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巴文可以连续书写,表达完整的句意,又是与巴蜀图符不同的地方。巴蜀图符往往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单符,缺少连续的符号,它能起到文字的表达功能吗?在东巴文中,那些与巴蜀图符相同的字,如表达“月”、“好”、“盐”、“护手”等文字,在巴蜀图符中很少单独存在,往往与其他图符相组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假使我们认为在东巴文中的这些单符意义,同样适合于巴蜀图符,它的内含会淹没在众多的图符中吗?
专家们统计,巴蜀图符的单符共有200余个。若以这么多的单符相组合,那么构成一个文字系统应当绰绰有余。但它们大多数是具体的实物图像,没有动词、形容词、连接词等词汇,似不能构成文句和篇章。所以有的人认为,巴蜀图符是一种看图像以解语意的图画寓意符号,简单地说,就是看图说画。这些画以一种望文生意的状态存在着,是一种由巫师诵读的韵语、成语、诗剧或吉祥谚语、历史典故。
这样,关于巴蜀图符之谜的解释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对于主张“巴蜀符号”的研究者,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巴蜀图符是文字!
在有关古代巴蜀的典籍中,研究者们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这段记载描述了远古巴人、蜀人在识读上的低能。也许,他们当时仅靠记忆来维持重庆地区出土的各种巴文化铜印章和传承民族文化,至多,也不过是画图记事!巴蜀图符大多铸刻在兵器上,即使是钟、于和钲这些乐器,在先秦时也多用于战争。因此,著名巴蜀文化专家孙华教授认为,刻在兵器上的巴蜀符号“应当是一种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使使用者免于受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杀敌。”巴蜀图符还大量发现于铜玺印上,玺印在巴蜀文化中十分盛行。孙华指出,铜玺印上的图形符号的种类变化不大,不同之处只在于这些图形符号彼此之间的位置,以及图形符号的多寡。所以,印章上的图符应是族徽的标记。
部分印章印面
“朐忍”、“灵叉”、“陬媀(z侪uy俅)”、“彭排”、“不律”……这些陌生而怪异的词汇,现代人闻所未闻,它们分别对应着“蚯蚓”、“大龟”、“鱼”、“木盾牌”、“笔”的意思。这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少琴先生,从散见于各种古代典籍中,收集整理的早已消失的巴人语言词汇。作为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是一个重要的标识。秦国统一巴蜀后,首先从语言文化上对巴人和蜀人进行改造,他们推行一系列政策,让巴蜀人民“能秦言”,从一个侧面说明巴人和蜀人原本是有自己的语言的。对于两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古国、古族,如果没有可以记录文化、传达政令的文字,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国家是怎么运转的。
罗家坝出土印章:中间似为宫殿,两侧似大树或立柱,另外还有星、月等图案此印章下部为二人扛罍
上部中间似甲胄,两侧为铜铎,反映了战国时候巴蜀地区大户人家的礼仪生活1972年的一项发现使许多人重新生起了存在巴蜀文字的希望。这一年,四川郫县红光公社的独柏树出土了一件虎纹铜戈,这件铜戈上面不但有巴蜀图符,而且还铸刻有一行看起来颇像文字的符号。这些“文字”约有十余字,它与一般的巴蜀图符完全不同,线条是构成这些字体的基本元素,它们简洁、流畅而圆润。紧接着在1973年,重庆市博物馆在万县新田公社又收集到了一件戈,上面的文字风格与独柏树的完全相同。同样的发现后来在四川新都县、重庆云阳县等地多次出现。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仔细研究了这些文字,他把这些脱离了象形而走向符号化的符号称为“巴蜀文字乙”,而把那些所谓的“巴蜀符号”称为“巴蜀文字甲”。李学勤的意见无疑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尽管他仍没有找到释读“巴蜀文字乙”的钥匙。
铜戈上的“巴蜀文字乙”
种
巴蜀符号描摹图
“巴蜀文字乙”与当时的中原文字在结构、形态、造字方法、书写等方面非常接近。从附着器物的年代看,不早于战国中期。或许在那个时候,列强环视巴蜀,巴蜀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益密切,自身内部的商品贸易、人员流通等也得到较大发展。那种仅由巫师掌握和使用的图画式的记事方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些对中原文化有所了解、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或许摹仿成熟的中原系文字,创造了巴蜀人民自己的文字。
历史上,学习摹仿汉字,创造自己文字的国家并不少。“巴蜀文字乙”也不例外,它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巴蜀的文化发展。但是,“巴蜀文字乙”是一种短命的文字,大概在它诞生不久,巴蜀两国就屈服在了秦国的铁蹄之下,“巴蜀文字乙”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基础,带着尚未成熟和推广的遗憾,消失在了强大的秦文化的汪洋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