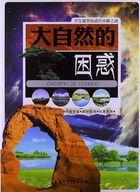八月,湘莲才进了京,先见了病倒在家的薛蟠。薛姨妈也不念旧事,只感救命之恩。又说起亲事,凡一应东西皆代置办妥当,只等择日,湘莲感激不尽。
次日,来见宝玉,将路上之事说了。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和你般配的人。”湘莲道:“如何只想到我?我平日和他交往并不深,他怎么如此关切。路上忙忙地定下,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礼。所以想向你细问个底里才好。”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得了个绝色的,何必再疑?”湘莲道:“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她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妹子,真真一对尤物!——她又姓尤。”
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说着告辞出来,一路来找贾琏。贾琏忙迎出来,让到内堂,和尤老娘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诧异。
吃茶时,湘莲说:“客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订了弟妇。如今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是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剑是祖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贾琏听了不自在,便道:“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湘莲笑道:“弟愿领罪,但此事肯定不敢从命。”
那尤三姐在房内听得一清二楚。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什么,把自己也当做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她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后,出来便说:“你们也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给湘莲,右手回肘,只往脖子上一横,可怜:
揉碎桃花红满地,
玉山倾倒再难扶!
当下吓得众人急救不迭。湘莲反不动身,哭道:“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没福消受。”他扶尸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眼看着入殓,又抚棺大哭一场,方告辞而去。这湘莲昏昏默默,信步来到一座破庙,取出那股雄剑来,将万根烦恼发丝一挥而尽,不知往哪里去了。
再说贾琏偷娶尤二姐的事一直瞒着凤姐。一日,有小丫头告诉平儿,她在二门里头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不知是谁,吆喝了两个一顿,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快悄悄儿的!叫里头知道了,还不把你的舌头割了呢。”平儿连忙对凤姐说了。凤姐亲自审问贾琏的贴身小厮,知道木已成舟,贾琏已给尤氏在府后置了新房子。凤姐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原来贾琏要去平安节度处办事,凤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贾琏前脚走了,回来便命人收拾东厢房三间,依照自己正室一样装饰陈设。十五日一早,只带了平儿、周瑞媳妇等四人,由兴儿引路,一直到府后新房门前。兴儿叩门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尤二姐虽也吃惊,但人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迎。凤姐下了车进来,二姐忙迎上来拜见,张口便叫:“今儿实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求姐姐宽恕!”说着便拜下去。凤姐忙赔笑还礼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儿的手,同入房中。凤姐在上坐,二姐儿又行礼,说:“妹子年轻,凡事求姐姐指教。”
凤姐忙下座还礼,说:“我也年轻,只知一味劝二爷保重,别在外边眠花宿柳。如今娶了姐姐做二房,这样正经大事,却不曾和我说。我也劝过二爷,早办这件事,果然生个一男半女,连我后来都有靠。不想二爷反认为我是那等妒忌心重的人,私自办了。现在可巧二爷走了,所以我亲自过来拜见。还求姐姐体谅我的苦心,起动大驾,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处,合心合意地谏劝二爷,谨慎事务,保养身子,这才是大礼呢。要是姐姐不肯去,我也情愿在此相陪,每日服侍姐姐梳头洗脸。”说着,呜呜咽咽哭将起来。
二姐儿是个实心人,便认做她是个好人,心想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也是常理。于是倾心吐胆,说了起来,竟把凤姐认做知己。又道:“今儿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这几个箱柜也不过是二爷的。”凤姐听了,催着二姐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车。凤姐又悄悄告诉二姐儿:“我们家的规矩大。如果老太太、太太知道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我们有一个花园极大,姐妹们住着,轻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先在园子里住两天,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时才妥当。”二姐儿道:“任凭姐姐决定。”她俩下了车,凤姐赶散众人,带了二姐儿,悄悄地求李纨收养几天。二姐儿得了这个所在,又见园里姐妹个个相好,倒也安心乐业。
这日,凤姐带人来到宁府,走进上屋。尤氏迎出来,见凤姐气色不善,忙笑说:“什么事情,这么忙?”凤姐照脸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你就是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统才是。你痰迷了心,油脂蒙了窍!国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来!这会子被人家告我们,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厉害、吃醋。如今咱们两个同请了族人,分证明白,给我休书,我就走!”一面说,一面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只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儿。众丫头媳妇等已黑压压跪了一地,赔笑求道:“二奶奶最圣明的。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如今还求奶奶留点脸儿!”
凤姐冷笑道:“你也和我过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才是。”尤氏拉凤姐讨主意,凤姐又道:“我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凭人撮弄我,我还是一片傻心肠儿。得,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我只领了你妹妹去给老太太、太太叩头,只说原是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愿意娶来做二房。仗着我这张不害臊的脸,死活赖去,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了!”尤氏感谢不尽。
那贾琏完事回来,先到新房去,只见静悄悄地关锁着,问起缘故。只有跺脚长叹。见了贾赦,将所完之事回明。贾赦十分欢喜,夸他中用,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头名唤秋桐的,赏他为妾。贾琏叩头领去,欢喜不尽。见了凤姐,未免脸上有些愧色。谁知凤姐反不似往日模样,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温。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脸上又有些得意之色。
凤姐听了,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到那边接了来。这真是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但她随即有了主意,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妹妹的名声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来往太密,‘没人要的,你捡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话,气得什么似的。打听是谁说的,又查不出来。”结果,凤姐自己先气病了,茶饭也不吃。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讽刺。
再说秋桐自以为是贾赦所赐,连凤姐、平儿都不放在眼里,哪容那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尤二姐,处处给她难堪。二姐儿淌泪抹眼,又不敢抱怨凤姐——因凤姐并未露一点坏形。而贾琏有了秋桐,就似一对干柴烈火,如胶似漆,在二姐儿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
凤姐虽恨秋桐,又喜借她先可发脱二姐儿,用“借刀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她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她三分,你去硬碰她,岂不是自寻死路?”秋桐听了这话,骂道:“奶奶素日的威风怎么都没了?让我和这娼妇做一回,她才知道呢!”
那尤二姐原是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不过受了一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渐黄瘦下去。贾琏来看时,便哭着和贾琏说:“我这病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预知男女。倘老天可怜,生下来还可;若不然,我的命都不能保,何况孩子!”
贾琏令人抓了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下来了。于是血流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
秋桐见贾琏替二姐请医调治,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哭骂道:“我倒要问问她呢!到底是哪里来的孩子?纵有孩子,也不知张姓王姓的!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她寻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无甚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想毕,挣扎起来,打开箱子,找出一块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狠命咬牙吞入口中,几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快穿戴整齐,上炕躺下。当下人不知,鬼不觉。到次日早晨,丫头媳妇们见她不叫人,乐得轻闲。平儿看不过,说丫头们:“你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她虽好性儿,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别太过分了,墙倒众人推。”丫头听了,急忙推开房门去看,只见尤二姐穿戴得齐齐整整,已死在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