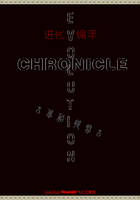一天,凤姐的丫环平儿在李纨处玩耍了很久才离开,她刚出园门,只见凤姐那边打发人来找她,说:“奶奶有事等你。”平儿说:“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我被大奶奶拉扯住说话儿,我又没逃,这么接二连三的叫人来找!”那丫头说:“这又不是我的主意,姑娘有怨言自己和奶奶说去!”
平儿不高兴地说:“好了,你们越发上脸了!”说着走来,只见凤姐不在屋里,忽见上回来寻求帮助的刘姥姥和板儿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张材老婆、周瑞老婆陪着。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上倒口袋里的枣儿、倭瓜和野菜。众人见她进来,都忙站起来。刘姥姥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儿的身份,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说:“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稼忙,好容易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蔬菜也丰盛,这里头一起摘下来的,还没敢卖呢,留着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算是我们的心意。”
平儿忙说:“多谢费心。”又让坐,自己坐了,又让张婶子、周大婶坐了。命小丫头:“倒茶去。”周瑞老婆和张材老婆笑着说:“姑娘脸上有些红色,眼睛圈都红了。”平儿说:“可不是!我原本不喝,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提着死灌,不得已喝了两盅,脸就红了。”张材老婆笑着说:“我倒把着要喝呢,又没人让我,明日再有人请姑娘,一定带了我去。”说着,众人都笑了。
周瑞老婆说:“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足能称两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要是上上下下,都吃只怕还不够!”平儿说:“哪里够,只是有名的吃两个子。那些散众的,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刘姥姥说:“这种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
平儿问:“你见过奶奶了?”刘姥姥说:“见过了,叫我们等着呢。”说着,又往窗外看天色,说:“天已经晚了,我们也得回去了,别出不了城,那就麻烦了!”周瑞老婆说:“等着我替你瞧瞧去。”说着,就去了,半天才回来,笑着说:“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平儿问:“怎么样?”周瑞老婆笑着说:“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地告诉二奶奶:‘刘姥姥要回家去,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说:‘大老远的,难为她扛了些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缘了吗?这也罢了,偏老太太又听见了,问:‘刘姥姥是谁?’二奶奶就给她说清楚了。老太太说:‘我正想找个有经验的老人家说话儿!请了来我见见。’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缘了?”说着,催刘姥姥下来快去。刘姥姥说:“我这模样儿,怎么见得呢,好嫂子,你就说我走了吧!”平儿忙说:“你快去吧,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比不得诳三诈四的那些人。想是你太有人情味,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和周瑞老婆引了刘姥姥往贾母这边来。
二门口值班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都站起来,有两个又跑上来,向着平儿叫:“姑娘。”平儿问:“又怎么了?”小厮笑着说:“这会子也晚了,我妈病着,等我去请大夫,姑娘我请半日假行吗?”平儿说:“你们倒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转告奶奶,只和我胡缠。前日柱儿去了,二爷偏叫他,叫不着,我答应了,还说我做了人情,今日你又来告假!”周瑞老婆说:“当真的他妈病了,姑娘也替他应着,放了他吧。”平儿说:“明日一早来。——我还要让你办事呢。别再睡到日头晒着屁股再来!你回去,带个信儿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问他那剩下的利钱,明日如果还不交来,奶奶不要了,就索性送给他使吧。”那小厮欢天喜地,答应着去了。
平儿等来到贾母房中,恰好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说话,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珠围翠绕、花枝招展的,并不知都是什么人。只见一张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边两个丫鬟,在那里捶腿。凤姐站在底下正说笑。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赔着笑,拜了几拜,口里说:“请老寿星安。”贾母也忙欠身问好,又命周瑞老婆搬过椅子来让坐。那板儿仍是那样,不知问候。贾母说:“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刘姥姥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贾母向众人说:“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么年纪,还不知能不能动得呢!”刘姥姥说:“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稼活也没人做了。”贾母问:“眼睛牙齿还好?”刘姥姥说:“还都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贾母说:“我老了,很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就不见他们。不过嚼得动的吃两口,困了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们玩笑一回就完了。”刘姥姥笑着说:“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都还不能。”贾母说:“什么‘福’,不过是个老废物咧!”说的大家都笑了。
贾母又笑着说:“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她收拾去了。我正想有个地里现摘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刘姥姥笑着说:“这是野菜儿,不过吃个新鲜。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贾母又说:“今日既然已认了亲,别忙着走,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走。我们也有个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回家,也算亲戚来往一趟。”凤姐见贾母喜欢,也忙挽留:“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场院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给我们老太太听听。”贾母笑着说:“凤丫头别拿她取笑儿,她是乡下人,老实,那里称得住你打趣呢?”说着,又命抓果子给板儿吃。板儿见人多了,又不敢吃。贾母又命拿些给他,叫小幺儿们带他外头玩去。刘姥姥喝着茶,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贾母听,贾母觉得很有趣味。正说着,凤姐儿便命人来请刘姥姥吃晚饭,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拣了几样,命人送过去给刘姥姥吃。
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鸳鸯忙命老婆子带了刘姥姥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两件家常的衣服,给刘姥姥换上。那刘姥姥哪里享受过这种待遇,忙换了衣裳出来,坐在贾母榻前,又找些话说。宝玉姊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觉得比那些老先生说的书还好听。
那刘姥姥虽是个乡下人,却生来也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一方面贾母高兴,另外这些哥儿姐儿们多爱听,便没了话也编出些话来讲。就说:“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哪里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没见过呢?就像去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场雪,地下压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没出屋门,只听外头柴草响,我想一定是有人偷柴来了,我爬着窗户眼儿一瞧,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贾母说:“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见现成的柴,抽些烧火,也是有的。”刘姥姥笑着说:“也并不是客人,所以说来奇怪,老寿星猜猜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极标致的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头,穿着土红袄儿,白绫子裙儿。”
刚说到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说:“没大事,别吓着老太太!”贾母等听了,忙问:“怎么回事?”丫头们回说:“南院子马棚里失火了,没关系,已经救下去了。”贾母最胆小的,听了这话,忙起身扶了人出来到廊上来瞧时,只见东南角上火光犹亮。贾母吓得口内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王夫人等也忙都过来请安,回报说:“已经救下去了。老太太请进去吧。”贾母直到看着火光熄了,方领众人进来。
宝玉只是一个劲地问刘姥姥:“那女孩儿大雪地里为什么抽柴草?假如冻出病来呢?”贾母说:“大概是才说抽柴火,惹出事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说别的吧。”宝玉听了,心内虽不高兴,也只得罢了。刘姥姥便又想了想,说:“我们庄子上东边也有个老奶奶,今年九十多岁了,她天天吃斋念佛,谁知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原本你该绝后的,你这样虔诚,如今奏了玉皇,给你个孙子。’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这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时,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后来,果然又养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岁,长的粉团似的,聪明伶俐得很。这些神佛是不是很灵验!”这一番话,正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王夫人都听呆了。
宝玉心中只惦记抽柴的故事,正闷闷的心中筹划。探春问他:“昨日扰了史大妹妹,咱们回去商议一下,还个席,也请老太太赏菊如何?”宝玉笑着说:“老太太说,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再请不迟。”探春说:“越往后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兴。”宝玉说:“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头场雪不好吗?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说着,宝钗等都笑了。宝玉瞅了她一眼,也不答话。
等人都散了,背地里宝玉到底拉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是谁?”刘姥姥只得编个故事告诉他:“那原是我们庄子北沿儿地埂子上,有个小祠堂儿,供的不是神佛,原先有个什么老爷。”说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管什么名姓,也不必想了,只说往下就是了。”刘姥姥说:“这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什么苦玉,小姐知书识字的,老爷太太爱得像珍珠儿。可惜,这小姐长到十七岁,一病就死了。”宝玉听了,连声叹息,又问:“后来怎么样?”刘姥姥说:“因为老爷太太疼得心肝儿似的,盖了那祠堂,塑了个像儿,派了人烧香儿供奉。如今年深日久了,人也没了,庙也破了,那泥胎儿可就成了精咧。”
宝玉忙说:“到底这个人是死了。”刘姥姥说:“阿弥陀佛!是这么着吗?不是哥儿说,我们还当她成了精了呢!她时常变了人出来闲逛,我才说抽柴火的,就是她。我们村庄上的人商议着用榔头砸她呢。”宝玉忙说:“快别这样,要平了庙,罪过不小!”刘姥姥说:“幸亏了哥儿告诉我,明日回去,拦住他们就是了。”宝玉说:“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多好善乐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日做一个样子出来,然后再找些布匹,你就做个香头,攒了钱,把这庙修好,再装涂了泥身,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好不好?”刘姥姥说:“若这样,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钱使了。”
宝玉又问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姥姥便顺口胡诌了出来,宝玉信以为真,回到房中,盘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茗烟几百钱,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让茗烟先去看个明白,回来再作主意。
那茗烟去后,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得热锅上蚂蚁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见茗烟回来了。宝玉忙问:“可找着了么?”茗烟笑着说:“爷听得不明白,叫我找得好辛苦!那地名坐落,不像爷听的一样,所以找了一天,找到东北角田埂子上,才有了一个破庙。”宝玉听说,喜得眉开眼笑,忙说:“刘姥姥年纪大了,一时记错了,也有可能,说说你见的。”茗烟说:“那庙门虽是朝南,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气,一见这个,我说:‘可好了!’连忙进去,一看泥胎,吓得我又跑了出来,活像真的似的!”宝玉笑着说:“她能变化,自然有些生气。”茗烟拍手说:“哪里是什么女孩儿?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
宝玉听了,啐了一口骂道:“真是个没用的东西,这点事也干不来!”茗烟说:“二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或者听了谁的混话,信真了,把这没头没脑的事情,派我去查实,怎么说我没用呢?”宝玉见她急了,忙抚慰她说:“你别急,改日闲了,你再找去,要是她哄我们呢,自然算了,如果真有,你岂不是积了阴德呢?我必重重地赏你。”说着,只见二厅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屋里的姑娘们站在二门口找二爷呢。”刘姥姥这胡编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