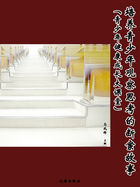如果说,贝克的这种表达方式肯定会令熟悉《共产党宣言》的中国学者觉得亲切(不止是由于句式的刻意模仿,而且还由于理念的某些近似,因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主张的是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那么,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和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的表达方式,则肯定会令具有“反帝情结”的中国学者产生误解——两人论述“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书,正标题竟然是“帝国”。然而,他们表达的正是与前述全球化思想家殊途同归的结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一种新的全球的秩序、逻辑和结构正在形成;“帝国”所指的是这样一种主体,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和调节全球范围内各个领域的交流,并对一些主权大国的主宰行为进行控制;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相反,它没有建立权力的领土中心,也不依赖于固定的疆界或屏障,用哈特本人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去中心的(decentered)和去领土化的(deterritorializing)机器,这样的机器在其开放的、不断扩张的边界内将整个全球版图整合起来。帝国通过对指挥网络系统的调整来对混合的身份、灵活的等级制度和多元的交流实施管理。”一句话,这正是前述哈贝马斯所谓的“制度和程序”,正是我们所谓航班上的“操作规程”。
我不敢说这一“帝国”概念一定受到了但丁《论世界帝国》的影响(因为该书的拉丁原名DeMonarchia意为“一个人统治”,也可转义为“大一统”),但我却在其中看到了但丁关于世界统一(当然除了“由罗马人统治”这一点),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甚至康有为和儒家思想家关于世界大同的理念,因为按哈特的说法,“具有明显的国家色彩的世界地图在帝国的全球彩虹中被融合在一起了。”
五、怎样选“机长”?
既然单独的一个机长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这趟国际航班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担任机长的人,而是一套有效的“操作规程”,那么,所谓“怎样选机长”的问题,实际上就转化成了“怎样制定出这套规程”的问题。
简而言之,这套规程的制定,只能通过合作协商。因为,只有通过合作协商制定出来的规程,才能反映出所有乘务员及其代表的所有乘客的看法和见识,才能明智而又合理,并因而得到所有乘务员的严格执行,既能自觉自愿又能承担责任。
正因为如此,当今大部分各持独立见解的全球化思想家,又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全球民主”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作者都论证过这一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我认为也几乎是必然的观点是:尽管现实世界中民主制度在各国国内的不健全、在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全球民主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尽管没有普遍的国内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国际民主,但是,考虑到现实世界各群体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力量极不平衡的状况,考虑到这些不平衡又有着种族、历史、社会、地缘、人口等极其复杂的原因,再考虑到全球化时代市场、资本、技术的巨大变化以及国家、地区、超国家组织、跨国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的变化与发展,全球民主确实会突破以往历史中的国内民主的各种模式,确实需要某些突破历史框架的新思维,确实需要比以往时代更周全和更宏大的眼光。
也许,人类在这方面通过不断“试验、纠错、再试验、再纠错,逐步完善”的过程,即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挣扎奋斗、摸索前进的过程,乃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贝克前引文章的标题提出了同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同样问题,而其文章的结尾,也提出了“世界公民运动”或“世界主义政党”作为一个可行的建议,但他的“省思”,主要还是从社会行动角度进行的。看起来,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下述“省思”,则主要是从社会意识的角度进行的。哈贝马斯写道:“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因此关键问题在于,能否在共生于广阔地域的各政治实体的公民社会和政治舆论中,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的意识。
只有借助于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的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改变,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只要国民出于可以理解的自我利益的原因尚未赞同这种意识转变,就不能指望执政的首脑人物实现这种由国际关系转向跨国性世界内部政策的观念转变。”因为行动毕竟是由相关的意识所指引,所以,哈贝马斯的“省思”,不但可视为对贝克“省思”的一种补充,而且可视为对讨论的一种深化,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哈贝马斯还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哲学省思”的层次去探索解决之道时,这种深化就更明显了。
在提出“为了按世界公民的意愿策划共同利益以及为了建立全球福利体制,人们需要一些制度和程序”之后,哈氏接着指出,“放弃了理论批判的社会理论”是无法胜任这一任务的。他写道:“在清理西方理性主义基础的理性批判方面,海德格尔是位关键人物,这种理性批判的目的仅仅在于重新玄化。在康德乃至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理性的辩证自我批判试图弄清西方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而海德格尔则坚持一种关联性的理性批判,指出自我掩蔽的主体理性那种虚妄的自负。海德格尔式的理性批判似乎想从内部揭示毫无根基的、抽象的自我理解的局部起源背景,打破理性的偶像,从而重建新的泰然境界。现代性的信仰者应当重新学会在虔诚的期待中向未卜的存在命运屈服。”
这些“哲学省思”已经接近了我所说的“宗教哲学省思”的边缘。而宗教哲学的省思,似乎也可以视为对其他角度省思的一种补充。
简言之,这种省思就是:在“选出机长”即制定“明智合理的规程”所需的“合作协商”之中,是否需要超出狭义的理性(如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和蒂里希所说的“技术理性”)?进一步说,就“机长”操作的实际内容即实行和修正规程的全部过程而言,是否需要超越作为手段的规程,永远不忘飞行的目标?是否需要期望一种髙于机长的指引,或有一种哈贝马斯接着上一句话所说的“末日式的关怀”?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至少,这里所需要的,不是只对自己群体(一个乘务员所代表的一群旅客)的利益、情感、见解的算计和狭隘的考虑,而是对航班整体的利益、处境、目标的悲悯和宏大的思考,而后者常常要求放弃前者,要求作出牺牲。
一句话,这里需要的是自我限制或自我降格或自我放弃,是某种宗教性的态度。
这种态度同理性的关联,只在于它是所谓“价值理性”或“存在理性”,是真正的“明智”,或与小聪明相对立的“大智慧”。
从全球角度来看,民族国家的政治(包括为了增强竞争力而采纳专制的或民主的制度)乃是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而全球民主需要的乃是“存在理性”。因为,把“合作协商”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其基础必须是对人类存在的关切、对宇宙和谐的信念。所谓“存在理性”,按蒂里希的阐释,即古典意义上的理性或“逻各斯”,是一种被称为“道”或上帝的表示宇宙本原的宗教概念。而不论是但丁的“世界帝国”,还是康德的“永久和平”,以至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都是带有一种宗教情怀的崇高理念,其实现所需的不只是算计性、理智性的谋划,而更是悲悯性、宗教性的献身。这种精神可以为贝克和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公民和意识转变,提供强大的动力。
六、飞向何方?
这涉及前面所谓“宗教哲学省思”的“进一步”问题:在“机长的操作”,即实行和修正飞行规程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飞行的目标。因为飞行规程永远只是为达到目标而服务的手段,手段必须适应于目的,而非相反。
按蒂里希的分析,“一方面,逻各斯意义上的理性决定着目的,仅仅在次一级的意义上决定着手段;另一方面,技术意义上的理性决定的却是手段,而从别的地方接受目的。只要技术理性是存在理性的伴侣,而且推理是被用来完成理性的要求,那么这种情境之中就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推理”脱离理性或技术理性脱离存在理性的威胁“已经变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现实,结果,提供目的的乃是种种非理性的势力,或者是种种实定的传统,或者是为求强意愿服务的随意选择。批判性的理性已不再对种种规范和目的发挥其制约功能。技术理性如果脱离了存在理性,那么它无论在逻辑方面和方法论方面如何精致,都会使人类非人化。”可以说,这是对全部现代性弊病病根进行的先知式的“宗教哲学省思”。
人类在现代时期常常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常常使手段脱离了目的,常常使技术理性脱离了存在理性,常常让非理性的力量或实定传统或求强意愿来指引自身的行动,因此而造成了无数的灾难,背离了人的根本目的,即符合自身本性的存在。这是从过去世纪数不清的战争到现今面临的巨大的生态危机,由无数方面的无数事件所例证了的。
“全球化-地域化”潮流使这种情况走到了自己的极限之处。在以往时代因为技术水准而受限的地方,即在物质的开发、消耗、生产、消费和抛弃方面,现今的人类已经不受技术限制,反而借技术的无限制发展而接近了资源的极限。所以,我们需要批判性的理性来发挥制约功能,需要存在性的理性来加以引导,我们需要一种精神性的自我限制。而这些都同宗教有关。
即使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也涉及某种宗教哲学的思考,两者的连接点乃是“信任”。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谈话时所提到的,在商务和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信任”,本来具有宗教的来源和含义。当吉登斯提到“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你必须具有一种笼统的信任概念”时,那绝不仅仅如他所说,是一种从“情感经历”中获得的东西,而是一种涉及了实存的(existential)和存在的(ontological)问题。众所周知,吉登斯详细论述了现代的“风险社会”如何因全球化而成为“风险地球”,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我们的确需要开创与传统的民族国家所不同的政府形式”,因为从金融到环保的各个领域的难题,都需要国际的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而这正如前面所说,就需要一种“天下一家”的宗教情怀。
总而言之,“全球化-区域化”的进程需要补充、矫正和引导。全球化的经济重心或对物质层面的侧重,需要政治安排或制度层面的补充,而后者又需要哲学-宗教的省思或精神层面的补充。一方面,某些物质利益和制度缺陷的结合,某种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的结合,导致了人们所见的垄断、集中或一体化现象,忽略了差异或区域或个体,因此需要一种矫正;另一方面,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带来的是一种相反的倾向,即多元并存,或者区域化甚至个体化,这已经成了全球化内部的悖论、张力或“矫枉过正”。这就引出了所谓“补充者”和“矫正者”自身的内在张力问题。
精神文化或所有形式的精神文明,必然是多种多样或多元的,必然是倾向于(不限于空间意义的)区域化和个体化的,因此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反全球化的可能性。但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之所以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就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源泉,即人类追求超越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的共同根基是单一的和普遍的——“道通为一”、“大道为公”。换言之,精神文化自身是某种“一与多”的统一。
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宗教同样是某种一与多的统一。一方面,宗教系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这是它不同于其他精神文化的本质核心,这是宗教的共性所在,是其“一”;另一方面,宗教又是以这种信仰为核心并与之相适应的人间的象征体系,而且包含纷繁多样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这是不同宗教的个性所在,是其“多”。宗教之“多”及随之而来的狭隘和对抗,其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执着于纷繁的象征,将其等同于象征的对象,从而将其绝对化神圣化;同时忘记了其精神乃在于“一”,乃在于被象征者,乃在于绝对终极的慈悲、仁爱和最广大的包容性。
因此,只有矫正者不忘矫正自身,补充者不忘补充自身,才能发挥某种矫正、补充和引导的作用。只有宗教处理好自身的“一多”关系,从形式之“多”返归精神之“一”,达到多元和谐的境界,才能对世界处理“一多”关系,达到多元和谐提供帮助,提供前面所说的精神支持。
在多元和谐的精神指引下,不忘人生的目标是与天下万物的共生共荣,是人性的完善,承认人类的历程和命运在于既与自然不可分离,又可以超越自然而自由创造,那么,这一趟不但有了机长而且仰望更高指引的国际航班,其飞行的前方目的,就将是回降于大地,而又再度起降,永不止息……但是这一切,还有待于全体乘客的努力,这既包括有所作为,也包括有所不为。
2004年6月12日于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