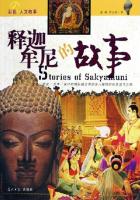纪事
这一年写的文章似乎较多。5月在首尔(当时称汉城)出席“亚洲哲学与宗教学会”时,对宗教对话的首倡者之一斯威德勒(L.Swidler)留下了很深印象。8月赴香港道风山做访问学者,住了三个月,感受良多,“有心无题”五则和“蜻蜓点水”只记叙了其中点滴而已。
有心无题(五则)
(一)
万万没有想到,在香港,在这座我只认识一两个人因而曾以为可以“隐居”两三个月的城市中,竟然比在朋友众多的大陆上还要忙碌(催稿信可以电传追踪!)。
“大隐隐于市”,看来我是不如“小隐”,不如不隐!
万万没有想到,香港,这座我曾以为是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令我想起的竟是我的家乡——贵州的连绵群山!
站在沙田附近高高的山上,看着脚下密密麻麻高低错落色彩明丽的高楼;走在道风山林莽丛生的小径上,听着由海湾填平造成的峡谷中火车和汽车持续不断的轰鸣,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降临我心——喧嚣与安宁、躁动与静止、时间与永恒,竟能这样相互依偎、和谐共处!永不止息的海浪,拍打着永远沉默的山崖,这样的景象,我不是见过许多吗?亘古以来,不就一直如此吗?
(二)
今天是我的生日,到港两月来我第一次放松自己,专程去爬山。快到山顶时,我想起听说过这山里有野猪,还有一个外国姑娘被野狗咬伤过,所以不敢再爬了。
我望着蜷伏在山坳中的小屋,想起二十七年前,自己在贵州黄平的山里当小学教员,那时我才十七岁。住在县城里的舅舅来看望我,他领我出门(出门就是山)去拾柴,同时对我说:“要记住:出门勤弯腰,进门不愁烧!”这是老百姓的生活经验——为了要有熟食,必须如此。在现在,在香港,这话还有用吗?我心里问。
当然有用!因为我想起《圣经》里有一句话:“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又想起古代寺庙里有一条规矩: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只鲜红的蜻蜓飞来,停在我眼皮底下的青草叶上。我又想起二十四年前,自己在贵州印江的山里当小学教员。当我教学生学“马”这个字时,我发现又画又讲还嫌不清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马——这种喜欢昂首驰骋的动物,无法进入这个“地无三尺平”、“路无一尺宽”的山区!就在那个闭塞的山区,在那个闭塞的时代,我整学期给学生讲的故事(因为我是唯一的老师,所以可以自订“课程表”——每天都有故事课),竟是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那些只吃过红薯没见过面包,更没见过木偶没看过马戏,不知道有鲸鱼不知道有大海不知道有意大利的终年赤脚的山乡儿童,在听这个“海外奇谈”时那种眼神之热切、那些欢笑之痛快、与“匹诺曹”的那种同悲共喜之心,对“蓝仙女”的那份景仰钦慕之情,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我突然想到那些大谈夷夏之别中体西用的雄辩高论,不觉哑然失笑!
(三)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对挪威夫妇,典型的金发碧眼、高鼻梁、白皮肤;但他们那七岁的女儿不但头发黑,而且皮肤黑,不但鼻梁塌,而且因兔唇造成牙唇粘连,在18岁之前必须常常去找牙医动手术。这小孩与其父母反差太大,以致我心中断定她只是养女,却不敢开口问其原委。有一天,我们在食堂里同桌,这小孩的同学、一位皮肤黝黑但眼睛很大的尼泊尔小姑娘也在座,我忍不住夸了那尼泊尔姑娘一句,不料,这小孩的养母、总是那么和善的金发夫人马上正色对我道:“你不该这样做!”她接着解释说:人们常常当着一个孩子夸奖另一个孩子漂亮(聪明)等等,但是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人人都有“漂亮”之处或独特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有负面作用,因为未被夸奖的孩子可能因此而产生自卑、委屈、嫉妒甚至怨恨等阴暗心理。对这位普通的挪威妇女,我不得不心悦诚服!
我也曾对这孩子表示亲切,她却不大理我。我观察她很活泼外向,便猜想她不理我,是因为她使用的语言太多(挪威语、英语、普通话、广东话),对我讲的普通话不熟悉。后来她的养母谈起她的身世,我才知道原委。她四岁之前一直在台湾的一所孤儿院里,也许因为她的特点和反抗精神,常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她的养母当时常为领养者们当翻译,正是由于发现孤儿院老师总说这孩子不好,以致一直无人领养她,又出于基督徒的信仰精神,所以才收养她的),有时甚至挨打挨骂。
所以直到现在,这孩子见到白种人或西方人,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开怀大笑,但见到黄种人或中国人,尤其是说普通话的中国人(她呆过的那所孤儿院里流行普通话),却总是心存戒惧!她的养父母着意要消除孩子心中的这种阴影,而且收养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中国人之中,但收效不大。
我想,这小生命心中的扭曲,恐怕不仅仅是那些孤儿院老师的歧视造成的,也许她后来生活其中的中国人也有责任,也许我自己也有责任——她不理我,是因为听不懂我说的话,还是发现我的“亲切”并非那么真切?
在这孩子眼里,中西确实有别。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人会收养这样一个孩子吗?
(四)
我怕麻烦别人,所以在早餐桌和中餐桌上,都未向同桌人(也都是邻居)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老外爱向人贺生日。我想,独在异乡为异客,一人悄悄过算了;何况出身布衣,一向也不重视什么生日之类的。
但在晚餐桌上,虽只有一对夫妇在旁,我却忍不住与他们分享我的喜悦了——因为我收到了妻子和女儿极好的生日礼物:一封报喜信(女儿报告她通过了钢琴八级考试),两幅漫画(女儿活画出了她未被繁重功课窒息的童心),四张照片(使我能看见暂时脱离的天伦之乐)!
然后我心满意足,回屋继续闭门造车——安心读书写作。
将近晚上十点钟,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只见烛光闪烁之中,一块蛋糕和一瓶鲜花上边有七张笑脸——两对挪威夫妇、一对尼泊尔夫妇、一位中国画家(都是邻居),站在门口,齐声高唱:“祝你生日快乐!”我因不知所措,竟然双手合十,眼眶也湿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吹生日蜡烛(正好蛋糕上只有一支蜡烛,虽然我不止一岁)!中国画家说要先许愿。我想起前几天中秋时写家信引用的诗句“但愿人长久(Maypeoplehavelonglife)”,不禁脱口祝道:“但愿人长爱(Maypeoplehavelonglove)”!
送客出门时,几位老外见墙上有“仁爱”两个大字,对那弯弯曲曲的篆书笔画颇感好奇。中国画家遂释“爱”字曰:中为人心,上有天帝覆之,下有人手托之,是为爱也。我则释“仁”字曰:仁乃二人合成,有你有我,方成其仁,有我无你,岂有仁乎?老外直呼“妙哉”(wonderful)!
也许,我们两人的解释,只是信口戏言。
但是,我们大家的感叹,确乎出于真心。
(五)
我在食堂里曾与一个在英国念书的中国学生聊天。她告诉我,一些暂不想回国的中国学生心中并没有忘记祖国,也不可能忘记,但“他们有一种观望心理,他们在等待”。我问她说:“望什么?”她说,当然是望祖国更好。“等谁呢?”她说不出来了。她当然知道,祖国的“更好”,是要人去干出来的;“等别人”去干,她说不出口,因为道理很简单:人人都等别人,那就无人可等。假如他们信上帝,她就会说他们在等上帝(即便如此,他们也知道英国有句谚语,叫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假如他们不信上帝,那么他们等的,若非戈多,便是自己了!
于是话题变成了“等自己”是什么意思。这看来是不行动,至少是暂不行动,也就是“无为”的意思。它与国内有人倡言的“退出历史的缺席权”异曲同工。主张等待与无为者,国内也大有人在啊!
于是我想起了汤因比所谓“退隐”与“复出”。历史上不少大人物似乎都曾“退隐”,但却都为了“复出”。有些是韬晦之计,有些是养精蓄锐,有些是时运不济,不久却东山再起,总之,是为了有为的无为,却不是真正的无为。
如果不是韬晦之计,不是养精蓄锐,不是被迫下台,而是真心诚意的、“出家厌世”的、“躲进小楼”的真正的“退出”呢?那难道不是真正的“无为”吗?我姑且不论人作为历时的和社会的动物能否做到“退出历史”,或者说“退出”了历史的人是否还能称为“人”,我只想问问:“退出”是不是一种行为呢?“出家”是不是一种行为呢?退出不就是让别人进来吗?出家不就是让别人进家吗?缺席不就是让审判更顺利吗?沉默不就是让别人多说些吗?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退隐?世界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无为?出生就是“复出”,生命就是行为,生存就是“在世”。
难怪莎翁要说:“我们都是演员,世界就是舞台。”这演员,就是有为者(Actors)。这舞台,不但没有后台,而且与观众席连成一片,无边无际。
难怪歌德要说:“太初有为。”这个“为”,就是行动(Action)。这句话,是歌德改写的《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而《创世记》第一句话则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其实,创造是“为”,道又何尝不是?即按老子之说,道既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难道不是大为吗?
所以,“无为”是假,要在“何为”。
我想起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又想起了谭嗣同(字复生)死后康有为的一幅挽联:“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原载《东方》1994年第6期
“生死苦乐”三问
前些日子,北京电视台邀我参加过一次“生命绿洲”节目的座谈,话题是“安乐死”。才过一周,该台“BTV夜话”专题组又来采访,话题是“安灵的启示”(“安灵”是一家殡仪公司的名字,它专为委托人举行向海里抛撒骨灰的仪式,据说生意不大兴隆)。然而,“生死苦乐”之类永恒的话题谈了一大堆,经电视台一剪辑,播出的就只有一小撮。我不禁觉得,当我的形体在荧屏上活现之时,我的灵魂却似乎萎缩了。于是我还得来找《东方》杂志。因为在书本里,形体虽然无踪无影,灵魂却比较舒展鲜明。
“安乐死”?
“安乐死”观念的兴起,是为摆脱或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这问题涉及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宗教等诸多方面,十分复杂。“安乐死”概念也分成很多类,其中最起码的,是“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类似他杀,很难令人赞成——汝非鱼,安知鱼宁取“乐”而舍“生”乎?“自愿安乐死”实为自杀,赞成者甚众——与其痛苦地活,不如无痛或短痛而死,“赖活不如好死”嘛!
确实,“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为“良好的死亡”,即“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