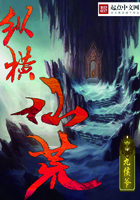文刘万里
六叔是我的父亲,我不叫他爹也不叫父亲,我喊他六叔。
奶奶有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父亲为六,奶奶叫他小六子。奶奶的哥哥,也是是我的舅爷,没有儿女,他就想在奶奶的六个儿子中挑选一个做儿子,为的是将来好养老,农村叫过继。
舅爷住在深山老林里,交通不便,离镇上有六七十里路。舅爷看中了老二,老二在舅爷家呆了几天就偷偷跑了回来,哭着闹着死活不去。奶奶没办法,就想把老三过继过去,结果老三呆了几天也跑了回来。奶奶只好含着泪把5岁的父亲过继过去,并切把姓也改了,随舅爷姓黄,父亲是个听话的孩子,就老老实实在舅爷家呆了下来。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天的日子似乎都在酒中侵泡过似的,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挥不去的酒香,人们往往还没进门就能闻到一股酒香,那准时我父亲来了。其实,父亲小时候根本没有喝酒的嗜好,都是在舅爷潜移默化的结果。每年腊月,舅爷就用包谷、高粱等自己烤酒,舅爷好客,亲朋好友经常聚在舅爷的院子里大碗喝酒,大声说笑。住在舅爷坎上的邻居江老头就故意逗父亲,“来,喝一口。”六叔就朵闪。舅爷哈哈大笑说,“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学会喝酒。”父亲端起碗大喝一口,喝得急,六叔咳嗽起来,舅爷他们都笑了起来。也就是从那开始,父亲没天尝一点、喝一点,慢慢父亲酒量大增,有时能喝一斤白酒了。
后来,父亲娶了母亲,一年后母亲生了我。我随舅爷姓黄,我也改口父亲为六叔。
在我小时的记忆中,一到冬天,大雪封山,闲不住的父亲就抗着枪,腰上挂着林冲那样的一个酒葫芦,牵着猎狗去山上打猎。每次父亲去打猎,母亲就让我随着父亲,并暗暗叮嘱我,把父亲看紧,别叫山上那只狐狸精迷住了。
母亲说的那只狐狸精我叫她江姨,我不明白母亲为啥叫他狐狸精,每次父母吵架,母亲嘴里总是少不了狐狸精这三个字。
江姨长得很漂亮,在我所见的女人当中江姨是最漂亮的。
父亲每次上山都要到江姨家闲坐一会儿,江姨对我很好,每次都拿出好吃的东西让我吃。有时,父亲把打的野兔、狐狸什么的就分一点给江姨,父亲总是叮嘱我,回去不要跟你妈说。
一次,我说露了嘴。母亲气得跟父亲打了起来,嘴里不停的喊狐狸精。母亲一气回了娘家,最后还是父亲去认错,才把母亲接了回来,也就是从那开始,我才知道了一些关于父亲和江姨之间的故事。
江姨是我们的邻居,所谓的邻居也就是最近的一家,我们住在半山腰,江姨比我们还高,山里的人家星罗棋布,东一家,西一家分布在山沟里。江姨从小跟父亲一快长大,也算亲梅竹马。
当时情犊初开的父亲喜欢上了江姨,这份爱父亲深藏在心底,晚上父亲经常梦见江姨,梦见江姨成了他的新娘子。
一天晚上,父亲把江姨约了出来,为了壮胆,喝了不少酒,借着酒胆父亲抓住江姨的手说,“我……我喜欢你……”江姨抽出她的手,脸一下红了,“你找死啊!”父亲迟疑了一会儿说,“我真的喜欢你啊!”父亲抱住江姨就亲,这时江姨的父亲江老头起来上茅房时看见了他们,他气得操起扁担大骂起来,“妈的屁,打死你这小兔崽子。”父亲吓得转身就跑,江老头就追,要不是江姨拦住了她父亲,江老头非要打死我父亲不可。
父亲怕江老头找上门来,吓得好几天都不敢回家。
江老头反对江姨跟我父亲好,是因为他嫌我父亲家里穷,再说父亲又是外地人,外地人容易被人欺负。其实江老头心里有一本账,他早就给江姨物色好了一个对象,是村长的儿子。这件事发生后,江老头把他的计划提前了。经过媒婆的牵桥达线,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很快江姨流着泪嫁了过去。
迎亲的队伍像条长龙,父亲目送着江姨在锣鼓和唢呐的声中消逝在山那头,父亲像个雕塑一样呆呆地站着,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一朵一朵,父亲像个雪人一动不动站在山头。
江姨出嫁后,父亲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只顾喝酒,有时独自站在山顶望着残阳嚎叫,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舅爷看在心里,他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女人,那女人虽然长得丑,但身体结实,庄稼人就需要这样的女人,那女人就是我后来的母亲。
母亲嫁来这天,父亲喝的大醉,父亲醉了四天四夜。在当地有个规矩,三天新娘子要回门,舅爷看着醉得如死猪般的父亲,气得大骂起来,“没出息的东西。”最后还是舅婆陪着母亲回的娘家。
父亲对母亲很冷淡,从不正眼瞧母亲,也不跟母亲说话,只到一年后我的出生,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才慢慢有所改变。
三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何江姨没生下一男半女,不久江姨的丈夫得疾病去世了,江姨一直也没改嫁。
半年后,江姨的公公也去世了,人们开始说江姨命克夫克公公,女人们开始躲避着江姨,怕她身上的霉气沾染到她们身上,同时也叮嘱自己的丈夫遇见江姨要躲开,不要跟江姨说话。
家里没男人,江姨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父亲有时偷偷把家里的粮食,山上打的野物悄悄地放在江姨家门前,然后像个做错的孩子一样转身就跑,生怕被别人看见。
一次,父亲又去给江姨送粮食,父亲放下就走。
江姨突然出现了,眼里含着泪,“站住!”
父亲难堪的站在那里嘿嘿一笑,“自家产的,值不了几个钱。”
江姨大声说,“给我拿回去,我有手,不要你可怜。”
父亲嘿嘿一笑,“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转身就跑。
每年冬天是父亲最快活的日子,坡上的活又少,闲不住的父亲就带我去山上打猎,其实我不想去,每次都是母亲恿涌着我去,母亲叫我私下盯着那狐狸精——江姨。江姨是个不错的女人,我不明白母亲为啥叫她狐狸精。
每次打猎回来路过江姨家时,父亲总是说口渴,去讨杯水喝。每次父亲总是把猎物分一些给江姨,江姨对我们很好,有时我们也在江姨家吃饭。每次父亲见了江姨就很开心,有说不完的话,而父亲面对母亲往往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有一次江姨在擀面,两个奶子像两只兔子在跳跃,父亲悄悄地走了过去抓那两只兔子,江姨吓得大叫一声,扬起擀面仗回头要打,见是父亲才送了一口气,笑着说,“你这个死鬼,小心我把你的狗爪子剁了下来。”父亲嬉皮笑脸的伸出双手还要去摸,“你剁啊,你剁啊。”父亲说第二句“你剁啊”时他看见站在门前的我,父亲一本正金的说,“小兔崽子,你看到了啥?如果你给你妈说,我撕破你的嘴。”我说,“六叔,上次都怪我说你摸了江姨的屁股,结果害得你跟我妈打了一架,这次我啥都不说。”江姨的脸一下红了,狠狠瞪了父亲一眼,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说,“下次到镇上给你买一把手抢。”
我高兴跳了起来,“六叔,你说话一定要算话。”
父亲说,“我啥时骗过你?”
一到腊月,年的味道开始在山谷里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