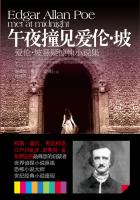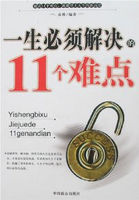88
高马丽这一夜是百感交集。
既羞涩又兴奋,既疼痛又快乐,既亲爱又恨气。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初夜竟是这样毫无准备,又是这样暴风骤雨。她想坚决抵抗,结果是全然承受。直到早晨,她才看到石金河象溶化着的糖人,软软睡去。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高马丽又喜悦又自责;看着熟睡的金河,她是又心疼又怜爱。
只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自己穿了衣服,赶到《又一村》早点摊儿。脸上的喜悦流光溢彩。
小妹一眼一眼偷看去,心里也是扑扑腾腾。她一边盛舀粉汤豆腐脑儿,兼着跑堂,一边忍不住多看几眼金河昨夜来时驾驶的那辆轿车。她作为一个女儿家,金河一夜留宿,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乔二棒正炸油条。抻面、剁份儿、炸煮、出锅。一边也狠狠地看那辆车几眼,他也不傻,见车停了一夜还在,什么想不到?
手头开始摔打、嘴里嘟囔不休:
“这买卖是不能干啦!你们做什么,谁能管得着、拦得住啊?你们也多少隐蔽些、稍微回避点儿!嗬,专门张扬嘛!成心表演嘛!就是往人的眼里插棒槌嘛!——有人还专意给腾床位,生怕人家没地方!跟上啥人学啥人,跟上巫婆学跳神!学吧!跟上往好里学吧!”
指桑骂槐,打鱼捎带捞鳖。
二棒唠叨劲儿这毛病上来,那是必须高马丽来治疗。小妹却不好意思去看高马丽。
抽斗桌子旁,高马丽收款、唱票,一边拣拾油条。早听见二棒数落,早霞映在脸颊上,只当今儿没带耳朵。
他们正要收摊儿时,一辆出租车可可停在金河的车子旁边。
出租上下来的是高马丽的对头星温小寒。服饰华贵、仪态骄矜的温小寒特地再次看看轿车牌号,又到车窗那儿瞅瞅里头。然后冲高马丽走过来。
乔二棒耸耸肩,小妹倾头收拾桌子。高马丽避开脸面,没看见温小寒似的。
温小寒皮鞋“笃笃”来到近前,指名道姓地与高马丽对话:
“高马丽,高小姐,我们又见面啦!没办法,我这是工作,和发荣公司业务上的事,必须马上找他!你,不介意吧?”
高马丽一听,原来昨天石金河是与她们一起喝的酒。
温小寒似乎是在解释着自己的动机:“昨晚他喝多了。一早电话联系不上,估计他是来了你这儿,果然!我看见他的车了。人呢?还没起床?”
高马丽开始是羞涩,此刻加上愤怒,脸子憋得通红。
温小寒猫儿逮着耗子似的,盯了高马丽。
“你手头正忙,要不,你指给我地方,我去喊他!睡在温柔乡里,就不管工作啦?这一笔合同五十万呢。”
高马丽脸子潮红,想了想,还是让小妹找石金河去。小妹见不惯温小寒的劲儿,不愿去。高马丽声色俱厉了。
“去呀!使唤不动你啦?”
这时,累疲了金河还在高马丽的床上酣睡,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穿上裤子,赤膊上前开门,进来的竟然是温小寒!
“你?你怎么来这儿啦?”
温小寒怪模怪样笑笑:“有急事找你,没法子,请这个姑娘带我来的!”
金河才看见小妹在温小寒身后,小脸上不成颜色。他面对小妹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小妹也不看他,愤愤地丢下一句话走了。
“石金河!她找你有事,别在我们房里折腾啊!出来了给我锁上门!男的来了女的来,我们这儿成了什么地方啦!”
金河连忙穿好上衣,温小寒探头瞅瞅房间里的情形,跺了跺鞋底上的土。似乎这样房间就是可以随意折腾似的。
金河完全清醒过来,说,“你在你家也能往屋子里跺土?别以为你那818是什么干净的地方!”这下,把温小寒的优越感打下去一截。
他锁了门,扭头问:
“说吧,什么事儿?巴巴地找到这儿来!”
温小寒这才说,两家公司签了合同,吉根茂一早已经飞回广东了。老板吩咐,关于饲料的事儿,叫她催着些。
金河不冷不热地说:“那你该去催我们侯老板啊。”
温小寒一边道歉,一边解释。“我也是实在没想到昨天会碰到你。想不到你已经升任了总经理助理。”
金河冷笑了:“你的眼里,我就该永远扛麻袋呀?”
温小寒被抢白得倒噎气:“你看你,我那么说了吗?两个公司合作,咱们以后见面联系,肯定少不了。工作上的事,我不能找你?”
金河依然愤愤:“以后当然能找我,可你今天没有急事!你是成心来给我找事!”
温小寒被说的有些忸怩。她确实是成心的,成心来找金河。
昨天夜里被石金河看见自己与吉老板的那种暧昧样儿,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尽管她一再自我解嘲,“我结过婚,并且又离了婚,哼,我还为谁保存贞节呀?”可是,她还是有一种莫名的负疚感、乃至负罪感。在金河的眼里,自己就是那种水性杨花吧?就是堕落的女人吧?可是,她自己又不愿意这样承认。她想与金河见见。见面之后,又能说什么呢?事情摆在那儿,自己已经迈出了那一步,能如何解释呢?然而,她忍不住还是要见见金河。哪怕见面之后,什么都不说。
谁知道金河手机不开。她凭着一种女人的直觉,认定他在高马丽这儿。当她这样认定之后,心里又突然产生出了另一种女人的惟妙心态。想到已经不能属于自己的男人,竟然属于了另一个女人,心里隐隐然升起一种类似醋意的感觉。
她怀着某种心理,几乎是成心要“撞破”什么他人的秘密;当这一切果然发生之后,她才有些后悔了。她希望能够得到金河的原谅,然而,一切都晚了。
金河认定,“你就是专门,就是成心!”金河甚至懒怠发火、动怒,点穿了她的心机之后,兀自在前头悻悻地走。道路泥泞,话茬难听。
温小寒无趣地跟在后面,全然没有了刚刚那种做出来的高雅仪态。
他们俩前后出现在《又一村》餐馆门口。
两人脸子都僵僵的。
温小寒尴尬地道别而去,石金河也不理不睬,没有一句哪怕出于礼貌的送行话。
这些,倒是冷眼旁观的小妹统统看在眼里。
89
金河朝小妹不尴不尬笑着,进了店堂。
小妹倾头墩地,没看见地下有个他似的。墩布甩打挥舞,朝皮鞋、裤脚上招呼。
里间,乔二棒在剁肉,刀板咣咣响。
高马丽在柜台那儿对账,目不斜视。
金河便解释一句:“已经打发走了。这个温小寒。”
高马丽充耳不闻,管自开抽屉、拨算盘。
金河又说:“公司里正忙,我恐怕要迟到了。我、我该上班去了。”
高马丽依然不理不睬。
金河尴尬着,又往前凑凑:“高马丽,我说你妈过一程不是要来嘛,来了就告诉我。”
高马丽起身拿了块抹布,开始檫抹餐桌。还是看都不看金河。
金河凑近跟前,要坐凳子说话,小妹使墩布将凳子推开了去。
金河一肚皮窝火,可又无从发泄;自己长长吁气,尽量平缓了口吻对高马丽说:
“小丽,你也不要这样嘛!温小寒伺候的吉老板,和我们公司做生意,是我的错吗?她突然来找我,我也不知道。她已经走了,你、你这是怎么了你?”
高马丽这才回话出声:“我怎么了?碰上了你的旧情人,心里又不好受了,拿我当醋喝呀?石金河,我高马丽充当你的什么女朋友,我当够了!我别高抬自己了我!”
金河低声道歉:“小丽,我、我,我夜来喝多了;我、我不该来你这儿——”
这恰是女孩子在这种时候最不爱听的话。高马丽说:“喝多了拿人醒酒啊?我成了你的什么了我!”
金河满脸通红:“小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喝醉了,怨我自己;醉死过去,活该!我、我借酒撒疯,我把握不住自己,我办事出格了!我给你赔情道歉!实在不行,你说怎么办吧?我一概承担!”
金河说着说着,声音高了些。其实,声音高不高,另外两个人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听他这么说,小妹停下了手里的活计,里间的刀板也不响了。
女孩子这时要的是温柔爱意、体贴安慰,最反感的是认错、后悔。
刚刚经历一场爱的狂热,怎么就把它全推给酒了?高马丽气恨交加,再也无法自持,突然伏到柜台上哭出声来。
小妹恼火地看金河,乔二棒手持一柄擀仗,挑开了门帘。
金河似乎没看见这两个人似的,上去抚弄着高马丽的肩膀:“小丽,你你,我我,——过两天大娘来了,我来相亲!咱两个的事情,就当着大人的面儿定下来!”高马丽抽抽噎噎的,金河搂紧她摇晃着。他实在不能让一个刚刚为自己献出女儿身的人再这样受委屈。
小妹见状,扭头冲乔二棒说话,“二棒,你去买粮!我去买菜。”
高马丽却挣开了金河,泪眼婆娑的,喝止住要离开的两个伙计:
“你两个都不要走!《又一村》,是咱们三个的饭店!——让该走的,自己走!以后这地方,不该来的,少来!相亲?哼!天底下没有男人了?——我去买菜!”
她这么一起身,把金河给生生干在了当地。
他真不知道自己把高马丽得罪了这样狠。
90
儿子在省城煮下糊糊一锅,;
老子正在老家煮另一锅糊糊。
石门掌石罗锅与媒婆三姑终于说定了弟弟代哥相亲的事。
三姑拍了胸脯,说柳树湾那边她能给瞒住。
而石罗锅深知银河那脾性。明着让他去哄人,那犟种保准不去;或者去了呢,也不会哄人。所以就没给他明说,今番相亲是顶着哥哥的名义。
银河不知内情,兴高采烈跟上三姑去相亲。三姑要走大道坐上一截汽车,然后再钻柳树湾的山沟。石罗锅舍不得一块五的车费,建议他们走山道,说这样抄近路,快。走山道,拢共不过十来里!
秋天山坳里,野枫山橡,红叶如火。银河许久没在野外了,这一走,倒也旅游似的,心情舒畅。再说,到了柳树湾,说不定能打听到小英家,也好设法去见见,好免了自己的思念。就是这个小英,叫他知道“人想人”是个什么味道。
一路上坡,三姑走的气喘吁吁。直叫站下喘喘,要歇脚,“累死你祖娘啦!累得你祖娘迷糊!知道要出人命,哪怕三姑花那一块五!”
银河撅了一根山柴,一把捋去了细枝杂叶。朝三姑伸过去,让她抓住:“三姑,来,抓住这,我拖上你!你是我三姑,要不然,我扛上你就上去啦!”
三姑没奈何地笑了:“小挨刀的!省下力气扛你媳妇儿吧!”
银河朝上拉着三姑,说:“三姑!我是说,我能扛动你三姑;我不是说,我要扛你三姑!你不愿意我扛你三姑,我还能硬要扛你三姑?三姑,你说是呀不是三姑?”
三姑也乐了:“小挨刀的!一气三姑,闹得三姑都快不知道谁是谁的三姑!”
银河并不觉得糊涂:“这还能成了问题?你是我的三姑,三姑你总成不了你三姑的三姑!对吧?三姑!”
三姑看银河逗嘴皮子,心里满意,这小子,头一回相亲,一点不慌。事情有成。毕竟还是在外头见了世面!于是又吩咐道,“银河,你去了她家,也就这样,大大方方的、舒舒展展的,叫人家看见像个在省城里做大事的、有文化的!”
银河一听文化两个字,就头大:“相亲,不考字语吧?要是考字语,我趁早甭去!咱文化低,不认识几个字!”
三姑让他放心,“不考字语,人家看见你满意就行!”
不想银河反问道:“那我要是看见她不满意呐?”
三姑倒没想到这一下。只得慢慢解释:“啥叫相亲哩?就是相看!人家大人先和咱们见面,说说话;看见你还称心、满意,人家闺女再和你见面。那闺女叫个柳莺莺,可是喜人待见一朵花儿!你包准满意!一百个满意!到人家对你也满意了,那不就成啦?”
银河想得又多一步,“她家要是对我不满意哩?”
三姑说:“人家爹妈要是不中意,那你就连人家闺女的面也见不上!”
银河觉得这下吃亏啦,“那她爹妈不是白白看了我啦?”
三姑便是个笑:“二半吊劲儿又上来了!那依你说哩?”
银河一脸认真地说:“依我说,他家那闺女,也得走十来里山道,来咱石门掌,叫我爹我妈,白白地看她一回!”
三姑拿指头数划他:“憨憨!抬死杠、死抬杠!和你爹一副驴性!——听我的吧,咱银河的人才、条件,他爹妈说不出别的来!”
三姑与银河脚步放快了。爬上山梁,柳树湾遥遥在望。
银河突然要打听个人,“你们这柳树湾一带有个叫小英子的吗?”
三姑想想,没这么个人。银河也就没再细说。
说话间听见狗咬了,进村了。
石门掌这儿,他们一走,老两口就担心上了。老妈担心银河笨嘴拙舌的,人家相不中。老爹说找对象是碰哩,过日子是混哩,也许碰对了,人家女方还就待见咱的没嘴葫芦!再说,咱还有硬头的条件儿,能在省城安排工作。好家伙,省城!
石罗锅担心的是,三姑招呼不到,银河心实,这“冒名顶替”说不定就漏了汤!
不过,已经煮成这号夹生饭啦!他们就只好看三姑的本事、看银河的命相了!
罗锅嫂嘴里祷告弥念,不知求告了哪几路神仙佛祖。
90
三姑领着银河进了柳树湾,走进柳七院子里。
三姑自以为两头捣鬼,相亲的两边都蒙在鼓里。却不知这出戏里,几乎都是真真假假,都不明真情实况;只有一个人不动声色地看着,象导演似的,所有的路数全明白。这个人就是柳莺莺。
她在自己屋子里,从窗户眼上看着打扮一崭新的银河跟着三姑进了大门。来相亲的果然是银河!一切本来都在柳莺莺的预料之中,可她还是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三姑含糊其辞向柳七老婆介绍道:“这就是石门掌我娘家那侄儿。”
柳七站在厢房台阶上,迎接了客人。
见银河大大方方、展展堂堂的身影进入厢房,柳莺莺不禁捂嘴笑了。
银河跟了三姑进了屋子。
三姑与七婶,在炕沿两端盘腿坐了。这是山里女人常见的相见方式。
所谓相看,此刻却是女方家长首先接待,老两口来看银河。
地下一只板凳,柳七微笑着朝银河指了。让座。
银河瞅瞅情形,搓了巴掌谢绝。“不。”
这是他今天说出的第一个“不”。
柳七从桌上摸起一盒香烟,拆了口,给银河递到面前。“吃烟吧!”
银河有点局促,说出第二个:“不!”
他靠桌子立了,柳七蹲在墙根。这是山里男人熟惯了的相见方式,其实也不能说完全不合适。
七婶急忙下地,倒了一杯开水,摆在桌上、银河身边:
“这娃,你喝水!”
水杯冒热气,自己喉咙里冒火气,银河第三次说:“不!”
开场闹了个“三不”,场面就有些尴尬。七婶来瞅三姑,三姑去看银河。银河却不看她,不理她的示意,只管眼睛巴眨抠指头。
三姑笑出声来,为柳家解疑:“我这侄儿是过于老实,笨嘴拙舌的。叫别人还当他是拿等架子哩!”
七婶为了打开僵局,咳咳了两声,又问,“听她三姑说,你家是弟兄两个?”
银河翻眼看看,哼了第一声。
七婶又说:“弟兄俩,有个伴儿,好。你们弟兄俩都在省里做事?”
银河哼了第二声。
七婶继续问:“弟兄们都在外头做事,可是不赖!听说一个月都能开千儿八百的工钱?”
银河又哼。——已是三哼!
三姑屁股底下坐了枣刺似的;柳七脸子僵板,谁也不看。
七婶还问:“这娃是话语不多。听说要是你成了家,女人能带到城里、你们那领导还能给安排工作?”
银河竟是四哼!
“三不”接着“四哼”,屋里的气氛就十分沉闷了。
七婶又来瞅三姑,三姑再也坐不稳炕沿,下地到桌子上摸了一根烟,狠狠拐了银河一肘子。银河翻翻眼皮,挪开些地方。
三姑到墙根来与柳七对火抽烟,好为主家省下一根火柴。柳七也翻翻眼皮,几乎全是白眼。
三姑便仗着自己的嘴巧,赶紧圆这场面:“我这个侄儿呀,都成了书呆子啦!没有见过这场面,看看腼腆拘谨成个啥洋儿!在家可是能说;和熟人一说一大套!还能说那省里的洋话,一路上没把我说得笑死。”
三姑唱了一折独角戏,故作镇静地、很夸张地回到炕沿那里,盘腿、吸烟,磕烟灰、吹头发帘儿。等待主家发话拿主张。
屋里静静的。
“三不”连着“四哼”,主家一时不好判断、又不知另开什么话题。
这时,院里有鸡们啄玉米的声音。柳七便向老婆发威:“鸡在院里糟践,你不能撵赶撵赶?”
七婶轰走了鸡,屋里更加安静。柳七看客人,银河抠指头、三姑掸裤脚,硬等着他们发话呢。
柳七看这样子,以为人家肯定是走过程来了,不是真心要相亲。于是便站起身,清清嗓子发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