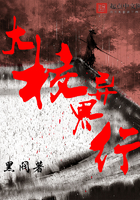屈昂有些意外。为了邬雪琴,他竟然会妥协,去尝试他一向嗤之以鼻的东西,真是了不起的改变呢。
随即,他的唇角泛起一丝看不见的笑,这样也好,说明邬雪琴在他的心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牢固了。
“好,属下这就去办。”他爽利地答。
“等等——记住,找靠得住的,口碑最好的那种。”
屈昂垂眼:“是。”
顾南风抬头:“这些事我是一窍不通,又要让你东西奔走了。”
“属下应该做的。”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回答,也没有假惺惺的自谦,这就是屈昂。顾南风点点头,不再多说,重新把脸转向邬雪琴。
屈昂反身退了出来。
刚才在邬雪琴脸上的匆匆一瞥,让他心惊。
比起前些日子的苍白,邬雪琴的脸色已经逐渐变得红润。这是意识在苏醒、身体在康复的迹象。
而邬雪琴自己,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唯一的可能是……
他一定要阻止,阻止事情这样继续下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屈昂的安排下,萨满驱邪的仪式,在第二天的下午,秘密地在顾南风的卧室里举行。
萨满巫师头戴鹿角帽、熊头帽,有的帽檐上装饰有鹰翎。穿着鲜艳繁复的服装,那衣服层层叠叠,饰以兽骨、兽牙,腰间系有九面铜镜,取驱邪震灾之意,手执抓鼓,既是法器又是伴奏乐器。
此时,原始的鼓点已经响起,祷词、咒语、吟唱和着鼓声,相为唱和,萨满们跳着模拟动物的舞蹈,口中念念有词,充满了神秘色彩。
中间欢蹦乱跳的萨满,脸上戴着猛虎面具,惟独露出一双眼睛。他身穿斑斓的彩条套裙,腰间亦挂着兽骨兽牙和铜镜,猛虎面具,和头上的一支五彩雀翎,是他区别于其他萨满的标志。他显然是这场法事的灵魂人物,从一开始,就被其他萨满簇拥到了中间。
他的身身体所有其他萨满的一样,充满粗犷和原始的气息,而他行起法步来,却显得格外轻灵和飘逸。那双灵活的、指节修长的右手,不时高高举过头顶,随着萨满身上的银铃发出的规律响声,来回晃动,口中一直念念有词。双目忽而紧闭,忽而圆睁,带领着余下的萨满们,绕着邬雪琴的病床,走了一圈又一圈。似乎这样就能完成某种仪式,达到驱邪的目的。
顾南风皱着眉头,独自坐在床边冷眼相看。萨满手中摇晃着的铃铛,诡异的妆容和他们身上奇形怪状的小装饰品,让他觉得很可笑。
虽然本能地比较排斥这样神神鬼鬼的东西,他还是决定安静地看完。
为首的萨满忽然大喝一声,像豹子一样,敏捷地跳到了邬雪琴的床上。
他的举动非常突然,但是顾南风并没有任何反应。这些人是屈昂挑来的,不可能出岔子。而且,即使有什么意外,身边潜伏的影卫也会立刻出现,在任何可能的损害造成以前,将他们全部生擒。
果然,那萨满跳到邬雪琴的床上,似乎也只是仪式的一个步骤而已。
如果说忽然跳到床上比较惊悚和突兀,但是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却可以说极为可笑。
他竟然想在地上一样,围着邬雪琴,来回打转,好在这床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就是一个大。
光是绕圈走不说,他一边念念有词,一边伸出两只手来在空气中乱抓——那手被装饰成了鹰爪的样子,连指甲都是尖锐的。
或许他并不是乱抓,而是在邬雪琴躺着的正上方的空气里,从头抓到脚,然后往旁边的空气里用力一甩。
好像就这么一甩,邬雪琴身上的邪气,鬼魅之类,就能统统被甩走一般。
顾南风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可笑的事情。如果这样都能治病救命的话,那御医馆里的那帮老头子,根本就不用混了。
他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做了这么愚蠢的决定,请了这些莫名其妙的人来。
正在这会儿的功夫,那萨满又是惊天动地地大喝一声,在床上猛跺一脚,身子骤然放低,头也飞快地弯了下来,无限接近邬雪琴的头部,他的眼睛也无限接近邬雪琴的眼睛,脸几乎要贴到她的面颊里去。
顾南风吃了一惊,霍然站起身来,这野蛮人想要干什么?如果他们的愚蠢,令邬雪琴受到任何损伤,那他吃多少后悔药都无济于事了。
正准备暴喝着阻止萨满的顾南风,却在下一秒睁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又震怒转为狂喜。
邬雪琴竟然睁开了眼睛,一切毫无预兆。
而她的视线,正好和萨满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那萨满则直起身子,一声不吭地跳下床来,像是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样。只是,这场法事好像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他跳下床来时,腿竟然因为发软,差点跌倒在地上,幸而旁边的几个萨满眼明手快地将他扶住了。
“嗯?你……”
邬雪琴睁大了眼睛,惊愕地追随着跳下床去的萨满首领。她甚至想要坐起来,可是身体的情况不允许。
“雪儿,别动,你大病初愈……雪儿,你醒了!你终于醒了!”
顾南风前后颠倒的说着话,看着她想要轻举妄动,慌忙跑过来将她一把扶住。
和萨满首领的反应完全不同的,是之前还镇静得像一块冰的他。
他因为连续几天作息极为不规律,面颊已经消瘦得凹陷下去了一大块,眼睛里也充满了血丝,整个人处在一种极端消糜的状态里,令人看了都替他觉得累。
可是此刻,他却像是被打了一针强心剂的人一样——至少在邬雪琴眼里看来是如此。
对于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她完全一无所知。顾南风身上发生的事情,她也全然不晓。只是,看着他憔悴的面容,和此刻眼睛里发出的近乎狂喜的光芒,知道他是真的关心着自己,心中多少有些感动。
邬雪琴避开他炯炯的目光,皱着眉头,再次努力地撑起身子。
喉咙好干,身上完全没有力气,却能明显感觉到,之前被抽走的灵魂,正在缓慢地归位。
一些回忆也在慢慢复苏。
想起了此前的最后的记忆,突如其来的剧痛;想起所有知觉的迅速沦陷,和最后听到的银铃般的声音;想起了不知道多久前,紫安闯进她的意识……或者是,她闯进了紫安的意识……
一切的一切,都如被点燃的火药一样,瞬间爆炸成巨大的蘑菇云,让她觉得脑子像是要裂开一样。
顾南风顾不上说话,见她执意要起身,便小心翼翼地扶住她的腰,一手揽住她的肩膀,慢慢地将她扶了起来,让她倚着床靠着。
然后抽出柔软蓬松的枕头,垫到她的腰下。
邬雪琴无暇注意顾南风的举动,一双眼睛只是牢牢地盯住方才和他对视过的萨满,此刻,他正在指挥其他的萨满收拾散落在屋子里的器具之类,自己则坐在角落里休息。
带着猛虎面具的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而且,好像是注意到了某人目光的追随,自从邬雪琴醒来后,他就再没有和她的目光相撞过。
邬雪琴咬着唇,几次想试探着喊他的名字,却碍于顾南风在场,生生地将这欲望压了下去。
他如果这样伪装,又这么努力地避开她的视线,一定是不想让顾南风识出他的身份的吧。
可是,真的好想和他相认。这么久,这么久没见了,又是在这样的打劫后,猝然相遇。
真的好想念他。
想在他冰冷而温暖的怀里,痛快地大哭一场。
邬雪琴幽幽地想,目光始终不曾离开那萨满身上半步。
顾南风兀自沉浸在巨大的欢喜之中,完全没有留意到她神色的异常,见她目光凝涩,只当她是大病初愈后的木然。
“这些是什么人?穿的好奇怪。”邬雪琴装作无意地一问。
“这是萨满,对亏了他们,你现在才能坐起来和我说话。”顾南风的语气里,竟然有罕见的感恩意味。
他救了她?他的身子那般单薄,还来救她?难怪他现在看起来,几乎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邬雪琴的心狠狠痛了起来。
“王爷,小人的任务已经完成,该告退了。”
邬雪琴一愣。这是那首领萨满在说话,毕恭毕敬的声音,显得有些粗粝和沙哑,全然不符合她的猜测。
这是完全陌生的声音,不是他的。
莫非,只是人有相似,她猜错了?
顾南风笑容舒展,大手一挥道:“做的很好,全部下去领赏。”
“谢王爷。”
程式化的,受宠若惊的回答。这不是他。邬雪琴的心沉了下去。
失望地目送着这群人走了出去,那首领率先消失的身影显得那般虚弱落寞。邬雪琴忽然觉得一阵烦躁。
“南风,我好渴。”
顾南风坐在床沿为她掖被角,听到她这话,手里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
邬雪琴这才发现自己叫错了。她竟然叫他南风,天,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顾南风不会就此大做文章吧?他一定会的,看他现在的样子就知道了。
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有些呆掉地看着他。
给他一面镜子,他就知道他现在的样子有多白痴。如果再流点口水,他花了三十年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就要被摧毁殆尽了。
谁料,木头人只做了几秒,顾南风还是醒悟过来了,只是说话的声音有些结巴:“哦,那我去给你……嗯,倒水。”
还是不习惯他这样的态度,邬雪琴看着他满屋子找水。他眼睛长在鼻梁上,却好像不是用来看东西的。在屋子里像无头苍蝇一般转了好几圈,却没发现茶壶和水杯就在桌上,他的眼皮底下。
也是,他做王爷的,渴的时候连嘴皮子都不用动,自然就有人把水送到他手上来了。
他什么时候又给人倒过水了?
或许是,他不是不知道茶壶在哪里,只是一下子晕了头,有些无所适从了。
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让邬雪琴心里觉得不舒服。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对她好,可她真的受不了。这里面多少有一些屈昂威胁的阴影在里面,可是就算屈昂没有提醒,她就能安然接受了么?
不能,不能。
除非记忆能消褪,除非受过的屈辱可以被当作荣耀。
“喂,你的眼睛是用来当摆设的吗?水除了在桌上,还能在哪里?”她没好气地提醒。
顾南风身子僵了一僵,邬雪琴能看到他的侧脸,他的表情好不狼狈。
如果换在以往,他该会粗声大气地顶回来吧,可是他只是“哦”了一声,就手忙脚乱地去给她倒水。
不知怎么的,邬雪琴更加生气起来。
“顾南风,停手吧,我不用你给我倒水。外面不是没有仆人,你这个样子被人家看见了像什么样?”
顾南风像是没听到一样,笨拙地取了套青玉的茶碗,满满地倒了一碗水,用双手捧着,转过身来。
邬雪琴看得一怔。
出乎意料的,他脸上竟没有丝毫的发怒迹象,反而相当平和。
不,不是平和,是虔诚。虔诚啊!
现在,连骂他都没有用了吗?
邬雪琴心中一烦,皱着眉接过他手中的青玉碗,却发现那碗烫的很,邬雪琴慌忙放在了床边的茶几上——桌子到这儿十几步,他就是捧着这么个烫得要命的东西,这么面不改色地端过来的吗?
他心里到底在想写什么啊?
顾南风站在一旁,两只手被烫的红红的,他到这时候才知道痛了,拼命地搓,举到嘴边哈气。
她心里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吼道:“顾南风,你这算什么?告诉你,我不吃你这套!”
“我怎么了?你又怎么不吃我这一套了?”顾南风龇牙咧嘴地反问,“你不要一醒来就发脾气,你这像是个刚活过来的人吗?”
他完全不看她的脸,自己咬牙道:“不准备点随时可以喝的温水在房里放着,这帮下人真是不想活了。”
没等邬雪琴反应过来,他抓起那只青玉碗摔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骄纵的作风又回来了。
外面待命的领事急忙进来,知道情况不好,一声不吭地跪在下面,连大气也不敢出。
顾南风面色铁青:“今天是你负责值班吗?”
那领事点点头,手脚都在发颤。
“人都是你管的?”
“是……”领事的上牙下牙直打哆嗦。
“茶壶里的热水是你们灌的吧?”
“是……”
顾南风点点头,指着桌上的茶壶:“喝下去。”
那领事的吓得面色煞白,哭都哭不出声来,只好跪着爬过去,将茶壶端起来。
邬雪琴再也看不下去,咬着牙从床上爬下来,几步奔到那领事跟前,在他将一壶滚烫的开水喝下去之前,夺下了茶壶。
那领事的感动的几乎要哭出来了。
“你下来做什么!疯了啊?”顾南风咬牙切齿地扶住她,“连站都站不稳还逞什么强?赶快回去……”
“你少来!”邬雪琴一把打开他的手,勉强扶着桌子才站住。
无缘无故被斥,顾南风也显得很恼怒:“我又怎么了?”
“顾南风,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哪有现成的温水?不都是将热水放凉了才有温水吗?你自己不会做这些事情,又不许别人进来伺候,自己搞不清楚状况,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赖在别人头上,你一向都这样蛮横惯了是不是?耍什么威风?你自己愚蠢烫了手,就要看着别人把肠子都烫坏是不是?只有你是人,下人就不是人吗?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蛮横狠毒的人?”
她说得太快太急,大口大口地喘气,胸口起伏不定。
顾南风站在那里,有一会没说话,好像是在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过了一会,小声道:“你发什么火啊,我……我确实认为温水是直接就有的。况且,就算是我做错了,你在床上说不就好了吗?下人的命是命,你的就不是了吗?好不容易又活过来,你就不能珍惜点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从开始的心虚,到后来变得理直气壮,伸手过来要搀扶她。
邬雪琴叹了一口气,情绪一激动,她确实有些体力不支的眩晕了,任由顾南风几乎是架着她回到了床上,然后对跪在地上战战兢兢的领事道:“出去吧,没你的事了。他要是找你的麻烦,你来找我。”
那仆人哪敢接她的这句话,一连道了好几声:“谢王爷饶命,谢姑娘恩德”,才抹着眼泪退出去。
顾南风闷不做声地重新拣了只碗,给她倒了杯热水,拿扇子扇,又用嘴吹了半天,才将碗端过来递给她,看着她喝了下去,又给她弄第二碗水——自始自终没说话。
邬雪琴知道自己的话伤到了他的自尊心。他看到自己醒来,那种高兴到神采飞扬的神态,她永远也忘不了。他发脾气,也是因为看她没有及时地喝到水,而迁怒于仆人。
而她冲他发火,就只是为他对下人的轻贱么?说到底,她不也是将心中的闷火迁怒于他么?
可是,就算是做错了,也不想道歉。他最好一直都这样不要理她,不要和她说话,她就最高兴了。
这是一个她发誓要将其置之死地的人,她绝不能因为他的小恩小惠而心软。
可是,那个人显然和她的想法相反,没憋多大一会就又开口了:“雪儿……”
邬雪琴心中苦笑,不想和他说话,眨了眨眼皮表示听到了,让他有话直说。
“你昏睡的时候,手里一直握着一样东西,是什么?”
邬雪琴皱起眉头,她的手里握着东西?有吗?
顾南风继续道:“你握得死死的,我怎么掰也掰不开。该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吧?”
重要的东西……
一个画面闪电般地划过她的大脑,她蓦然睁大了眼睛,看看手里,已经没有了那样东西,于是立刻开始在床上一顿乱翻乱找。
“找什么呢?”
顾南风凑过来,虽然不知道她在找什么,可是也不由得帮她翻床揭枕地找。
找了半天没找着,邬雪琴忽然觉得一阵心慌,停下手里的动作,颤声问:“顾南风,紫安……紫安是不是已经……已经……”
顾南风手里的动作停了一停,又继续翻找。
他的脸背对着她,看不清是什么表情。可是他的声音传过来,是闷闷的:“嗯,她死了。她害了你,可是也为这个付出了代价,你——不要怪她。”
邬雪琴激动地抓住顾南风的手:“不是她害我的,不是!”
顾南风转过头来,一脸的不敢置信:“你说什么?不是她还能有谁?”
“我手里……我手里握着的,是一截断掉的指甲,那不是紫安的,紫安从来不留长指甲!”邬雪琴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微微发抖。
顾南风一时怔住了,他的手从床上拿起,伸到她面前,展开:“是不是这个?”
一截染了丹寇的,殷红的指甲,半寸来长。形状修剪得极为精致。
声音,装扮,都可以作假,可是,从人身上掉落下来的东西,作不了假。
这就是当日死去之前,她从那个人指甲上,侥幸获得的证物。
这就是她在昏迷之中,一直紧攥不放的东西。
一切可以真相大白了,只是当初被错怪,被责难,甚至间接因此而死的那个紫安,已经不在了。
“有人一直在试图嫁祸紫安。这人心思太缜密了,缜密得让人害怕。紫安曾经公开放话,要置我于死地,全府上下的人都听到了。这人恐怕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嫁祸紫安而除掉我的。她知道,一旦我出了什么事,所有的人都会怀疑到紫安的头上。她只需要采用紫安惯用的手法,秘密杀死我,就可以让紫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邬雪琴打了个冷战,继续道:“在杀我的那天,她蓄意模仿紫安的形象,模仿紫安的声音,甚至连在我失去辨别能力的时候,她都伪装得一丝不苟——她什么破绽都没有留下——除了这截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