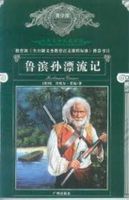她虽然已经来过这里一次,也知道了齐师墨是何许人也,甚至和他有了男女间最为亲密的接触……可是,再次来到那扇紧闭的门前,邬雪琴仍然感觉没有底气。
手已经举起,却迟迟没有敲落。
如果他开门,见到她,她该说什么好呢?
对他说:“你给我做的手术出现了后遗症,你这蹩脚的医生!”
这样未免太粗野,或者她客客气气地说:“我偶然路过,见你房里还亮着灯,所以顺便来看看你。”
……可这也未免太扯了……深更半夜的,谁会路过这样一个死人墓穴般的地方?
自己都在觉得好笑,忽然,半空“扑棱棱”地一阵响,邬雪琴急忙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冲着她的面颊,攻势凌厉地破空而来!
“啊——”
邬雪琴本能惊叫一声,挥袖去挡,那黑乎乎的一团却疾速拂过她的面颊,又扑棱棱地飞到榕树上,不见了。
原来是一只夜鸟而已!
“谁在外面?”
邬雪琴正兀自惊魂未定,屋子里却已传来齐师墨警觉的声音。
邬雪琴好不尴尬,只得应声:“我——是我,邬雪琴。”
里面静默了一会,才道:“门没关。”
那声音,依旧是坚不可摧的,千年寒冰。齐师墨。
邬雪琴苦笑一声,伸手一推,门果然开了。
一股浓烈的药味,扑鼻而来,苦涩而腥烈。
记得上次进来的时候,是迎面的一阵笔墨书香,这次怎么……
待看清屋内的情形,邬雪琴止不住一愣。
屋中摆起了一小桌,桌上放着一大罐冒着腾腾热气的瓦罐,想来那股苦腥的味道,就是从瓦罐中传来。
除了这瓦罐,还有一个大海碗,一个细白瓷的酒瓶,一只小酒盅,齐师墨坐在桌前,将那瓦罐之中的东西盛出满满一海碗,面无表情地大口吞掉,再倒满一杯酒,端起来仰脖吞下,依旧是面无表情。
那瓦罐中倒出的东西,黑糊糊,黏稠稠,冒着极难闻的热气,可他似乎毫不介意,大口地吃着,似乎鼻子和味蕾已经失灵了一般。
见她进来,他头也不抬,似乎眼睛也失灵了一般。
邬雪琴也不觉得奇怪,自己走了过来,在他桌前坐下:“你生病了吗?”
齐师墨不答话,又从瓦罐中舀一碗,面无表情地吃了,喝掉一杯酒,才慢腾腾道:“你眼瞎了吗,我在吃晚饭。”
邬雪琴一惊,指着那瓦罐中冒着恶劣气味的粘稠黑糊:“这就是你的晚饭?能吃吗?”
齐师墨淡淡道:“不仅好吃,而且大补。你要不要也来一点?”
邬雪琴慌不迭地摆手:“谢了,这东西我一看就饱了。而且,我拒绝吃看不出原材料的食物。”
齐师墨抬眸瞧了她一眼:“骄纵的女人。”
“这和骄纵没什么关系吧?”邬雪琴气道:“这样的东西能被称作食物吗?”
“怎么不能?”齐师墨伸出右手,弯着手指数道:“青蛇、蜈蚣、蝎子、壁虎、蟾蜍,每一样都是食物,混在一起煮烂成五毒羹,当然也是食物。”
……天,这些黑糊糊的东西,竟然是……
而他竟然在……吃……
邬雪琴只觉得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地难受,胃里的东西直往上涌,忍不住俯下身子干呕起来,连眼泪都涌了出来。
“还没吃到肚子里就开始吐,我说你骄纵错了吗?”齐师墨冷哼一声,倒了一杯酒,推到她面前:“喝点酒压一压。”
“我才不要!”邬雪琴一把将酒杯推开,“我才不要喝臭虫和老鼠泡的酒。”
齐师墨不耐道:“蠢货,这是今年新酿的米酒。”
邬雪琴狐疑地看着他,端起杯闻了闻,浅绿色的酒液,香甜无害的糯米香味,应该没问题,再加上实在是恶心得难受,便端起酒杯,一口喝了个干净。
好甜,好香,还有股馥郁的酒味,真好喝……比雪碧和可乐还好喝一百倍。
邬雪琴放下酒杯,意犹未尽,盯着齐师墨手里的酒瓶,眼睛直放绿光。
“干什么?”齐师墨警觉起来,将酒瓶牢牢攥在手里。
“还要喝。”无比贪婪的声音。
“不给。”
“给我啦。”邬雪琴绕过桌子,扑了上来。
“不给!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馋嘴的女人?干什么?啊——”齐师墨叫了一声,手上已被咬出一排牙印。
那酒瓶,自然已经到了邬雪琴手里。
齐师墨怒道:“怎么你是狗吗?还会咬人?”
邬雪琴抓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得意洋洋道:“这叫巧取不如豪夺。”端起酒杯,微笑着倒进咽喉。
喝完,犹自赞不绝口:“好酒,好甜。”
她原本是不胜酒力,偏又贪杯,两杯酒下肚,面颊上已泛起胭脂般的绯红,眼中水波流转。
齐师墨站在一旁看着,冰冷道:“喝米酒都会醉,你就算了吧。”
说着,拉住她一只胳膊,劈手就要夺她的杯子。
邬雪琴早有防备,敏捷地躲开,笑道:“你总能喝到这样的美酒,让给我一点又何妨,小气——”
“鬼”字还没出口,唇齿已经被他的唇温柔地堵住。他的舌也趁势蜿蜒进来,如游龙一般裹住她的丁香,在她温暖而柔软的唇齿间翻弄,扭转,忘情地吮吸她的芳泽。
干——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