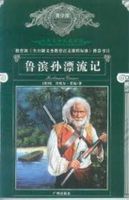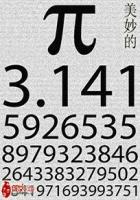商怡安 著
非份之想
一向沉默少言的赵本善这年头也不安份起来。
他意外发现五分厂的统计员鲁丽酷似自己的妻子。举手投足,腰段儿,走路态势都象,所不同的是脸蛋儿深得比妻子白净,虽说也成家立业,少年风韵犹存,曲线优美得给人一种享受。要是她看得起,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交给她,他想。
鲁丽爱说爱笑,还跟他开过几次玩笑,且毫无顾忌,有时当着旁人面,有时就只他俩,弄得怪不好意思的。有一回鲁丽向他提出要上他家里去玩玩。这本是一件常事,赵本善却吓得不敢大声冒气,颤悠悠地说,那要等妻子出差再去。声音象老鼠。鲁丽听了笑眯眯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盯了他好久才点头。这场景一直在赵本善心中无法消失,他的心常因她那注视而绽放蓓蕾,灵魂常因她的倩影而升腾,他好爱鲁丽,他觉得鲁丽好那个,他被鲁丽年轻成熟,绝伦的美丽感动着。从此,他做过许许多多美丽奇妙的梦,梦得羞不堪言。
赵本善从那时候起就盼着妻子能出几天差,心想只要妻子一出差他就。想到这里,他脸上一阵阵的燥热,都三十大几的人了,还不安份,是自己的妻子不好么?赵本善自己叩问自己,自己也说不清。兴许是偷吃别人家葡萄另有一番滋味,这滋味儿兴许能给自己带来新的温馨,新的感觉,他想这是个难得诠释的谜。
机会终于来了。
赵本善的妻子要随单位的小车出差南京审核一个技改项目,来回至少要三天。下午四点,妻快要动身,临行前赵本善特意要为她煮了一碗荷包鸡蛋,眼看这渴望已久的日子已经扎扎实实地拢来,他已经心不在焉,神不守舍了,在鸡蛋里放了盐又放糖。妻子平时很少享受丈夫的这种温存,竟有滋有味地吃了一碗,放心地走了。
赵本善碗都没来得及收拾就迫不及待地赶到分厂里去了。谢天谢地,鲁丽正独自在统计室埋头抄表,乌黑的头发遮挡了大半边脸,好清爽,好妩媚。赵本善不知为什么这时见到她心里却慌慌的,脚杆儿直罗嗦,喉眼里象塞了团棉絮,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脸上只觉得火燎燎的生痛。当他壮着胆子告诉她说妻子已经出差时,话刚出口就感觉到有一股血一样的东西堵到他的胸口又涌到头上,差点要栽倒。鲁丽抬头怔怔地望着他,过了好半天才完全弄清他的来意,露出满脸的微笑。那笑,笑得好甜蜜,好自然,脸颊绯红,眸子里光闪闪的。赵本善赶着又吐出一句,晚上我在家等。说完便再不敢抬头看她,分明意会到鲁丽已颔首而应,目光中透露出令人心动的专注。赵本善悻悻地离开了,心里象蜜蜂在叫,一身的轻松,心虽然还在跳,却跳到使他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
晚上,似乎一种魔力的驱使,使赵本善表现出少见的勤快,他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陈旧不平的地板被擦得泛亮,所有的家具被抹得在日光灯下耀耀生辉,桌椅上一尘不染,整个房间打扮得给人一种优雅、温馨,给人一种舒适、乐观。他原本想在这殷勤的劳作中迎接鲁丽的到来,以缓解自己静候贵客敲门而至造成的慌乱。然而时针已毫不客气地指向深夜十一点,却不见鲁丽露面。无奈,他只好静候在小客厅里,任凭骨子里热血横流,任凭心中欲火燃烧。
他笃信她会来的。他住在这幢宿舍的尽头一楼,楼上一般十点以后就熄灯就寝,这里显得静极了,寂静得能听清楚楼外远处走动的脚步声。鲁丽过去曾因工作上的事儿同伙伴们来过两回,每回都对这住在楼尽头的优势赞不绝口,然而今夜她怎么还不来呢?
十二点了,仍不见鲁丽的踪影,赵本善有些坐不住了。他想躺下,拴上门,拉灭灯,兴许鲁丽很快就会来的,说不准她已在老远发现这里亮着灯,怀疑有人来访不敢轻易走近哩。赵本善为自己的这一猜想感到一阵高兴,觉得甚是英明,他责怪自己为啥早不想到这一层,差点要打自己一巴掌。
他真的躺下了,拉灭了灯。
一种被压抑、禁锢已久的本能生命欲求使他变得格外精神,他没有丝毫睡意,屏息细听门外的动静,饥渴难耐地期待那种脚步声,那种与妻子一般走路步态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一定很轻,他想。他入神地倾听着。此时此刻,他听得出门外任何一种微细的响声,这响声给他带来无限的联想。他幻想着鲁丽出现了,哟,打扮得好入时好漂亮啊,刚烫过的刘海高高翘在凝脂般光洁的额上,淋淋沥沥飘散着的头发,瀑布般的倾泻在肩头,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被描过的眉睫上,淡淡的弯弯的月亮似的,明亮的大眼流淌出一种温顺迷人的光芒,微微抹过口红的嘴唇,轮角清晰而鲜亮,她上穿一件杏黄色束腰式新潮衫,下配一条黑闪闪的弹力裤,一个身材匀称窈窕,娉娉婷婷弥漫着青春魅力的少妇正向他款款走来,好一付丹青照人的风采。他的心儿象打鼓一样扑扑嗵嗵的蹦跳,他欣喜地紧紧拥住了她,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化作一股乳汁似的东西从后脑勺儿窜到脚趾头,又从脚趾头蹿到脊梁,在每一根骨子里荡漾。赵本善完全陶醉了,陶醉在如痴如醉奇妙的幻想中。他清楚这是一种幻觉,然而又不愿从这幻觉中走出来,任它心驰神往,他要充分地、尽情地消受,巴不得在这种如云如雾的幸福中死去。
就在此刻,远处真的传来脚步声,且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听出是他所熟悉的那种脚步声,赵本善听到这声音时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心都快要炸,头皮子一麻麻的,慌乱得不知所措。他想翻身下床,可是来不及了,他的门已被轻轻敲了两下,是用指甲盖儿敲的,那声音传导着一种神秘,一种亲切,象涓涓流水,象微风吹拂,好细腻、好温柔。他的心颤粟了,浑身醉酥酥的瘫软,刹那间几乎失去了开门的力气,甚至后悔不该去约好晚上来。
软蛋。赵本善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当渴慕已久的灿烂辉煌的时刻来到面前,自己竟变得如此懦弱畏怯。这一瞬间,他真正领略到勇敢这字眼的含义,又为一瞬间的畏怯而后悔。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伸出高频率抖动的手,扭动了门锁,拉亮了电灯。
天!赵本善一下子傻了眼,进来的不是别人,是妻。妻子一脸的笑,一进门便夸他那碗鸡蛋煮得好,说鸡蛋定心,让她不能离去。原来漳河大桥出事,车在途中又拐了回来。
象一堆熊熊焰火被突如其来的风暴掀进了大海,赵本善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不过他只愣了片刻便回过神来。妻很快就溜进了被他暖热的被窝里。赵本善此刻心境复杂极了,觉得浑身象有蚂蚁在爬,不自在而又无可奈何。好懊丧,好晦气。
灯又熄灭了,门外死样的肃静,不料这时远处又隐约传来砰砰的脚步声,赵本善此刻却害怕起这声音,猛然间心狂跳起来,叮咚叮咚的呼吸都显得十分困难。黑夜仍笼罩着一切,鲁丽还随时都会来的呀!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心被那脚步踏得鲜血淋漓。他的血都要凝固了,那声音越来越近,他的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他恨不能弃家逃走,差点没拿起菜刀抹向自己。再听听,苍天有眼,这脚步声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消失了。身边的妻被旅途的疲惫夺走了精力,竟发出细小的鼾声。赵本善出了一身冷汗,总算松了口气。
夜,完全剥夺了赵本善的睡意,他整个心身都处在一级战备状态里,恐惧的折磨还让他失去在床上辗转反侧的自由,妻细小的鼾声时时对他进行着巨大的攻击,连门外鼠叫的声音都能叫他心惊肉跳,慌乱不已。好难受,长夜难眠,提心吊胆。他只好在这黑暗中睁大眼睛,等待着命运的审判,俨然是一个被恶魔捉住绑押在翻滚油锅前的唐僧,欲哭不可,欲笑不能,任命运宰割吧,快放进油锅里炸吧,他内心在声嘶力竭地呼喊,黑暗,快要把他逼成一个疯人。
天终于亮了,倍受煎熬的赵本善终于盼来光明,脱离了险境。晨风慰抚着他受伤的心,他又恢复了正常,如同走出恐怖的森林,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觉得世间一切都很太平。
东方的曙光仍象昨天一样迷人。这一夜鲁丽没有来。
这一夜鲁丽压根就没有打算来。在黑暗中沉浮了一个通宵的赵本善白费了光阴,他两眼被熬得象乌眼鸡似的,紫乎乎的难看,整个身子都瘦了一圈,神情恍惚,一夜之间象是苍老了许多。
这天一上班,赵本善与鲁丽正好在厂门口相遇。赵本善百感交集,心涌狂涛,仿佛有一肚子苦水要找她倒。可是他发现鲁丽居然象往常一样平静,平静得没有一丝异样,仿佛没有昨天,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
赵本善悲哀极了,他恨不得倒在厂门口嚎啕大哭一场。
不过,从此以后,赵本善再没有做过那种美妙的梦,他觉得女人看不透说不清,他觉得自己的妻子还是很漂亮。只是自己他妈的生得好贱,好贱。
箫笛声声
玉叶有心事了,坐在门前的柴垛上,呆呆望着远方。
太阳刚溜进了大黑山那边,一弯新月挂在西山的天上。
落日,奶油色的余晖把大地涂得通亮,通亮。月儿啊!成了天边多余的光。你不能来得晚些吗?在落日余晖散尽的时候,在忙夜的人们需要你的时候,月亮却不见了,她被大黑山叼走,她被大黑山咽下。天上只剩下星星,无数星星,晶莹的星星,露珠儿似地抖动着,汇泛出融融的清辉,悄悄散满山峪,散满柳家寨子,散满人间,充实着静静的夜晚,装点着墨绿的田禾,抚慰着寂静的山林。天上的星姑姑哟,可真好啊。地上的人吗?
姐姐哟,就象那西山天上的月儿,欺骗了林子哥。在林子哥最需要的时候,象月亮一样坠进大黑山去了。
玉叶望着神秘灿烂的天际,凝睇着朦胧的远方,心里饱含着恨怜、怨叹,充满了无限的怅惘。
一
叶儿。
一声亲切的呼唤,把玉叶从万千遐想中惊醒。
她在这里坐了多少呢?送走了夕阳余晖,咒落了残月,等来了亮晶晶的星儿,却记不起自己是否吃过晚餐。听到父亲的唤声,玉叶噌地站起身来,走到父亲跟前,一头扑进父亲怀里,紧紧抱住父亲的身子,没有平时的娇嗔,失去了往常的自矜,摇了摇父亲那病后虚弱、略显佝偻的身躯,接下来是一阵无声的抽泣。
娘啊,您为什么要早早地离开叶儿呢?您一生辛勤的劳作,就象山溪的水一样奔流不息。您又那样的善良,从我们姐妹俩懂事那时起,您就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教我们要懂得山里人情的珍贵,懂得自身的贵贱、荣誉和耻辱。还有好多好多的话儿,您没有说完就悄悄地去了,带走了一身的劳疾。娘啊,您也想不到吧?姐姐已经洞房花烛了。您也动气吧?
她嫁的不是林子哥。
泪,也从父亲眼里流出。他明白叶儿心里正难受着。珠泪滚过面颊,滴在玉叶的肩头,也落在自己的心上。
玉娄逆儿,早知如今,当初没把那血泡掼进粪缸里溺死,没一扁担吹断你那双四处奔窜的小蹄子。他好后悔啊,后悔自己能整治住十几块责任田,却治不了亲生女儿。玉娄是什么时候开始滑过去呢?在她的身上失去了什么呢?自己在这块洪荒的土地里有过多少耕耘?现在他记也记不清,或者只记得影影绰绰。但他清楚地记得三年前林子参军临走的那个夜晚。
那时,他的眼睛不像如今这样昏花,月光下亲眼看见是玉搂挽着林子的手臂,把他拉向寨子旁。都怪那不知世俗的夜风,把自己女儿的私情话都扔了过来:
到了部队,你说你还想我不?他听见这是玉娄调皮的调儿。
想。他知道憨厚的林子会这样诚实回答。
升了官儿变心不?
我不是那种人。
上有青天下有地,凭口说的不算,来,勾着指头赌咒。
别胡闹。
嘿,你不敢伸手?
我不敢,我是怕你,好,来。
来。
谁要变心雷劈火烧不如狗。
我若丢你死在路旁无人埋。
啊,多结实的咒语呀,出自女儿之口,顺着林子的心,一口一个应承,凭着就能夫妻偕老呀。父亲不为听了这儿女私情而羞恼,这位乡俗淳厚的老汉,反而心中荡漾起快意。从实说来,打林子懂事起他就暗暗喜欢他,他喜欢这孩子沉着,厚道,精明能干。此刻,这水牯壮实的后生,放学回村路过他家菜园子帮他翻地,喊他大伯,替他挖山药,夜里给二女儿玉叶补课等诸多的举动,一幕一幕在他眼前展现。
他耐不住性子了,他甚至比女儿还要高兴十倍、百倍、趁着他俩不注意便轻轻溜回家,来到患病的老伴床前,时而低声嘀咕,时而大声说笑,忙把他所遇到的一切毫不保留地说给老伴听,乐得老伴拖着病身连夜摸到林子家,亲口许下女儿的终身大事。
二
山里人性情直,定了婚就似乎是了却了一块心病。女儿是有主儿的人,静等林子退伍回来娶亲。父亲整日在责任田离勾头耕地,从此,就很少过问他亲手播下种子的另一块土地。
林子来信了。听老伴夜里说。
林子立功了。是老伴夜里讲。
姐姐进城烫发了。这是玉叶报的信。
烫发?父亲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如今山村的姑娘也有人烫发。可玉娄烫的是什么发形?当他发现玉娄头上成了一串一串鸡冠花,一缕缕狗尾巴时,几乎要怒吼,但他只是叹了口气,既然已烫了。
姐姐买了高跟鞋。玉叶用不无告状的口气说:那是瞎花钱,上山过坎拐断脚。父亲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当他发现玉娄在山道上走路一拐一瘸时,又几乎要怒吼。但又只是叹了口气,妞她娘不在了,让孩子自己打扮吧,反正是有主儿的人,快出阁了。
姐,你不能乱来哟,犯军婚法哩。玉娄的行迹有些不轨了,玉叶实在看不过打扮得日益娇艳的姐姐了,毫不拐弯地警告她。
屁,军婚法保护的是结为夫妻的哩,未婚妻也管么?别吓唬,我查过书哩,《婚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配偶你知咋讲?玉娄唾沫溅到玉叶的脸上,砸得她眼睛一眨一眨哩:配偶是指给军人当了婆娘哩,我给林子当了婆娘么?玉娄还自我暴露地说:我早听说了,如今当兵的升不了官儿,退伍回来还不是在这山沟里当农民,有多大出息。看,玉娄比妹妹精得多哩,她背得了法定的条款,讲得出其中的道理哩,玉叶的话她能听半句么?不如耳旁风呢!
对父亲来说,如今责任田里他获得了丰收,成了山里人家的冒尖户,人们尊重他,选劳模冲他直举拳头,可是在另一块土地上,他打了败仗,被山里人看不起。玉娄在默默流淌的日子中,在粗心的父亲眼皮下,从勤变懒,从烫发开始产生了更高的欲望,为实现自己的欲望,她丢掉了山里人的美德,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贞节,伤败了山乡的淳朴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