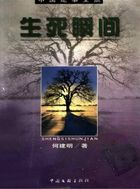我的童年,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歉收,但雪却是年年富足。
也许是受近几年天气变暖的影响,也许是黄河断流的原因,也许是砍伐森林、破坏植被的惩罚,总之,这几年我所在的城市,雪成了稀罕物。自小被黄河哺育,在雪的世界里长大的我,对雪有了一种久违的期盼,就像游子盼望回到故乡,就像村头的那棵老榕树下,望老了岁月,望白了双鬓的母亲。
今夜无电,静静地坐在阳台上,目光穿越时空界限,看床前十五的明月光,真真切切地体会着疑是地上霜的意境,心里什么也不想,耳朵里回响的是天地间雪花簌簌飘落的天籁之音,想起了那个多雪的冬季中的一件往事。
那时我在一所偏僻的山村学校任教,因寒假学生补课,我急忙往学校赶,头天还是冬阳慈祥,一夜之间便纷纷扬扬,雪们像赴约一样,山、树、村舍、道路,全是雪的杰作,就连电线上,也被雪装饰一新。尤其是那树,仿佛新娘,浑身雪白,真正的玉树琼枝、晶莹娇美。
坐在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上,裹紧大衣的我闭着眼,听着落雪和大地的对话,思想的野马在无垠的旷野上漫步。仿佛我与天地融为一体,我也变成了雪的兄弟姊妹,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意境上挥毫泼墨,装点江山。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那傲雪的梅花,点点滴滴地绽放在诗人的笔下和我的心中。
“啊——”
一声尖叫,打碎了我的风景画框,紧接着是一阵冷风夹着雪花旋转而进,车厢里一片慌乱。原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块车玻璃碎了,司机师傅将车停下来看了看,又翻了翻工具箱,然后无奈地说,哪一位有多余的衣服或毯子什么的,借来堵一堵。全车的人谁也不吱一声,包括我在内。虽然那玻璃只碎了一个角,但针大的窟窿牛大的风,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厉害。
靠近玻璃窗子的那位大嫂怀中的婴儿,一个劲地叫着“妈妈,我冷,冷……”
就在此时,一名瘦瘦的青年站了起来。“大嫂,咱俩换换位置吧。”那青年就坐在靠近发动机的座位上,那儿有发动机的热气扑来,是个好座位呢。
车继续往前开着,雪依旧默默无闻的精灵般的飞舞着,车厢里一阵冷似一阵。提了提衣领,我又闭上眼睛,进入雪的意境。
过了一阵,听不到冷风光顾车厢的声音,感觉也没有刚才那样冷了,我睁开眼一看,只见那青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身上当时很流行的军用棉大衣和那瘦小的身体堵住了那块破碎了的玻璃窗,像一尊雕像。
“你,能行吗?”
“行,没事,我这棉衣顶事着呢。”
全车人都投去热乎乎的眼光。
汽车像一位沉默的独行客,小心翼翼地向远方移动着。
就在我下车的时候,无意之中瞥见那青年人的一只棉衣袖子是空的。
今天,坐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巢壳里,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下,想起那场雪,想起那只空袖管,我这颗因日趋势利的现实而早已麻木冰冻的心,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心灵深处被震颤着、感动着,像三月春风里的柳芽,被暖暖的太阳温柔地融化成一片一片春的绿色、春的风景。
那只空袖管,宛如一面猎猎有声的旗帜,今生今世恐怕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