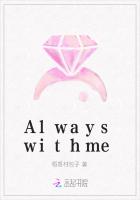李玖妍只弄破了一点皮肉,没弄破血管。听见响动跑过来的武装基干刚好看见阎瘌痢扔掉个什么东西,阎瘌痢把李玖妍推过来时,他又看见了李玖妍手腕上的血。武装基干便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子,跑过去往溪水里看,浅薄的溪水下面是光滑的卵石和白白的沙子,他一看就看见了那只黑发夹,又几步跑回来,对阎瘌痢说:“她好像掉了一只发夹。” 阎瘌痢没好气地说:“掉了就掉了!”武装基干鬼笑一下,又话里有话半庄半谐地问:“怎么还弄出血来了?”阎瘌痢瞪一瞪眼,正色说:“严肃点哈!”想想又说:“谁知道她,得了软脚病一样,走路还会摔跤!”
阎瘌痢不但包庇了李玖妍的自杀情节,一路上还对李玖妍比较关照。他老看李玖妍那只湿了的脚,说:“冷死你!”等看到潭底大队革委会门前那棵老柏树了,他叫车停下来,大声喊有没有人?喊了几句,有人答应了,推开一扇窗户,探着半个头来。他又喊:“快去找杨老八,就说我瘌痢子来了!”他点着一根烟,抽到一半时,杨老八就来了,一边颠着小跑一边扣棉袄,还偷空眯着眼睛看一下手表。阎瘌痢说:“老八你什么毛病哪,怎么还是老看表呀?赶快叫人煮面吧,要细挂面,一人煎一个荷包蛋,记得要多撒些胡椒粉啊。”杨老八说:“什么事啊?” 阎瘌痢便骂他耳朵被屎糊住了:“下面,煎蛋,听不懂啊?”杨老八眨着泡泡眼,瞟一下两个背枪的武装基干,又瞟李玖妍,样子有些惊讶。李玖妍站在那里簌簌地抖着。杨老八把阎瘌痢拉到一边,用嘴努一下李玖妍,小声说:“怎么回事呢?”阎瘌痢说:“你大主任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没通知你?”杨老八摇一下头。阎瘌痢说:“既然没通知你,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你还是赶紧叫人下面煎蛋吧。”杨老八嘟哝着说:“要吃我的,又要跟我卖关子。” 阎瘌痢笑骂道:“鬼样!”
杨老八正要去叫人,阎瘌痢又喊住他,叫他先弄个火盆过来。阎瘌痢说:“不要拿炭屑子,搁几块好炭,这鬼天气,骨头都要给它冷断了!”杨老八说:“不是要吃面吗,一吃不就热乎了?” 阎瘌痢说:“操,要个火盆,又不是要你老婆!”
火盆弄来了,阎瘌痢便叫李玖妍脱下鞋袜拿到火盆上烤,李玖妍不动,阎瘌痢说:“莫非还要我亲自动手?脱!”李玖妍脱了鞋,他又叫李玖妍烤裤腿,他伸脚把李玖妍的腿拨过去,说:“我在执行任务,你老实配合,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等到把面端上来,只有三碗,阎瘌痢皱皱眉问杨老八:“怎么才三碗?”杨老八说:“都吃呀?”阎瘌痢问他:“你想叫谁不吃呢?”杨老八咧咧嘴,只好又叫人端了一碗,放在李玖妍面前,却没盖荷包蛋。阎瘌痢说:“老八呀老八,不是我说你,你也是台面上的人,你就缺一个蛋吗?”杨老八说:“缺倒不缺,只怕吃出什么事来。”阎瘌痢说:“就你肚子里鬼多!我就不信邪,一个蛋嘛,会吃出什么事来?”
杨老八只好又叫人去煎了一个鸡蛋,亲自搛过来,把鸡蛋盖在李玖妍碗里。李玖妍却呆呆地不动筷子。阎瘌痢说:“你怎么不吃?”他看见李玖妍的眼睛里早没有泪迹了,干了,像蒙了一层灰,而且是灰灰地看着杨老八手腕上的瑞士手表。他以为她在看时间,便冷飕飕地哼一声,说:“你还用得着看时间?你现在有的是时间。”可李玖妍还那样看着。杨老八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便装着抓痒,把戴着表的左手藏到屁股后面。李玖妍忽然说:“请你把我的表还给我吧。”杨老八皱一下脸,但他装憨,像没听懂似的。阎瘌痢一愕,厉声说:“李玖妍,你要嘛老实吃面,要嘛老实坐着,若是再胡说八道我扇你!”李玖妍说:“那是我妈的表。”阎瘌痢在下面踢了她一脚,对杨老八说:“你到底叫哪只鬼下的面?”杨老八还没来得及反应,他那里就哗啦啦地将碗一推,说:“打破了盐罐子!盐不要钱的是不?是叫人吃呢还是叫人不吃?”说着一把扯起李玖妍,吼道:“走呀你!”
李玖妍只穿着一只鞋子,另一只鞋子和袜子还在火盆边烤着。阎瘌痢扭头叫武装基干给她拿着,自己抓住李玖妍一只胳膊,将光着一只脚的李玖妍推上了吉普车。车子开动以后,阎瘌痢便大声骂李玖妍:“你脑子里真的全是糨糊?这时候你还有心思记挂一块表?”李玖妍仰着一张白纸似的脸,眼睛灰蒙蒙地看看他,又看前面,一声不吭。风将她的头发吹得斜挂在脑后。阎瘌痢叹一口气,把鞋子和袜子递给她,叫她穿上,同时莫名其妙地摇头,摇了几下,他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李玖妍说了一句话:“你呀你呀,还拿什么茅草蔸骗我,你是眼睛没吃油呀,看不清好人坏人,到头来把自己弄得狗屄都不值!”
阎瘌痢嘴里没好话,这句话说得尤其邪痞。
大概是那年的农历三月初十左右,上午十一点多钟,阎瘌痢经过一路颠簸,终于把李玖妍押到了县城。本以为能交差完事,可县里说他们已经接到了地区的电话,还是请阎部长直接把人送到新洲去吧。他们将那份从金竹转出来的材料又交回给阎瘌痢,另外加了一纸公文,盖上大印,请阎瘌痢再辛苦一趟。新洲离县城一百几十公里,也是坑坑洼洼的沙石路,阎瘌痢头皮都红了,说,怎么这样啊,这么好的差事,你们就让我们金竹全包了?人家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计较?革命工作嘛,分什么你我?阎瘌痢虽然十分不情愿,但也没办法,只好将那辆破吉普加满油,又像蚂蚱似的开往新洲。他对李玖妍说:“这下好了,县里都放不下你,要把你放到新洲去了!”到了新洲,天都黑下来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人,交割之后,人家说免得麻烦,要阎瘌痢将李玖妍直接送到看守所去。阎瘌痢说:“我直接送到北京去算了!”人家就笑,说:“用不着到北京,不远,往西不到十里,你踩一脚油门就到了。”阎瘌痢便又掉头往西北,嘴里骂骂咧咧,说这帮狗东西不像话,一个个都懒得屁眼出油,都生怕沾一下手;又骂李玖妍,你也是,插队嘛就好好插队,跟人家谈什么鸟恋爱,害得老子尾巴骨都颠断了。快到看守所时,阎瘌痢问李玖妍:“要给你家里捎个口信么?”李玖妍摇摇头。阎瘌痢说:“你要捎,我就想办法给你捎,捎个口信不要紧的。”李玖妍还是摇头。阎瘌痢说:“不捎拉倒,你以为我愿意捎?”
交接时,阎瘌痢又和看守所所长吵了一架。所长是个黑黑的矮胖子,他一见李玖妍就皱眉头,扭脸问阎瘌痢:“她反抗了吗?”阎瘌痢说没有。所长说:“那犯人手腕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阎瘌痢说她解手时摔了一跤。所长又问:“你为什么没给犯人戴手铐?”阎瘌痢被他问烦了,说:“操,人跑掉了吗?这不是交给你们了吗?”所长说:“跑掉了就不是这样跟你说话了。”阎瘌痢一心想交差,不跟他纠缠,说:“好吧,我承认错误,我思想麻痹,反正现在人在你们手上,你们爱怎么铐就怎么铐,关我屁事!”所长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说话的,还有没有一点觉悟?”阎瘌痢忍不住,火蹿上来了:“老子从天不亮跑到现在,米水没沾牙,你说老子没觉悟?”所长脸色就变青了,说:“你充谁的老子?”阎瘌痢愣了愣,悻悻地说:“我充我自己的老子,行不行?”
他们回到金竹以后,包括李玖妍撒尿,一只黑发夹,杨老八的鸡蛋,还包括吵架,包括阎瘌痢的那句痞话,等等,全都被人传出来了。是谁传出来的猜都猜得到,除了那两个武装基干,还有谁呢?加上新洲看守所的赵所长又适时地奏了他一本,阎瘌痢受处分是必然的。据说阎瘌痢被下放到一个小山村去放牛,一放就是三年半。那小山村极偏僻,出来进去只有一条路,还要翻山越岭。他那个白豆似的电话员也受了牵连,也跟他去了那个小山村。电话员一路哭哭啼啼,不停嘴地骂死瘌痢骚瘌痢。
大概是那年的农历二月头上,也就是李玖妍被抓后大约十天左右,我们家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留寄信人的地址,落款处写着“内详”;信里的落款处则空在那儿,连年月日都没有;信里只有一句话,—你女儿在新洲看守所。我爸妈看着这封信,怎么也看不明白,我女儿在金竹呀,她跑到新洲看守所去干什么,他们觉得这是一封莫名其妙的信,要不就是寄错了。可是看地址和收信人姓名,又分明没错,那么这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要寄一封这样的信?他们忐忑不安,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想来想去,便给李玖妍去了一封信,在信里问她,你最近还好吗?又说我们很想念你,记得给家里写封信。
那回去金竹,我曾经找过阎瘌痢,但没找到,黄花萍说他退休了,带着他的女电话员回了皖南老家。我拜托过皖南一个姓陈的分销商,请他一定帮忙,给我找到这个人,我说这个叫阎国富的人曾经有恩于我们家,我想当面感谢他。姓陈的分销商是个踏实可靠的人,然而至今也是没给我一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