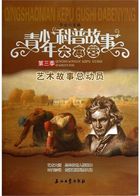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爸就那样勾着头黑着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坐了一阵子,出去买了一盒“梅雀”烟。“梅雀”烟很经济,一毛七分钱一盒,戒烟以前他就专抽“梅雀”。他往嘴里塞了一支“梅雀”,手抖抖地划火柴,划断了三根火柴,第四根火柴才把烟点着。他几口就把一支“梅雀”抽成了烟屁股,又摸出一支,伸出左手大拇指,在指甲上笃笃地顿一顿,把烟头顿空一截,尽管手还有点抖,却还是将烟屁股接上去了。他抽烟确实很专业,只有烟灰,没有烟屁股,烟屁股都变成了烟雾。他烟雾腾腾。他就像一个从里往外冒烟的人。
他接第五个烟屁股时,李玖妍忽然又抽泣了几声。抽泣声从板壁缝里漏出来,我爸像被人抽了一鞭子,身子一哆嗦,手又抖起来了,这回他怎么也接不上烟屁股了。他的脸一点点变青,又变紫,连暴出来的筋都是紫的。他扔掉烟屁股,火星子溅得老高。他说:“怪我呀!”过一会儿又说:“当年我怎么就没跟他们要个明白些的说法呢?”又抖抖地点上一根烟,又划了半天火柴,抽一口,摇摇头:“不行,这件事我一定要跟他们说说清楚,我要跟他们赌咒发誓!”他说着站起来,这里走两步,那里走两步,走得也不急,像散步,忽然在房门口站住,对房间里说:“妍子你听着,我李德民要是贪了公家一分钱我就不得好死!我今晚就不得好死!你好生看着!你们都睁开眼睛看着!”
那天晚上我爸抽掉了一包“梅雀”烟。我妈说别抽了,他像没听见,闷着头抽他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爸就去找南杂店的领导,他眼睛上兜着血丝,脸又黄又黑,像敷了一层烟膏,说话时满嘴烟臭,把领导熏得皱眉皱脸。领导一边听一边摇头。领导怪他不懂事,说:“老李呀,不是我说你,你也太不懂事了,这不是组织上的事吗?莫说我不知道这些事,就是知道,我能跟你说吗?”
我爸拔腿就走,又去找公司革委会。公司革委会主任不是别人,就是曾经给我吃过一颗水果糖的苏晓晓的爸爸、检举过我爸称盐时“给笑脸”的苏酒糟。我爸仗着跟苏酒糟在一个柜台上学过徒,一直喊苏酒糟做“师兄”。“师兄”从一个柜台营业员到领导岗位,可以说是一蹴而就,或者说坐直升机。他长了一个酒糟鼻子,从前在南杂店时大家都叫他苏酒糟,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大家便一律改口叫苏主任。但这天我爸既不叫“师兄”,也不叫苏主任,还是叫他苏酒糟。本来我爸也想改口叫一声苏主任的,大约心里憋着一口恶气,就直接叫苏酒糟了。我爸说:“苏酒糟,哪天我去你家,把我打的床和柜子桌子都拆掉。”苏酒糟说:“我没说打得不好呀,你拆它做什么呢?”我爸说:“不拆我过不得。”苏酒糟笑道:“莫非你想重新给我打一套?”我爸这时候真不简单,不枉在旧社会生意场上混过,愣了愣,转转眼珠子,用力咽下一口唾沫,竟把一口恶气也咽下去了,兜头接过苏酒糟的话,说:“重新打一套?你有木头吗?有木头的话我就给你再打一套。”苏酒糟说:“木头还不好办?你肯打我就有。”我爸又吞血一样吞下一口唾沫,说:“那好,我给你打。”
我爸真的又给苏酒糟打了一套家具。
李玖妍这次在家里住了五天,五天都是气闷闷地待在家里,中间只出去了一次,中午没回来吃饭。我妈那几天真不容易,自己心里一团乱麻,还要对她格外小心。她喜欢吃小鲫鱼,那天我妈就煎了一碗小鲫鱼,还汆了一碗肉片汤,焖了一碗烟笋,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人,只好叫我和李文革先吃。我们吃完了,我妈也吃完了,她却回来了。我妈看着她的脸色,说:“我们等你吃饭等了半天呢。”她也不作任何解释,不说自己去了哪里,只说一句我吃过了,就躲进房间里。我妈便摇头,闷闷地叹气。
那是我爸妈最憋闷的日子,就像出了一点黄晕的梅雨天,弄得他们时时刻刻想出油汗。他们说话都憋着喉咙,听得我喉咙里都像长了毛。尤其是我爸,回到家里就是一副罪孽深重的样子。想想也是,一个人活着活着,没想到活到一把年纪,没给儿女一点好处,反倒牵连儿女,耽误儿女的前程,不是罪孽是什么呢?估计他心里是扎着一把刀子的。他大约把给苏酒糟打家具看成是赎罪,下班回家就闷着头蹲在门口磨斧凿和刨刀,把它们磨得雪亮,用大拇指一刮,发出清脆的沙沙声,吃过晚饭就带着磨好的工具去了公司仓库门口的一个毡棚里,在那里熬夜给苏酒糟打家具。平常他帮人家打点家具都是慢腾腾地磨洋工,这回给苏酒糟打家具像拼命,整套家具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星期天也不歇一下。一般是半夜里才从毡棚里出来,一路咳嗽着,咳到巷子口里就把我咳醒了,我就知道是他回来了。
打好了一套家具,他就对苏酒糟说:“苏主任,我有一件事想求你。”苏酒糟说:“叫什么主任,苏酒糟嘛。说,求我什么事?”我爸说:“苏主任是这样的,前不久人家推荐我们家妍子进工厂,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卡住了。”苏酒糟说:“哦,这是好事呀,是被谁卡住的呢?”我爸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政审,我就是想问问,这政审是怎么回事?”苏酒糟嘿嘿地笑着,说:“我操,给我打了一点东西,就以为什么都可以问?”我爸说:“那当然那当然,我是不该这么问的。”苏酒糟又笑:“什么该问不该问,多大的鸟事,问吧问吧。”我爸这时候有点奴颜婢膝了,他讨好地看着苏酒糟:“我是说,我们这里会出什么材料呢?会不会翻我的历史旧账,还说我贪过污呢?”苏酒糟说:“谁家没有小孩?关系到小孩子嘛,应该不会有这种事吧,有这种事我能不知道?谅他们没这么大的胆子,敢瞒着老子干这种烂鸡巴的事!”我爸说:“可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呢。”苏酒糟就重重地翻一下眼皮,说:“扯淡吧?真的?那好,等我查查看,查到了看我不脱他一层皮!我看他下回还敢不敢!”我爸把眼圈弄得都有点红了,一个劲地点头:“我不说什么了,我就拜托你,若是今后还有这种事,苏主任你一定要关照一下。”苏酒糟说:“一定一定!”我爸得寸进尺,又说:“苏主任哪,我真的不是什么贪污犯,这点苏主任你应该清楚的,我确实一点都没贪过,哪怕贪了一点点,我都不得好死。我敢拿我的儿女赌咒发誓!”苏酒糟在我爸肩上亲热地拍两下,笑着说:“明白,明白明白!你看你,赌咒发誓干什么?不用不用!”
这以后,一直到现在,只要提到苏酒糟,我爸就发感叹:“那个人哪,油是油了一点,君子如水,小人如油嘛,当然不能说他有多好,可你也不能说他有多坏。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喜欢走点顺风罢了,可是,人嘛,谁又不喜欢走顺风呢?”
苏酒糟后来倒霉了,成了准“三种人”,也就是那种在“说清楚”运动中说不清楚的人。“说清楚”运动到底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我只知道人家说苏酒糟没说清楚,于是他只好又回到南杂店做老本行,跟我爸站一个柜台,负责卖酱菜。又过了两三个月,我就跟他女儿苏晓晓谈恋爱了。苏晓晓是苏酒糟家的老大,比我高两个年级,从小学到中学都跟我在一个学校。那回我摔倒后她扶我起来并给我吃了一颗水果糖,除了她本性善良之外,还因为她也是个残疾,—这一点我在前面说过,说到底我们是惺惺相惜;但仅凭这一点,我们还是谈不起恋爱的,关键是我们在一起卖过三年冰棒,而且她说她喜欢我的豆芽腿。我那两条软绵绵的豆芽腿有什么好?她喜欢得这么奇怪,这么病态,叫我自己都想不通,可她说她就喜欢那种滑滑的软软的感觉,摸上去柔若无骨,感觉像婴儿一样。她还把她那条残腿和我的腿放在一起,摸摸我的腿又摸摸自己的腿,说你看,你的像没长骨头一样,我的多难看,骨头包多大?这样就开始了,等过几天她再摸我的腿时,我就不客气了,摸了她的胸脯。我先把手放在她肩上,然后往下一滑,就滑到她胸脯上了。她身子一抖,说你该死!但只说不动,由我摸。开始是隔着衣服摸,摸着摸着我的手就钻进她衣服里去了,贴肉摸。其实我也在发抖,而且抖得比她还厉害,不过摸了几回就好些了,不抖了。她的胸脯真不错。那时我们相处得确实很亲密。她梳两根齐胸的粗辫子,颧骨稍稍有点宽,嘴巴比较大,嘴角边有一颗小黑痣。因为发育得很好,走路时又一歪一扭,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前翘一下后翘一下,一上一下,两“翘”都比较高。她那条好腿很丰腴很粗壮,这种丰腴和粗壮是一种充满生机的感觉,这一点从她的脚脖子就能看出来。她的脚脖子非常圆润,白里透红,长着细细的浓密的汗毛。汗毛是浅褐色的,让人想入非非。
有一天我摸她,大约摸得有点过分,把她摸得不省人事。开始时她还比较正常,跟以前我摸她时一样,浑身抖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我摸到她哪里,她哪里就蹦起一片鸡皮疙瘩。可是摸到后来,也就是摸到了她乳头上,她猛喘几下,突然往后一倒,双目紧闭,没一会儿两个嘴角里都流出了白沫。我被她吓坏了,手足无措,不明白她怎么这样。过后我知道这是羊角风,我就再也不敢摸她了。她比我大三岁,她爸爸苏酒糟说女大三,抱金砖。不要说金砖,金山我都不敢抱了。我们在一起时,我坐都不敢挨着她。她知道我是吓着了,便鼓励我别怕,说她这个病不要紧的,几年也难得发一次的,这次是不巧让我碰上了。凭良心说,她很难得,喜欢我的腿,脾气又好,说话从来不高声大气,声音就跟棉花糖似的。她问我:“假如人家问起你,我为什么会好好地就发病了,你会怎么说呢?会不会说是被你摸得呢?”我说:“没人知道你发病,所以也没人这么问。”她说:“傻瓜,我是说假如。”我说:“那我就承认是被我摸得。”她又骂我是傻瓜,她一本正经地说:“你真傻,这种事也有明说的?再说哪里一摸就会发病呢,跟你说了是碰巧的,不信你再摸摸看?”她腰一紧,胸脯翘过来,我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把手伸过去。我说:“我信我信。”
我不但不敢摸她,还有意无意地疏远她,待在一起也是心神不定,到后来便有点躲她了。不过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她,我只是在犹豫。我说不清我在担心什么。我得承认,我自私、胆小,什么事都要尽量算计清楚。苏晓晓虽然对我很好,可她会不会是一个麻烦,一个累赘?她的羊角风几年发一次?发起来危险不危险,会不会闹出人命?人命可是关天的。再说我也确实怕看那种口吐白沫的样子,她发起来是不是一定要吐白沫呢?
苏酒糟见苏晓晓抹眼泪,以为我占了便宜又不要他女儿了,于是气势汹汹地来找我,开口就问我碰没碰过他女儿。我说:“怎么算碰呢?”他想了想,说:“别的不提了,你就说她还是不是黄花闺女吧。”我松了一口气,说:“如果原来是,那么现在肯定还是。”苏酒糟说:“你敢保证吗?”我说:“当然保证。”苏酒糟点点头,恶狠狠地说:“能保证就好,不过我要告诉你,你要是敢骗我,我会把你的脑壳扭下来当尿壶。”我又保证说:“没问题的。”苏酒糟说:“那好,那你以后离她远点。”
苏酒糟便不再为难我,我们不谈了他好像很高兴,虽然他说过女大三抱金砖之类的话,但在他心里是认为我配不上他女儿的,他女儿除了偶尔会发发癫痫,哪样都比我强,而我再怎么说也比他女儿多残了一条腿。他用一种蚀本打倒算盘的口吻说:“也好,人家是两个人四条腿,你们呢,两个人才一条腿,真在一起的话,将来怎么过日子?”
这事被苏晓晓知道了,屁股一翘一翘地跑来臭骂了我一顿。
“李文兵我问你,你怎么敢保证我是黄花闺女?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好像我苏晓晓就认识你一个人,好像我只跟你一个人谈过恋爱,好像我让你检查过似的,你检查过吗?你倒想!你做梦吧,你撒泡尿照照自己吧!现在不说话了?哑了?什么德行!无情无义,自私自利,一个冷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