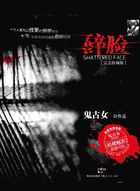元月5日 星期二 晴
一个不幸的人,无论他作出怎样的努力,一切都终将成为徒劳——我已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个结论。
我的一切努力,换来的只是班主任给我的“开始堕落”之类的训话。我真笨呵,也许我根本就没必要那样去做,这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更复杂。我的幼稚天真的想法,遭受到了一次狠狠地打击。但谁又能肯定,如果我不那样做,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呢?不幸的人呵,你已注定了你是不幸的,你也就无须后悔你的过去了。
本来我的所为是无可挑剔的。星期六晚上,我独自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着,思考着,我对我的将要实施的计划作了自认为很周密的思考。我要让项晓曼知道,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任何误会,我们之间是毫无疑问的同学关系。
回到教室里,里面亮着烛光,许多同学在忙着期末复习。我来到座位上,拿出笔和纸。虽然烛光是那么的昏暗,我又是借着别人昏暗的烛光,但我还是害怕别人发现我在做些什么——我甚至感到自己是在做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我用颤抖的手写下这么一行字:
忘记过去的一切,重新振作起来吧!
但我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加了一句互勉的话:
我们的明天是美好的!
可想而知,后面的时间,我根本就看不成书了。我拿出历史书,埋头装着看得很认真,其实心里老在推敲着这两句话。我千万次在心里证明,绝不会有任何岐义的。
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点燃了一支蜡烛,否则黑暗会将我围的严严实实。我多么希望其他同学快些离开啊!寝室里还有热门的话题在等着他们,何若呆在这里呢?我知道他们自然不会邀我一起离开的,但我已习惯独来独往了。自从文艺晚会以后,我就处于这样的境地。大概是班主任向他们宣传了什么吧!我已经快要成为李健环第二了。他们回到寝室里,很显然把我和项晓曼当作笑料来谈论,就像以前我们对待李健环一样(有几次我一回到寝室里,他们的谈话戛然而止)。
该走的终于走了,随着一声雷鸣般的意味深长的关门声,我已成为一只被主人无情地关在笼里的鸟。这一声惊响,就像一根针扎在我的伤口上。
但我终于有了难得的自由。
我重新看了一遍纸条上的两句话,然而小心地折起,夹在了项晓曼的英语书上。我想,她明天早上起来读英语时一定会看到的,绝不会落到他人之手的,我放心地离开了。以后又怎样的惴惴不安,哪里还用的着我多写呢?
我敢断言,第二天早上,项晓曼一定看了那张纸条。可是,我去教室里的时候,她正低着头在看书,似乎一点反应也没有。她能理解我吗?她是否还那么恨我呢?
我一本一本地翻着桌面上的书,我无法看进去,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令人心烦的东西。我抱着一丝的希望,看看是否能找出一点儿项晓曼的字迹来。但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我很清楚。我知道自己当时有多么可笑,但别人绝不会注意我这些可笑的举动,惟有上帝知道我在做什么,但上帝是理解我的。
项晓曼出去了,我已不在乎一切,所以我有勇气跟出去。
她可能是去楼下的小便处。在楼梯下,她发现了身有后人跟着,便转过身来。我无心去打量她,只是低着头,等着看她是否有话要说。但她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
“不能停一下吗?”我怯怯地问。但我不知道她停下来之后又该说些什么。
她真的停了下来,转过身,脸涨得通红;见我仍没开口,她有点不耐烦了,但还是尽量客气地说:“何必这样呢?你就不能安分一点吗?!”
……
她走了,我呆若木鸡。原来我这是不安分呵!我什么时候才能安分呢?什么叫安分?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我干了些什么?我似乎又做了一场噩梦……
自然有人告诉我什么叫安分。他就是班主任。
昨天下午班会课,易老师板着脸孔来到教室里,宣称他“有一件严肃的事情要处理”。我心里自然明白,但我无所谓,我还巴不得他早点儿“处理”完这件事,我要向他解释这一切,我再也忍受不了同学们的目光了。
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跟在易老师背后走出了教室。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勇气!也许只有内心完全清清白白的人才有这样的勇气!
来到易老师的房间里。他坐在办公桌后,又在前面放了一张凳子,让我坐下。这种布置完全跟审问犯人一样,受过他审问的人都很清楚。
“说说吧,以前我待你如何?”他摘下眼镜,语气听不出半点严厉。听说他每次审问学生都这么开头的。
“易老师,这没说的,你向来待我如同父母,我并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那你良心何在?我教过你多少遍,要学好不要学坏,你很清楚近来你做了多少对不起我的事,对不起你父母的事,更对不起你前途的事!你已经开始堕落了。”他的语气越来越重,脸色越来越难看。
“易老师,我敢对天发誓,我没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我可以向你说清楚……”
“在这里你有解释的余地吗?我不会让你作半点解释——因为每个人无论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都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同学的眼光是雪亮的,我想你不会忘记你跟项晓曼在溪边的约会吧!你也不会忘记文艺晚会上她跟你暗送秋波吧!这该有多么浪漫呵!我已忍受了一切,我没找过你,我只是找过项晓曼,只是狠狠地批评过她。在她稍微安分的时候,你又给她留下这么一张纸条。不错,你们的明天是美好的,可她已背叛了你,自觉地交出了这张纸条……”
“易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你没有说话的余地!看在我的一个学生的份上,我还是要教训你,这是我的责任!”
“我没有错,我不必受多余的教育!”我孔叫着,愤然离开了。
“你……。”
我不顾一切地跑开了。
如此简单的事情,可我却没有解释的权利,难道我就该这样无缘无故被人误解,受人嘲讽,遭人谩骂?!也许他们是对的,他们的“眼光是雪亮的”!
我不知何去何从,一个人来到操场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流泪。什么溪边约会,什么暗送秋波,这突如其来的侮辱诽谤,除了圣人外,谁受得了?可是,无辜的项晓曼竟然忍受了!还甘愿交出纸条,难怪她说我不安分,原来她这就叫安分?!
在这个可怕的世界,我不知日后还会出现多么可怕的事儿,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