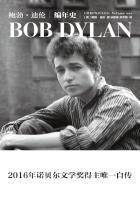端木蕻良的母亲先后为曹家生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端木蕻良是她的第四个儿子。关于端木蕻良的出生日子,在端木蕻良研究领域里始终有些混乱。其中沙金成认为是:“8月25日”;而胡文彬则认为是:“8月15日”;再有李兴武却指出是:“9月25日”。后经端木蕻良本人于1992年6月30日给笔者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他“出生于1912年阴历八月十五日”,这也就证实了端木蕻良在一篇题为《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文章中的自白:“我是191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出生。”这一天的阳历是9月25日星期六,也就是中秋节的晚上。
端木蕻良的本名为曹汉文,这是他的父亲曹仲元为他取的。由于曹仲元经常在南方,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因此便萌发了“反满”的倾向。所以,当他给他的儿子们取名字的时候,中间都有一个“汉”字。这个“汉”字也就是“汉人”、“汉族”的意思,公开表达了他的“反满”倾向。但是后来,端木蕻良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认为“汉”字的含义稍微狭隘了一些,所以就在他的家里第一个带头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汉文”改为“京平”。紧接着,他的大哥和三哥也跟随端木蕻良,把原有的“汉”字改为“京”字,分别叫曹京哲和曹京襄。只有他的二哥保留了他原来的名字,仍旧叫:曹汉奇。
有关端木蕻良的本名,在其他相关研究文字当中,几乎一直没有得到过统一。例如李兴武、沙金成、秦牧、丁言昭等,都把端木蕻良到天津以后才改的名字“曹京平”当成他的本名。而施本华则把端木蕻良笔名之一曹家京当成他的本名,所有这些,都遗漏了端木蕻良的真正本名应该是曹汉文。
另外,端木蕻良还有一个“乳名”,端木蕻良的乳名叫“兰柱”。乳名通常包含了特殊的意义,这意义里面往往又灌注了父母的意愿、期望等,“兰柱”谐音“拦住”,这是一个双关语,表示拦住,“到此为止了”的意思。这是因为端木蕻良的母亲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儿子了,不欲再生,故为最小的儿子起此名。不过事与愿违,这个“乳名”兰柱似乎并没有起作用,因为在生了端木蕻良以后,他的母亲又怀孕了,生下一个小女孩,只是这个女孩十分虚弱,还没长多大就死去了。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算是“拦住”了吧。
端木蕻良出生以后在他的出生地并没有住上多久,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由于当地土匪的不断骚扰,离开了他的老家鹭树。端木蕻良后来曾经这样说:“我生长的村子叫‘鹭村’,在我出生后一个月光景,就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在我母亲的乳房下,由着颠簸的大车,渡过了滚滚黑泥,突过了土匪的袭击,逃到了城里,从那之后,我没见过‘鹭树’。”如此匆匆地出逃,是因为有一天,曹仲元从上海、苏州游荡腻了回到家里,突然发现土匪已经踩好了路子,准备劫持他。正如当地的一种流行说法,“小乱住城,大乱住乡”。于是,他就当机立断,乘着暴风雨,连夜从镇上搬到昌图县城里。由于途中受了惊吓,端木蕻良的母亲把奶吓回去了,而后吃了很多催奶药都不灵,只好找奶母,但奶妈又带不好小端木蕻良。最后还是只好用炼乳喂他,那时只有一种“老鹰”牌的炼乳,端木蕻良就是吃这种炼乳长大的,所以他的母亲总说端木蕻良从小身上就有“火气”,就好像是老鹰的“火气”一样。
细算起来,端木蕻良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似乎已经不住在曹家的老宅,说明这是分家以后的事了。曹仲元一家不久又搬到了镇上的新房子里,端木蕻良说:“打记事起,我已是城里人了,从来没回到我出生的地方,但心中却一直想着它。从我母亲的话里,知道那村子叫鹭树。我的哥哥们是在老宅子里生的,独独我是在鹭树生的。当然,我对老宅子和新宅子都想去看看,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应该说,鹭树村到底是什么样子对端木蕻良来说是并不清楚的,也不可能给幼年的他留下任何一点儿的实在的记忆。然而,端木蕻良在他的很多长篇、短篇、散文当中,都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来描绘这个鹭树村。这个鹭树村似乎在端木蕻良整个的生命中显得是那么重要,时时刻刻呼唤着他的寻根意识和归属感。但事实上,他所描写的鹭树村完全是虚构在他的想象里,建立在他那思乡怀旧的意念之中的。端木蕻良说:关于鹭树村的许多故事,都是来自“我母亲的话里,还有的是来自鹭树的乡亲们口中,所听到的一些情况,就和我想象中的鹭树联合起来了,经过时间的推移,它们又在我脑海中生起新的幻想”。端木蕻良的幻想是在离开了鹭树,来到昌图县城以后开始的。
曹仲元刚到昌图的古榆城的时候,全家大小先是租住了一个倒闭的当铺财东马老钧的房子。关于这幢房子,端木蕻良是没有什么印象的。过了几年,在端木蕻良四五岁的时候,曹仲元又在聚兴成大院里找了房子,这里有很大的院子,大概有十几户人家住在这里。中间是院落,可以停留十几辆马车。端木蕻良一家住在高台阶上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里,正房在高台上面,居高临下,有独门独户的味道。曹仲元似乎搬到这里以后觉得有几分舒心,常常傍晚时刻,在房前的砖地上,放好地桌,独自喝茶,他很喜欢饮酒品茶。
这时候的端木蕻良开始有些记忆了,他记得他的母亲曾经梳过一种老式的大方头,这种大方头梳起来是非常费事的。过去当他母亲在老宅过着奴婢式的媳妇生活时,为了缩短梳理头发的时间,少挨婆婆的骂,通常是睡觉也不敢放开的,整晚上头不转动,身不翻,吃尽了苦头。端木蕻良母亲梳得最多的是一种叫“西瓜头”的,浓密的头发又黑又长,有时还梳一种盘转头,脚上穿着花盆底鞋。应该说离开了老宅的母亲是满意的,但是端木蕻良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的母亲一边在炕毡上缝制什么,一边又无缘无故地落下了眼泪,看到幼小的儿子,才强把眼泪忍了下去。
在聚兴成大院安顿下来以后,曹仲元和兴隆昌茶叶庄的掌柜又到南方去了。那时候,端木蕻良的小妹妹经常生病,端木蕻良母亲的身体也不很好,便无暇再照顾端木蕻良,只能把他交给了保姆。保姆姓王,心地很好,端木蕻良管她叫妈妈。这个“妈妈”非常疼爱端木蕻良,就好像疼爱亲生儿子一样。后来“妈妈”的亲生儿子来接她回去,端木蕻良扯住不放,“妈妈”又想走,又舍不得幼小的端木蕻良,把眼睛也哭坏了。最后“妈妈”还是被她的儿子接走了,端木蕻良为此大病了一场。
聚兴成大院其实是一个大杂院,端木蕻良的母亲为了睦邻友好,有时也和院子里的其他女眷们走动走动。西边一家是代销报纸的,四周用日本式的栅栏围着,自成院落。报商隔壁是一家私塾,窗明几净,住的也是新派人物。东边住了家朝鲜人,这家人十分穷苦,寒冬腊月都生不起火盆,墙上挂满了霜;快过年了,这家人买不起肉,就弄条狗来宰了。母亲告诉端木蕻良,他们亡国了。这是端木蕻良第一次听到“亡国”这个词儿,而且又有这么一家人活生生的形象,于是“亡国”两个字在端木蕻良幼小的心灵上烙上了阴影。
曹仲元曾经为他两个大儿子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但这位教师教的是旧学,曹仲元很不满意,便送他们到学堂里读新编的教科书。端木蕻良在六岁的时候上了县读小学,县读小学位于昌图城天齐庙的东堂。那时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其中有人、手、刀、尺等,还有一幅红黄白蓝黑的五色旗。读书识字对端木蕻良最初的效益,是幼年时就偷读了父亲皮箱里的《红楼梦》,虽并未看懂,只是看到里面善良的好人的不幸遭遇,渐渐激起了端木蕻良的不平。加上又发现作者和自己同姓,便引起了更大的兴趣与喜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端木蕻良还不满八岁。他常和小学生们一起唱着:“日本小鬼真真完,夺我旅顺大连湾,期满了,他还不归还……”那时候的小学生们还也会打着小旗子上街参加示威游行,喊着“雪我国耻,还我河山!”的口号。这或许是端木最早参与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