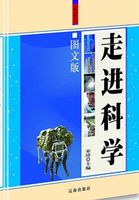报社领导要我这个文字记者赶到滴水堡拍一组回民欢度古尔邦节的照片;怎么推也推不掉,就因为我是回民。老实说,我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除了不吃猪肉,回民还有哪些风俗习惯,伊斯兰教又有哪些规矩、特别禁忌,并不熟悉。我忐忑不安地出发了。
司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喜欢开玩笑。我们曾多次一块出差,关系不错。
汽车在简易公路上行驶,路面像一块又长又大的洗衣板。加上上坡,汽车吃力地喘着气,由于这一带沟坎起伏,司机聚精会神地把着方向盘,顾不上和我扯淡了。
快八点钟了,太阳才慢慢地升起来,它也好像怕冷一样,脸冻得紫红紫红的。风沙很大,车棚上沙沙直响,灰蒙蒙的,不但见不到人和牲畜,连沙鸡和飞鸟都不见,满目荒凉。我于是迷迷瞪瞪打起盹来。
突然,我的整个身体向前猛冲,头撞在挡风玻璃上,差点把玻璃顶破。等我清醒过来,听到司机在骂:“不想活了吗?按喇叭都听不见……要死也得找个好地方……你们活够了也不能这样害人吧……”
汽车停在一个大沙沟的下坡上,三米外直挺挺地横躺着两个人!任你怎么骂,他们不但不还嘴,连动都不动一下。
我们只好下车。走到跟前一看:左边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趴在地上呻吟;右边看样子是个回民老头,五十开外,侧着脸好像怕羞似的,我们发现他的灰绿色的眼珠子翻了两下。司机的火气又上来了,冲着老头,唾沫星子飞溅:“你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怎么不说话,你是哑巴吗?”他仍不吭声,但布满皱纹的脸上却露出一丝憨笑。司机无可奈何,像是诅咒自己,又像是诅咒别人似的说:“今天算见了鬼!”
老头坐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沙土,显出红红的鼻子,特别刺眼,嘴唇动了两下,终于抱歉地说:“他有病,发烧,走不成……今天是古尔邦节,你们看在胡达的面上,把他送到滴水堡医院吧。”
“你们要搭车也行,怎么这样闹!这多危险,刹车稍微有点不灵,你们今天就报销了。你看!”司机指着车轮“犁”出来的两条深深的沙沟。
老头憨憨地笑着,在皮袄里掏了半天,我以为他在掏什么证明之类,结果掏出一把两寸来长的小梳子,梳起他的胡子来。他挺得意地说:“好哥哥,没办法。挡谁的车,车也不停。我把他背了半天才背到这里。我想,既然胡达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俩就一起无常吧。上天堂、进多灾海都认了。”
我和司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什么病?”我问。
“他说肚子疼,疼得在地上打滚!”红鼻子老头诚恳地说。病人这时又“哇哇”的吐起来。司机皱了皱眉头。老头赶紧爬过去,用一块发黄的白手帕给病人擦嘴,一摊黄色的液体很快渗进沙子里,留下一块湿印。我对司机说:“把他们带上。可能是阑尾炎!”
司机戴上手套,叹了口气:“上车吧!”上车后,老头把包袱放在一边,把病人的头抱在自己的大腿上,用手抚摸病人的脸。
“他是你什么人?”我问。
“不认识,”老头不慌不忙地说,“他说他是从甘肃过来买牲口的。”
司机猛回过头,深情地望了老头一眼。我觉得红鼻子老汉,也变得可爱了。
我们赶到滴水堡的时候,已经是九点钟了。一进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使人馋涎欲滴的煮羊肉的香味。我不自禁地咽了两口唾沫,大概很响,司机都笑了。此刻我才隐约地记起儿时爸爸的唠叨:“古尔邦节是宰牲节……是回民的年……有条件的人要宰牛、宰羊,施舍给穷人,叫散乜帖……”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学生,不愿听这套迷信、落后的东西。但爸爸不管你听不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你灌!
我拿出记者证和省委统战部的介绍信,向公社秘书说明了来意。他显得很为难,说按习惯,回民是不愿意照相的,这事还需要研究一下。
“这样吧,你们先去招待所住下。”他说,“完了我陪你去找一个朝过觐的丁阿訇,他叫丁哈吉。”
看来我事先的顾虑完全是有道理的,这号事,也只有听人家安排了。司机在擦车,我独个儿去招待所找住处。
招待所里,一个中等身材的服务员,穿一身笔挺的灰色涤卡制服,背朝外,正对着一面花花绿绿的镜子,专心致志地梳头。我叫了几声同志!他像根本没有听见,不理不睬,头歪过来扭过去地自我欣赏着,使劲地用手把后脑门勺上翘起的一撮头发压下去,但这撮头发好像故意与他作对,怎么也压不平,他把手伸进嘴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按到那撮头发上,慢慢转过身来。他上下打量着我,冷冷地问:“干什么?”
“登记房间。”我回答。
“客满。”他指着小黑板。
“那怎么办?”
“我咋知道你该怎么办?”他说完把梳子撂到桌上。
“公社秘书让我来的。”我无可奈何地说。
“我管他秘书不秘书,皇帝老子来也没用。”
他悠然地坐在凳子上,大腿压着二腿抖起来,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我受不了,掉头就走。
司机知道我碰了钉子,拍拍我的肩膀:“看我的。”他戴上手套和墨镜,打开车门,做了一个演员谢幕的姿势:“请上车!”我摸不着头脑,由他摆弄。
本来就新新的北京吉普,加上他刚擦过,在太阳下油光锃亮。车子一发动就到了招待所。我要下车,司机叫我别动。他点上烟,叼在嘴里,使劲地按喇叭。
真见效,小伙子出来了。司机向他招手,示意他过来。他顺从地过来了。司机磕掉烟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
“给我们安排一个最高级的房间。”
“包房吗?”
“嗯!”司机装得不屑一顾的样子。
等小伙子开门的时候,司机狠狠地捶了我一拳,鬼祟地微笑着。
“这是我们招待所最高级的房间,专门给首长们留的。”我们进屋后,小伙子一边倒水一边说,“前天专区领导来,就睡在这。老汉好得很,没一点架子。能抽烟,一阵工夫,我给他点了三次烟,他还给我一支。”
一会儿,他又打来洗脸水,殷勤地对我说:“山区风沙大,洗一洗舒服!”他又怕得罪了司机,“洗完我再去打。”我没有理睬他。司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呼呼啦啦洗了个痛快。
“你们认识马文福吗?”服务员忽然问道。
“……”我们感到莫名其妙,我望着司机,司机也望着我。
“他是我叔叔,在地委当部长。我们县上第一把手还是他培养起来的!”
我开始收拾东西,一边擦相机,一边装胶卷。
“我叔叔家也有个照相机。盒子上还有个小鸟在飞,照得可清楚了。”他随手从一个塑料折叠钱包里,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个姑娘,长得一般,涂抹得大红大绿。
“您看漂亮吗?”小伙子问我。
“给我看!”司机抢过去,仔细地欣赏着,时近时远,赞叹不已:“不错。长得不错,照得也不错。这是谁?”
“我媳妇。”小伙子骄傲地说。
“小子真有福气!这么胖到哪里去找啊!”
小伙子趴在司机肩上,指着照片上的皮鞋:“这双皮鞋是上月我们结婚我叔叔送的,真正的北京货!”
“哎,去把你老婆叫来,请我们大记者给你们俩照一张登在报上。”司机又逗他。
“现在不行,她跟我妈吵架,又回娘家去了。”
“为啥吵?”
“我们要分家,我爹倒没啥,我妈哭着骂着不肯。不分还能成?光我们结婚,就花了九百多元,我爹攒了十多年。我还有两个弟弟,那不白白给他们受苦吗?我妈气得躺在炕上,我就叫我婆姨回娘家去了,我妈又骂我‘爹亲娘亲不如老婆亲’,我也不回去了。”
“有志气,小伙子!”司机把照片还给他,拍拍他的肩膀。
“哈哈哈……”司机笑着。
“嘿嘿嘿……”小伙子也笑着。
讨厌!
稍事休息后,我们又从招待所出来去找公社秘书。拍照的事未落实,加上又碰上个这样讨厌的服务员,我心里挺恼火的。秘书去清真寺找丁哈吉去了,我们干脆也径自去那里。
清真寺里人流如织,一个个见到我们都投以惊异的目光。只有井台上一个人,等我们走近,他撂下水桶向我扑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这不是红鼻子老汉吗!”我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此时此刻,一般暖流传遍全身。
“您贵姓?我总觉得您怎么看怎么像我们回民。”老汉歪着头,灰绿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非常自信地憨笑着。
我告诉他我姓马,是回民。
他像孩子般地叫起来,把我的手捏得生疼:“我们还是一家子哩!”我告诉了他我们的来意,他热情地带着我们去找丁哈吉。
哈吉正与公社秘书谈话,一见到我,脸上马上显得紧张起来。我热情地伸出手,他却一动也不动,弄得尴尬极了。
哈吉七十开外,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显得很威武。他双手抱于脐下,两个大拇指绕过来绕过去,足足有两分钟。秘书又给他作了解释,他才冷冷地说:“没什么好照的,我们回民不兴这个。”
哈吉转过身去。这时,红鼻子老汉一把抓住他,说:“他可是我们回民!”哈吉站住了,迅速地调转身来,诧异地问:“你也是穆斯林?”我什么也顾不得了,拼命地点头。哈吉突然跑过来抱住我的双肩,几乎把我搡倒。
哈吉热情地请我进屋,秘书有事先告辞,红鼻子老汉又去打水。屋里围满了人,按照回民的礼节,他们摆上了油香、馓子、盖碗茶,茶里放着糖、红枣、苹果干、核桃仁,一连给我冲了好几次,开口闭口“我们穆民”,我发现他们把对宗教的虔诚和对本民族的热爱搅和在一起,你想分也分不开,像一个人热爱自己的父母同时又热爱自己的故乡一样。他们问我“政策还变不变?”“照相干什么?”我都回答了。
哈吉关切地问:“您打算怎么照?”对他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我忍不住笑起来:“您不是说回民不兴照相吗?”哈吉狡黠地笑道:“穆民不是一般地反对照相,而是反对把相片供起来当偶像崇拜。不瞒您说,那些年被整怕了,有一回,马文庆的母亲死了,请我去站者那则,为此他们把我打得屎尿拉了一裤子。马文庆跪在地上哀求他们:‘你们抓我吧……你们打我吧……是我请他念的,你们放了他,我的好哥哥……’别人都说他是受蒙蔽的,没他的事,但他一直哭到大队部。到大队部别人又叫我念。胡达啊,吓死我了,还敢念吗,别人又要我跪下请罪,我说《古兰经》不许可这样做。他们就跟疯了一样骂我是‘现行反革命’,一绳把我吊到房梁上。开始我觉得身子很重,我默默地喊胡达……慢慢的身子就轻了。”哈吉舒了一口气,又说:“那晚多亏马文庆把我背回家,帮我洗换干净天就亮了。三天后,他又偷偷背来一袋土豆,我说不要。他说:‘要不要在你,我可是散了的!’不怕您笑话,那时每人每月二十斤带壳的红高粱,一个土豆也是宝啊!总算熬过来了。马文庆真是个好穆民!”
“马文庆是谁?还活着吗?”我问。
“帮寺师傅打水的老汉,你们不是很熟吗?”
我“啊”了一声,明白了:红鼻子叫马文庆!我顺嘴称赞道:“真好。”
给我倒茶的老汉拉着我的衣袖:“您可不知道,这才是个奇人哩!土改那会儿定成分,他本来是个贫农,但说啥他都不要,非要当中农。工作队问他啥道理?他说他要是当贫农,那就是穷人,谁还愿意给他做媳妇呢……”哈吉见他说离了题,赶紧问我照相的事。
我先请哈吉给我介绍古尔邦节的来历。他说古尔邦节是为了纪念伊布拉欣圣人。他平时爱做好事,经常散乜帖,接济穷人,但没有儿子。有人说他并非真心。说他那样做是因为他有钱有财。他于是向胡达祈祷说:如果胡大给他一个儿子,他将毫不可惜地把儿子宰了奉献给胡达,以表示自己的真诚。后来他妻子果然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夫妇俩非常疼爱他。他长大以后,圣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把刀磨快了真宰自己的儿子,可是怎么也宰不动……胡达给他牛、羊,叫他用牛、羊代替。后人在古尔邦节宰牲是胡达赦免人在顿亚的罪过,净化自己的灵魂。他还讲了古尔邦节的仪式。我思考了一下,决定拍礼拜、讲卧尔兹、穆民在家吃油香和宰牲等几个镜头。
哈吉仰头望着顶棚,显示出为难的表情。我问:“怎么样?”哈吉尴尬地说:“其他的好办,只是宰牲比较难!”其余的人也异口同声地说:“是呀,该宰的昨天都宰了。”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红鼻子老汉马文庆进来了,走到我跟前,问:“咋回事?”哈吉说明了难处,我求救似的盯着他灰绿的眼睛,希望见到早上他在沙坡上那种兴奋的闪光!
半天,他掏出他的小梳子,梳起他的胡子来,随后他笑了,是那种憨憨地笑,那种给人安慰和希望的笑。他说:“我到食堂去看看,他们每天都是宰羊的!”有人说:“今天放假!”他说他去找!
二十分钟之后,他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进门就说:“行,等礼完拜,我去帮忙宰!”我站起来,高兴极了,抓住他粗大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礼拜结束后,人们互相祝贺,用宗教语言问好;邀请亲戚、朋友到各自家里去做客。马文庆被不少人拉扯着。
在清真寺门口围着一堆人。马文庆挤进去。原来坐着一个六十开外的瞎子,脸朝天,双手捧着帽子,嘴里不停地在喊:“讨个古尔邦节乜帖,讨个古尔邦节乜帖……”马文庆躬下身对瞎子说:“您好呀,老哥!”瞎子好像听出了他是谁:“托胡达的福。您好吗?”马文庆说:“我们都一样。”
马文庆把手伸进皮袄里,摸了半天,我以为他又在找梳子,结果摸出五角钱来,放在瞎子的帽里。停了会,他又从包袱里取出两个油香递给瞎子。
显然,这是一个不幸者。是胡达在考验他呢,还是在考验他周围的人呢?不得而知。这时不少人三分、五分、五角,甚至还有一元的陆续撂到帽子里。我冲动了几次,仍不好意思。瞎子又在不停地喊:“祈求胡达襄助你们吉庆,求胡达襄助你们吉庆……”
我想:这不就是要饭行乞吗?然而并不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反而使人觉得热热乎乎的!这是什么道理?
姑娘们、孩子们都穿得花花绿绿,整整齐齐,焕然一新。为了今天的节日,人们准备了很久,盼望了很久,是可以想象的。跟汉族过年一样啊!
在公社食堂的后院,圈着十多只羊。我们挑了一只比较肥大的黑山羯羊。马文庆敏捷地抓到一只后腿,羊跳了一下,失去了平衡,被他拽到准备宰的地方。
我把相机挂在脖子上,找好角度——侧逆光,调好光圈、速度,色彩效果我也很满意。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马文庆弯下腰,把羊紧靠自己的膝头,用手分别抓住靠里的前后腿,借助后退的劲,手一提,胳膊肘一压,羊就倒下了。一个人帮他把羊捆好。马文庆又把羊调了方向。我叫他别动,他说不行,非要朝西方。我又赶紧找位置,等我准备好,马文庆左腿脆在羊身上,右腿岔开,左手抓住羊耳朵,把羊腿子搁在两个小瓦盆上。阿訇看了一眼刀刃,便念起经来。我一直盯着取景框,就在阿訇刀下去回上来的时候,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啊!太感谢马文庆了。
回到招待所,我躺在床上,马文庆老汉的形象一直盘踞在脑海里,迷迷糊糊睡着了。看见他远远地从山梁上下来,银须飘飘,神采奕奕,笑呵呵地向我招手……
笃笃……隔壁一阵敲门声搅醒了我,“嘎西,嗄西……”好像在叫谁。
我开门出去,愣住了:马文庆,是他?我迎上去拉他进我屋里,他却推开说:“我找儿子呢?”
“他在这里干什么?”
“服务员!就住这。”
门开了,老汉还憨憨地笑着,他儿子却怒气冲冲地说:“你来干什么?”老汉说:“古尔邦节,我来礼拜。”老汉打量他一眼又说:“你没去清真寺?”“我还吃饱了撑得慌哩!”
老汉在床上坐下,把包袱放在桌子上,取出油香和羊肉,对儿子说:“好久没回去,我心里想得慌。哎,你妈又病了,叫你给五块钱替她买点药。”
儿子说:“高价油香我吃不起!”我没听懂。老汉好像也懵了,嘴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儿子却气势汹汹地把油香往爸爸手里一塞:“你拿回去,我没钱吃。”
“你不是刚发饷吗?”。
“四十多块钱,不吃饭了?”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厉声地说:“你太不像话了……一点道德都没有……不养父母要追究法律责任,要判刑的……”我语无伦次地说。老汉听到“判刑”二字,震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说:“算了,算了。”
他显得无地自容的样子,两手哆嗦着,把油香放在桌子上,拿起包袱往外走,嘴里喊着:“胡达啊!”
儿子使劲地扫床。我又气又难过,跟着老汉走出来。我想安慰他几句,又找不到适当的话。我突然灵机一动,把口袋里仅有的五块钱掏给他。他痛苦地握着手,坚决不要,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知道,他的痛苦不是这五元钱能安慰的!我跟着他默默地走着。在离招待所二百米的地方,老汉站住了,他激动地说:“同志,您别笑话。孩子本来好着哩,前几年不知咋的变了。”停一会,又说:“将来下多灾海怎么办啊!”
老汉向我凄然地一笑,点点头,算是告别。我望着他迟疑着走远的背影,感慨万千,我突然想到,可以请司机送他一程,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