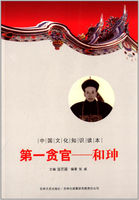于是,以后的每个星期天,凯特都会去看望露西太太。星期天一大早,露西太太便会起床忙碌,为凯特准备很多好吃的,直到凯特晚上走的时候,露西太太还要站在门口默默地送凯特一程。
凯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只是上天没有给他机会: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足够的创业基金,让他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如果露西太太能够早点将她的财产交给他,凯特便能够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并且能够让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但协议上规定的是等露西太太过世后,那些财产才属于凯特。现在提出来,他还是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凯特唯一的希望就是露西太太快点儿去世。
可是,一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露西太太不但没有衰老的迹象,反而越活越年轻,每天都精神抖擞地去晨练,或者去后院摆弄花草,虽然其间她因为肾病发作进过几次医院,但都没什么大碍,很快就病好出院了。这让凯特很失落。
凯特的公司还是开起来了,不大,将他自己算进去才5个员工。凯特第一次跟露西太太谈起了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当谈到自己为了筹集办公司的资金向银行贷了款时,露西太太没有主动提出资助凯特的事业,而是转着弯将话题绕到了她养在后院的花草上。露西太太说,她的花草长势很好,一定要带凯特去看看。凯特去看了,那些花草确实长势喜人,只是凯特却高兴不起来。
又是半年过去了。凯特确实是个干大事的人,这从他的公司发展情况便可以看出来。由于对市场把握得准,凯特的公司很快便盈利了。凯特的员工也由原来的5人,变成了10人。这天一大早,凯特接到了露西太太的电话。露西太太让他去她那里一趟,口气颇为严肃。又不是星期天,她怎么会突然让自己过去呢?莫非她的身体不行了,有后事要交代?凯特喜出望外,如果这时候将她的全部资产接过来,投入到公司的发展中,那凯特的公司将有可能得到迅速扩展的机会。
等凯特赶到露西太太的家里时,凯特发现露西太太的身体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糟糕,在满屋温馨的红色烛光里,反而显得精神饱满。这是怎么回事呢,凯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露西太太笑吟吟地望着凯特,深情地说:“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是一首生日快乐歌响起,露西太太从柜子里端出来一个大蛋糕。对,今天是凯特22岁的生日。22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给自己买过生日蛋糕,没有一个人对凯特说过祝他生日快乐的话。凯特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凯特再也忍不住地抱紧了露西太太,喉咙哽咽地喊了一声:“妈妈。”22年来,凯特突然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关爱和美好。有家的感觉真好啊,为什么自己以前就没有觉察到呢?望着露西太太一脸幸福的泪水,凯特有点恨自己,感到自己真的是太自私了。
由于惦记着这个“家”,还有家里的“妈妈”,凯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露西太太。凯特竟然习惯了吃露西太太做的饭菜,习惯了让露西太太给自己洗衣服,还习惯了他每次出门时,露西太太站在门口静静的凝视。就在凯特几乎忘记了露西太太身后的财产有一天会属于自己时,他突然接到了医院的通知。
此时露西太太已经昏迷不醒,医生说如果在一个星期之内还找不到一个适合露西太太的肾,就只有给她准备后事了。凯特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来救“妈妈”,他不能让自己刚刚拥有的家就这样因为“妈妈”的离去而破碎。凯特求医生检查一下自己的肾是否合适,他愿意捐出自己的一个肾来换回露西太太的生命。真是无巧不成书,凯特的肾还真的与露西太太的吻合。露西太太得救了。
露西太太的律师却跪在凯特的面前不肯起来。律师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啊,可是我却对不起你。”凯特在惊愕中听完了律师的叙述。原来律师是露西太太的弟弟,他为了给露西太太治病,已经花尽了她的财产,就连那栋别墅也抵押给了银行。也就是说,露西太太跟凯特签的那份协议是假的,露西太太的弟弟之所以要欺骗凯特,主要是因为露西太太认准了凯特是她的儿子,于是他便想让凯特以露西太太的儿子的身份,来帮助她治病,这样露西太太的病可能会好得快些……
最后,露西太太的弟弟说:“我的姐姐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她现在是孤身一人,已无能力偿还她的治病欠款,我愿意承担她的所有债务。你想要多少赔偿金我都愿意给,我这辈子还不清还有我的儿子、孙子,只求你开口说句话……”
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的凯特,终于开口说话了,凯特的话令露西太太的弟弟失声痛哭:“老人家的欠款还是由我来偿还吧。至于那栋别墅,我愿意从公司里支付每月的按揭款,谁让我是她的儿子,她是我的妈妈呢?金钱,我还可以赚回来,可是母爱却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露西太太跟凯特一起出的院,她一出院便迫不及待地要将那栋别墅的产权转到凯特的名下。凯特很开心地答应了,并同意马上搬进别墅跟露西太太朝夕相处。只有露西太太一个人不知道,那栋别墅其实还需要凯特用20年的时间来按揭。
原谅我曾经不懂你的爱
我和妈妈是相克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太像了。我几乎遗传了妈妈的所有:她的长相,她丰富的情感,她的敏感,她年轻时的浪漫,以及她的好胜、死要面子,面对一切带按钮的东西时的无所适从,她的没有方向感和害怕过马路。
我上小学前曾经是孩子王,手下有二三十号孩子。我野性、霸气、极有号召力。每天,我领着学校家属区的一群小孩子上山爬树下河捉鱼,我安排着他们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我6岁时,竟然说服了比我大三四岁的一批孩子在我的带领下,夜晚去爬一家军工企业几十米高的贮油罐。我们沿着窄窄的小铁梯往上爬,横七竖八地躺在弧形的油罐顶,望着月亮。我记得一个大孩子说了句让我费解的话:“面对天空,我们是多么渺小啊。”回来的路上,我对这次杰作无比得意。进了家门,等待我的却是妈妈的皮带。她让我脱了裤子趴在床上,我还能记得皮带抽在肉上的质感和声音,我哭得死去活来。长大后妈妈跟我说,那次打完我,她一个人不停地哭,她不知道该拿调皮的我怎么办。因为担心下一次我又有什么杰作,我6岁时就被妈妈送进了学校,告别了人生最快乐的6年。这次的皮带非常有效,我突然变了个人,成了个乖顺的孩子,服从、听话。
我开始努力学习,一次一次地考第一,做妈妈眼中听话的孩子,让她满意。我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厌倦语文,讨厌阅读理解,总答不对题目;讨厌三段式的议论文,因为我总是没有观点。那次全年级作文比赛,我竟然连入赛的资格都没有。那个下午,夕阳透过小窗照在我吃了一半的饭碗上,妈妈不许我吃饭,她坐在床上骂我,声泪俱下。做语文老师的她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她摔筷子,打在碗上,几粒米跟着一跳一跳,让我心惊胆战。“从今天开始,”妈妈总结发言,“你必须每天写一篇日记给我看,我就不相信你的作文上不去!”当天晚上,我开始写我人生的第一篇日记《台灯》——“我念书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亮了,开心地看着我;我不看书不努力的时候,你就那样忧郁地黑在那里。”从此我坚持写日记,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大本,虽然再也不用妈妈审查。
我17岁以前的人生都是由妈妈安排的。她在家中说一不二,她决定一切、安排一切。服从者就是我和老实的爸爸。桀骜不驯的哥哥经常在妈妈的控制之外,妈妈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个现实。
每天早上,妈妈总是起得最早。她外出走一圈,亲自感受一下当天的温度,回来后为我们准备好当天穿的衣服。初中时,我拒绝在冬天穿棉裤,因为这让我完全没有了线条。那个早上,妈妈大喊大叫地和我吵架,她以她的感受来揣度别人,她认为今天已经冷到要穿棉裤的程度。那场争吵非常恐怖,整个楼道都可以听得到当老师的妈妈高八度的声音,虽然我决定反抗到底,但毕竟功力不够,事件最终以我穿着臃肿的棉裤去上课收场。
除了决定实体,妈妈还要安排我的精神世界。她为我仔细筛选着报纸杂志,每年都会订很多。尽管工资不高,她还是为我大量购买书籍。
妈妈结婚晚,生我时已经31岁了。我最叛逆的青春期刚好和妈妈的更年期撞在一起。那时我很不听话,经常反抗妈妈的安排,我们冲突不断。妈妈大喊大叫,我叫得比她更凶。于是妈妈就流泪,搬出爸爸来训我。但爸爸经常对妈妈的无理取闹表示沉默。最后妈妈总是从柜中拿出一只绿色的包袱皮,边哭边收拾着东西,威胁说这个家有她没我,有我没她,她要回河南娘家去。可这个包袱皮总是包了拆拆了包,总也收拾不完。我和妈妈的冲突总是如此剧烈,我非常痛苦,我经常站在五楼的阳台设想着跳下去之后的种种景象,我想象着妈妈将围着我僵硬的身体泪流满面,设想中她的心碎让我得到了内心的满足。于是每次和妈妈争吵失败后我都会进行这样的想象,我设想跳过无数次楼,每次跳下去后妈妈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她一次比一次痛苦。
我1989年报考了复旦大学,这也是妈妈决定的。因为那些日子她总听学校一个上海老师说复旦是多么一流,而她的女儿一定要上一流的大学。虽然我的分数完全够了,但没想到因为当年那特殊的事件,复旦在我们那个省突然一个也不招了,而我也没有机会第二次填报志愿,就这么稀里糊涂被打发到第二志愿——一所不出名的外语学院。中学六年,我的成绩如此之好,每个人都认为我会非北大复旦不去,包括妈妈也这么有信心。但命运就是这样残酷地打击了妈妈。我复旦梦的破灭被妈妈念唠了无数年,甚至到我工作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她还念念不忘,我才明白了这件事情对妈妈打击的程度。
据说妈妈中学时的成绩相当好,她梦想上的大学就是我后来念书的学校。没想到因为我那年轻时据说生活花哨的姥爷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几年的军医,这个历史污点让成绩完全够了的妈妈因“出身不好”而白白断送了上大学的机会。有时,历史会惊人地相似。妈妈太好强、太要面子,我想过很多次,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对她的打击,造成了妈妈日后的性格:暴躁易怒,紧张焦虑,没有安全感,对未来和对周围的人没有信心。我不知道答案。
妈妈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于是她把我设想成另一个她,精心地打磨我、设计我,把她没有实现的理想安在我身上,我是她全部的事业。她对我的要求是上完大学继续读书一直读到博士。但她没想到我从大二就开始谈恋爱。仿佛是为了反抗她多年的安排,我在大学时有意过着她无法控制的生活,任性而自由。在妈妈的要求下,我考过研究生,但成绩差了一点点,从此结束了妈妈心中的博士梦。
我毕业后想离妈妈越远越好,到一个她终于控制不了我的地方。我一口气跑到了海南,后来又跑到了深圳。离妈妈远了,需要自己过日子的时候才发现从不让我做家务的妈妈多么温暖地呵护了我的人生,同时也让我除了读书以外什么也不会,不会做家务,不会和人相处。面对社会,我手足无措,像个弱智。
离妈妈远了,我们没有机会激烈地冲突了,我开始想到妈妈种种的好,我每周给妈妈打电话,长长地聊天。妈妈苍老了,她没有了以前的强势,面对经常不能发到位的退休工资,她总感到面对社会的无助。她总胡思乱想自己老年的生活,是到哥哥那里住还是到我这住,她反复同爸爸讨论这个问题,直到爸爸受不了。
去年过年我把爸爸妈妈接到深圳来住。我和妈妈一起坐电梯下楼,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几乎比妈妈高出一个头,我突然看到妈妈头顶几乎掉光的头发,她满脸的皱纹,她混浊的眼神。她很无助,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她的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很不自然。她像个孩子似的,我说什么她都点头附和我,她笑时甚至有些讨好我。我用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胖胖的老太太很久,很想放声大哭:就是眼前这个老太太决定了我曾经的人生,那时她无所不在,她控制着我,那样强大,不可战胜。而现在她老了,面对一个她越来越不懂的社会,她变得像个小孩子,希望得到我的呵护。过马路时她像只刚出生的小鸟,惊恐地缩着脖子,紧张地左看右看,身体僵硬,她总希望我拉着她的手。
妈妈老了,真的老了,随着岁月一同带去的,除了她的年龄,还有她当年的力量和强大。现在,她只是个需要我哄,需要我照顾的老太太,一个会把一句话说上无数遍的总希望得到别人注意的老太太。
我想搂着妈妈大哭一场,告诉她:原谅我,妈妈,那些年,我曾经恨过你。可现在,我只想照顾你,温柔地陪着你,我希望你在我这里舒服、安全、踏实,我希望你终于不再担心什么,终于停止焦虑。
“狠心”的母亲
9岁那年,他开始逃学。
一天中午,先生终于气愤难忍,把他逃学一事告诉了他的母亲。
下午,他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赶回家来。一切都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在他眼里母亲依然是一副和蔼慈祥的样子。“孩子,今天学堂里的功课你能听懂吗?”“能。”他随口答道,顿了顿,又眉飞色舞地补充道,“我们今天学了《论语》,那里面有好多的‘之’和‘乎’……”母亲没再说什么。他知道母亲从没上过学,是不会问出什么高深的问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