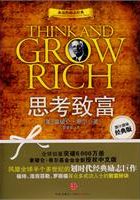“甚至连猫也要埋掉它的粪便;而我却把我的大便带在身上。”从医院回到家里,她想,几个星期来,这话已大声地说了多少次。她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决定笑起来——他们是不是会到笑起来的地步。发病前他们唯一一次提到这种机械的存在是在几年以前,当时——在愉悦的周末早晨的床上,他们像往常一样交换着报纸——她在读一篇有关失业和少年娼妓的文章,并向他发表了看法,我的上帝,人们给那个女孩提供的福利是让她在一个工厂干活,那工厂专为那些不得不切除了胃的人们生产塑料袋之类的东西——难怪她要跑到大街上去,可怜的小家伙……她清楚地记得那个早晨,那张报纸。他们的谈话越来越频繁地回到这上面。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到工业化造成的悲惨状况;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认为工业化会带来人的隔离,只有在生产方式属工人所有后才会消失,可是,苏联和中国的工厂不是也像西方的工厂一样悲惨吗?她记得她曾提醒他(他们一道访问过北京),中国工人至少每天必须要做两次十分钟的工间操——可他说,你愿意用这个去换吃茶点和抽一支香烟的休息时间吗?
在知道那个十六岁的未来的娼妓之前,他们两个在星期日早晨的床上大笑,那些在装配线上传送的塑料玩意离他们很远,就像任何工厂工人的生活离他们很远一样。
现在,这个机械就附在她自己身上。它从她身上,从掩盖在衣服下面的小创口冒出来。她已从他们共同的卧室搬出去,他很理解,一句话也没说。她一直在医院里学习怎样摆弄那玩意儿,它不同于自然机能的不可告人,而是令人讨厌的不可告人,因为自然机能是——过去一直是——他们俩都使用的。她孤零零地跟她的活物在一起。
医生说那玩意儿到时候就会被取走的——六个星期。第一个医生预言;不超过三个月,第二个医生告诉她,他们本应合作编造他们的童话。他们说(六个星期或三个月后)她体内的一切都会重新连接起来。一直敞开的伤口会缝合。她会重新变得完整,恢复健康,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她将回到音乐学校去教书。她现在就可以回去——为什么不?——如果她想要回去的话,只要她不使自己疲劳。可是她不想回去,身上带着这玩意儿。她不得不听更多的故事——从令人鼓舞的朋友那里——关于别人对付得是如何好,过的是如何正常的生活。甚至一个英国王室成员也这样说。她要他们别再胡诌这种童话,她说,可是对我来说,这只有6个星期(或者3个月),我用不着去对付。他替她买了两件漂亮的土耳其长衫,是他自己选的,完全适合她,恰恰是她喜欢的颜色和款式——她在高兴中忘了(过后她知道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她将穿上这衣服来遮住那玩意儿。当朋友们来看他们时,她有时穿上这件,有时穿上那件,她的这身装束获得了赞美,他们说她一定是在装病,她看上去妙极了。他向他们证实说,她正在好转。
他们交谈,不久以前,有一回,在此之前他们交谈,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难舍难分的生活中——可那些话是多么的大众化。真的,那时候!一个幼稚的协议,志同道合的情谊,就像那个无穷无尽不必回答的问题一样,你爱我吗,你会永远爱我吗?要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得了不治之症,我们都不会让对方受苦,好吗?然而,当这种事发生时——好了,这种事绝不会发生。这个愚蠢的、戏剧性的、清晰的抽象概念不会变成事实。谁能说“不治”是什么意思?谁能肯定遭受磨难就是生命的终点,而不是延长生命,以便历经磨难而活下去?有个人二十年前切除了乳房,但至今仍然每个星期去参加赛跑。还有个人失去了前列腺,但在任何一个鸡尾酒会上,都能看见他带着他的第三个妻子,吧嗒着加汽水的杜松子酒。
可是,就在她去医院做探查手术前,她找了个时间和地点以便再证实一下。“要是结果不好,要是变得很不好……任何时候,你答应我要帮助我摆脱病魔。我会为你做这种事的。”他无法说话。她跟他躺在黑暗中;他拼命点头,以致这协议被他的下巴按进了她的肩部。骨头弄痛了她。然后他跟她做爱,在协议中进入她的身躯。
手术之后,她发现那根管子,那个机械从她身上牵出。他们没有再次交谈;只谈愉快的事,只谈病愈的事。那玩意儿——把它导引出来的伤口不像别的伤口,不允许缝上,就像他或她的生活中被隐瞒了的一次艳遇,它们的重量会将他们的外皮撕破,如果承认了的话。每次他们的目光相遇,他们便立刻朝对方微笑。可这毕竟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就得有一个童话。在每一天,每一个他们为下星期、下个月、下一年制定的计划里,每一个谁也不相信的继续过日常生活的假设里,这童话被说了一遍又一遍,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没有一句话不是谎言。杂货商来了吗?又有一次抢劫啦,你在椅子里舒服吗?他们说选举在春天开始啦,我们需要新酒杯啦,我应当写信啦,定购咖啡和火柴啦,中东的又一场危机啦。把窗帘拉上,阳光照到你眼睛啦。星期四我必须理发啦。要是现在她抓住他的手,那只是处在不朽的谎言中。因此,肉体对他们来说不再是真实的了。
剩下只有一件事,正是由于它的性质,才不可能成为谎言。只有一个地方爱情可以幸存下去:虽然生命遭到背叛,但那协议并不是跟生命有关的。
那个星期四下午他开车送她去美容店,当他来接她时,他对她说,她看上去真漂亮。她窘迫地表示感谢,就像一个初次受到赞美的姑娘一样。这时她被一种对他的极度信任——除了多少个月来的恐惧和厌恶而外,第一个强烈的情绪——所压倒。那天夜里,一个人呆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数出储备的药片,在用白开水把它们冲下去之前,把她给他的纸条压在用作镇纸的打火机下面。“遵守你的诺言,别把我救活。”
自从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起,她就把这理解为一次长眠,就这么回事。自从她看见一只鸟,躺在篱笆下,被一根树枝拨弄,它的眼睛没有睁开的时候起,她就这样理解了。可是,一个人只有当他从睡眠中醒来时才能意识到睡眠,所以一个人永远不会意识到长眠——她对死一点也不害怕,可现在她却对自己正从死亡中醒来,从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死亡的状态中回来的感觉感到恐惧。她的跟睑因光线照射而成了粉红色的遮帘。她打开遮帘,目光落在一所医院光滑的墙壁上。手中握着一只手——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