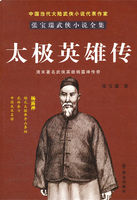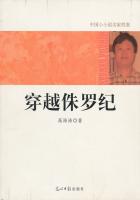景恺睡下,再次来到那被上帝主宰的世界,这地方依旧朦胧。他一人独立一片光际中,像没有时间的约束。耳畔响起小提琴凄厉的唯美,走在这无垠的通衢上,瞳孔中充满着玄之又玄的妙惑。遽然,一个佝着腰的老人像老式电影一般印在景恺的前方。“奶奶!”他轻声叫了起来,刚伸出手去触摸那景象,倏忽变成了雪花,她惆着脸看着景恺,景恺再一次把手缓悠递向了她。蓦地,无穷的白色被涂成了云墨的一角。景恺环视着周围,一道斑白的亮光夺目而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向他徐徐走来。“妈!”“顾景恺!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她的声音在这纯白黑间的世界不停回荡。接着,顾父踏着那软皮跟鞋走了出来,他狰狞的面孔逼得景恺惊恐万分,顿时顾父的头像被不间断的语音贴向四壁:“顾景恺,顾景恺、顾景恺!”……
“阿恺,阿恺!”
“呃!怎么了!”
“打铃了,你不下去吗?”景恺梦呓全醒,像丈三的头脑,头脑都不摸,直让枕头作后补,对智锋说:“你们去吧!今天下午我就呆在这睡觉了。”
“那你睡吧!我们去打球了。”
“嗯。”
大家都走了,宿舍里空荡荡地只剩下景恺和他的回忆在原地徘徊。不知不觉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与景恺的右手心两点一心串成一道孤独。景恺感觉自己的悲吟像食进他人所做的难咽菜肴,其味只在自己心里知道,嘴上不说。景恺打开音乐,倾听Jay的《止战之殇》,任这歌的韵味在没有硝烟的介质中传颂。景恺无力诉说也无人诉说。他倚在墙上,又折射出比阳光更刺眼的——孤独。人摔倒了一万次,总有一次会站起来。这句话对景恺来说是假话,他在无数挫败中寻找站起来的机会,可一站起来才发现地面尽是油,于是又坐下来。旁人就像体育老师,看他做“蹲下、起立”当然是站着观赏不腰疼。景恺的身体被折磨得炼出八块胸椎,学那机械不知疲倦地闷着胸口抽泣,呼吸,像是跑在八百米的赛道,难受只进不出。也许,对他来说,幸福是短暂的,时间是漫长的,幸福的时间是三长两短的。景恺一次性想起几十个邓小平,不为别的,就为这几十号人数起数落的经历能抚平自己的心理。他爬起身下了楼,经教官斥了一顿放出了牢笼。行尸走肉般在这路上摩着对地球的不满,阴沉的心情不随运动会的气氛同流合呼。景恺来到双杠旁,双手摇晃着勉强把自己撑离了地面,拨通了父亲的号码——
“喂,顾景恺!你这时候打来,不用上课?”景恺温和的打断让顾父无案可稽,顾父难得听到景恺如此女人味的语态,像在家门口看见奥巴马,惊讶地连自己的耳朵鼻子都不敢相信。便问:“那你没事打我电话干嘛?你不知道我很忙吗?你知道你这是在耽误我的时间,我的金钱!”
“是在和那个小情妇偷蜜吗?”景恺一针见血让电话那头的顾父如同在公厕遇见华盛顿,惊讶地连自己爷爷的爷爷都不敢相信。景恺怕父亲再惊讶下去的话,就可以去见他爷爷的爷爷了,说:“我都知道了,妈都告诉我了,你不用再隐瞒我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嘟嘟嘟……。”
“喂,Fuck,可恶!”父亲省钱儿子却不在乎。有其父必有其子,为何呢?因为其子有钱其父才有,其子无钱,那后一个“其”便无理可循,应夺为“有其父必有子”。景恺按下重拨继续骚扰他。
“您好,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
“该死,我就不信你一辈子都关机。”景恺从杆上狠跳下来,咬牙切齿把对这世界的怨恨狠踩了下去。
晚间,景恺的情绪严重影响到学习效率,一个晚自习都望着金慧欣痴想。金慧欣的背影似乎有朱自清父亲的借鉴,景恺看着她,亲切感倍增,却又做了那进餐之人,胃酸抵制地直在心中哽咽。Easy是个大嘴巴,告诉他只比狗仔队的时效慢上一点,一天就这么迷糊地过了。
次日,景恺睁眼后的第一件事是呼吸,第二件是呼吸空气,第三件事是呼吸新鲜空气。如此有条不紊地借中华文化罗列下去,景恺的惰性便有理可趁懒床不起。只惜中华文化发展至今已被教育充冒得所剩无几,铃声一响,不得不起。景恺牙都没刷,把昨天残余在口上的污气一齐留给父亲的通话上,他按下拨号键便听得移动公司营业小姐敬业的声音:“您好,您所拨打的用户……。”景恺挂下电话,看来昨日事应该昨日毕,昨日之气也该昨日气。今日之气还是今日息。景恺这时想起今天继续开运动会,哪管那教育,直接复兴中华古代文化埋头睡觉。
一上午景恺哪都没去,呆在宿舍不断消气,但听到的则是一遍又一遍的移动服务,只不过换女声不换女生。那移动公司小姐的口语气吞时空,其先还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华汉语,语出十七个字后时光穿梭回到现代。什么地不挑,选中广东,一口粤语翻译古代,倒不若说给古代人翻译。广东人不老实,偷工减料,省去一两字的读音后就匆忙奔赴伦敦。英国人慷慨大方,一句话下来,反送了十几个字母给中国。景恺听后为自己身为国人而不敢再骚扰女人,便开始对自己的处境犯愁,再过两天便是月底,他也不知父亲是否会汇钱抚养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又对月光族抱有向往,景恺不禁又叹人的生活要比利益实际得多,至少你会牵动手脚为它做,而利益则会使你牵动手脚为他人而做。景恺自我安慰好不被良心责得太深。
三天校运会时间就让景恺不停地谴责掉了。回到家后卡上余额只足半个月的生命维持,看来顾父真是气吞秤砣,且不止一个,多的足以铁化他的内心。可怜景恺半个月后真要学古人勤学时吃西北风。他看了看时间,七点一刻,按往前,这时候总该学习,而他的行动与思想反目成仇,各执一边。此二者似有商品与消费的模样,商品陈设却不消费,光看是不能享受物质的。他光想也只是脑中的一个摆设罢了,它永远也僭越不了行动的范畴。他发过信息问她吃饭否,她未回应,估计正在进行时。景恺没了享受,上肢百无聊赖地点着鼠标在桌面上不停地刷新。刷来刷去,桌面是干净了,内心却是一片混浊。气这虚似世界只有物质作用,精神略无一用。
“嘀嘀嘀……。”景恺猜是慧欣,迫不及待地想与她倾谈,打开消息:“景恺,你在吗?”是杨雨馨,景恺的希望让他的猜测坠成了失望,起先还在天上飞着,滑一足就在地面躺着了。却又不好认命,道:“在的!”
“你那天看了我的比赛吗?”景恺小惊一度,校运会期间一个劲地忙着给移动公司搞录音投资却忘了看她的比赛。歉意十足,恨学校的摄影仪器都用来捕捉早恋人士的旖旎风光,否则自己倒能看录像补回过失,道:“对不起!我忘记了,那天也正好有事!”
“有什么事比看我的比赛还重要?难不成雪萍吃醋不准你看吗?”景恺一听这话不觉心凉,人与人比会比死其中一个人,男人与男人比会比死其中一个男人,女人与女人比则会比死另一个男人。原因极简单,人与人比无非是比钱的利益,其多受个重伤;男人与男人比则是比女人的利益,其多也只弄个半残;女人不同,比的是自己的利益,会让男人的心房变坟场。景恺离那坟墓只差雨馨再掘一地,但他不甘心自己是为王雪萍而死,打上:“不要再提她了,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杨雨馨自责不已,疏于平时,用文言说就是人之常情,用理学讲就是惯性,用英语译便是usual。可见人性这东西就是各自的命根子,一次性可吃掉高考生三门主科的分数,只能怪教育愈加深入人心,且渗入人心。
“什么!你们分了!好好的怎么分了?”她的话对景恺虽没起到一言致命的效果,却让景恺给自己掘了一亩坟,他自惭道:“别提了,我不想那么啰嗦去重复那些往事。”
“好吧!尊重你,那是否跟不看我的比赛有关?”
“没有,不过原因我也不想说。”
“你心情不好吗?那你一个人静静吧!我不打扰你了。”景恺一感动,难得说出了自己的善性:“谢谢你。”
“不用谢,记得开心点后告诉我噢!”景恺二感动,善心大发:“愿你的善良能保佑你一生平安!”杨雨馨捧回一颗感恩的心:“呵呵!谢谢!”
她的再见在景恺心中很是稳重,把他当死人般深埋在了地下。
此时慧欣还未回复,景恺气急败坏又发了几条信息过去。这话倒像是迟到的扣篮,百扣百中。慧欣立即回复:“你在啊!我以为你挂着呢!”
“挂着会不理你吗?”
“会,你刚才就没有。”景恺看后感叹:现在的女生,不做女友时是外敌,做了女友是外宾。这关系好比中日友谊,甲午前一面,建国后又另一套,亲密度变了,内情未变。景恺说细了是担忧国情,说白了是为了爱情,说得又细又白是女人。问她:“你这样说那我们像是一对情侣吗?连说话都带腼腆,陌生人?”景恺的话说得粗又黑,仅为反衬慧欣的白皙。
“不是啦!因为你是我的第一个那个,我真的有些开不了口。不要生气了,我向你道歉以后不这样了。”景恺灵机一动打上:“你唱《开不了口》我就原谅你!”
“呵呵!怎么唱啊!你又听不到。”景恺这时才想起挖了半天的坟地却忘了买棺材,主事未办,杂事倒做掉不少。只好倒回去要棺材:“欣,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呵,怎么改名了,你说吧!我听着。”景恺人死心未死,顽强地做升降运动,踌躇不已。突然一刻停了,心死了,自然心事也不成事了,打上:“我妈昨天来信息,因为我爸有了外遇,他俩离婚了。我妈到别处生活,我之前打过一个电话算是批评他,这两天他一直没汇生活费给我,我担心我的生活过不长久了,马上要独立生活了。”与往常不同,景恺此次的痛楚仿佛一个人丢了一百元,他老婆捡到两百元,毫无忧患之意。
金慧欣自为淑女,想说的话又让她做妇女,冗长得连她自己都嫌啰嗦。只怪中国汉语流传至今,只与女人同一观念,拖泥带水。不像哑人,本自没有女人啰嗦的天性,所以他们出生前被女人尊重,出生后被男人尊重。再比如说聋子,与前之相反,他们一出生便被女人尊重,她们的啰嗦在他们身上得以发挥,且这女人与古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越老的女人越啰嗦,同理越老的女人越尊重这类残疾。世上多一些聋哑之人,原本的战火在家庭中就和平多了。景恺不是聋子,慧欣不是哑巴。金慧欣不禁想到自己才诗敏捷,又恨当代之人对中国古典文化漠不重视,不然以诗代话淑女便可稳当,无奈之下只好当回现代妇女,慢腾打上:“景,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你。我真的很难想像你是怎么走过这段路的。那样的坚持,那样的执着,要是我早就垮了。我不能做些什么,只希望你不要太难过,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你明天回你以前的家找一下你父亲吧!男子汉要敢于面对,无论怎样我都会为你祝福祈祷的。但愿你能快乐!”景恺的双眸为现代人难寻的一丝清纯而湿润。他想上帝并不是百无一用,至少派下一个天使为自己疗伤。景恺不负这恩惠,应承上帝一定会珍惜这份感情,道:“欣,谢谢你!明天就去找我爸,Iloveyouforever!”幸福产生的美感就像中国古代武侠人物的决斗,你给他一拳,他还你一脚,你给他单鞭,他送你双刀。直到双方中的一人倒下,这决斗也便结束。恺欣二人距生死离别还言之过早,并不担忧。慧欣被景恺宠诺一生,幸福加倍,言语数倍奉上:“景,Iloveyouonemillion。”
景恺眼前浮现她可爱的模样,像瑊珏般无瑕。令他唇唇欲动,有种想亲吻她的冲动。女人的吻要比男人的吻值钱得多,像女人卖身也要比男人赎身昂贵得多,因为好色一词从来只在男人身上体现,女性鲜有耳闻,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波及世界,世界也惧怕中国男性,于是世界人口偏袒男性,世界上男人总是多于女人,而女妓永远多于男妓。物以稀为贵,妓女多了,自然不是妓女的就少了,故她们的吻便值钱多了。窑姐当然不会这样想,她们认为女人卖吻是一种牺牲,卖身是一种精神,只有像她们这样长期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中才是资本。这情操还真是欲壑难填。绕了半天,想到的还是利益问题,这天下恐怕要唯利益不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