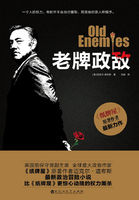副局长“红版图”有一大嗜好,喜欢惨无人道地蹂躏书画。我们科长的书画水平了得,于是他经常性地找我们科长“切磋”。
一天,他画了一幅“印象派”画,找科长“斧正”,科长外出,“红版图”有种“欲将心事付瑶琴,弦断有谁听”般的失落。正在这时,我一头闯进办公室。“红版图”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惊喜招呼我:“麻秆张’,你来得正好,据说你对书画艺术颇有研究,来,给咱看看。”
平时“红版图”见了我辈都是鼻孔朝天,何曾如此礼贤下士过?我被这巨大的幸福冲击得晕晕乎乎。今天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想不让我受宠若惊,难!
我战战兢兢接过副局长的画作,小心翼翼地铺开,认真欣赏,越欣赏,越感到心里没底,脑子愈发混沌。“红版图”的画,看起来满纸烟云,黑糊糊的一片,根本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我费了好大工夫,才发现画的中间有一个似人似兽的怪东西。我为自己的发现欣喜若狂,又为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忧心忡忡。好我的局长大人啊,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就明着来,何必这么难为我呢?
“红版图”悠闲自得地喝着茶,等着我的“高见”。长这么大还没有发表“高见”的机会,机会来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天生不是当领导的料,我真的太佩服那些领导了,他们有本事把一团漆黑说得天花乱坠。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不禁埋怨科长,你老人家有啥要紧的事儿非得现在办,害得我受这般洋罪!
“红版图”说:“哎,我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尤其是艺术品,视角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同。我很在乎你们这些年轻同志的看法哦。”
按照“龙从云,虎从风”的说法,我估摸着,副局座大人画作中间那条弯弯曲曲的东西应该是一条龙。我努力张开想象的翅膀说:“您的这幅大作大气磅礴,非我辈凡夫俗子所能领悟。在您的这幅画里,我似乎听见了风雷轰轰作响,您的这条龙吞云吐雾,气吞万里,气势非凡!”
“红版图”的笑容慢慢僵化了,悻悻地说:“你怎么欣赏的?哪有什么龙哦?我画的是松鹤延年,很传统的题材!”
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我大窘。嘴欠,没看出什么东西就不要说嘛,装什么大头蒜。话又说回来,能把松鹤画成龙的模样,也真够难为咱们这位副局座大人的。
正在这时,“红版图”的手机响了,把我从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我简直要对来电话的同志高呼万岁了。接罢电话,“红版图”说:“这幅画儿先放你这儿,等会儿我还回来,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天啊,还“切磋”,还要不要人活了!“红版图”前脚出门,我就准备来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小林就在这时一头闯了进来。
我十二万分火急把小林拉到桌前,请他欣赏副局座大人的画作。小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了许久,愤怒地说:“这是什么东西?竟然敢拿来污辱我的眼睛!”
当我告诉他这是一幅“松鹤延年图”的时候,小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这明明是乌云密布下的一条水沟嘛,怎么成了松鹤延年?咱们局座大人真幽默,简直就是幽默大师。我说,你甭管他是不是幽默大师,先帮我渡过这个难关,等会儿副局长大人还要来找我切磋呢。小林说:没问题,交给我了,看我怎么忽悠他!
“红版图”很快踱着方步进来,笑呵呵地说:“怎么样?看出点什么名堂没有?”
小林一脸严肃地说:“局座,不是我说您,画画儿嘛,对您来说不过是个业余爱好,您根本犯不着拿这幅画来蒙我们!”
“什么?你说什么!”“红版图”愤怒了,脸上“祖国山河一片红”。我心里替小林着急,怎么说话呐,还想不想进步了?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
小林两眼朝天,似笑非笑地说:“局座,甭以为就您满腹经纶,我们什么都不懂。书画研究我自然比不上您老人家,可是高低好坏还是能看出几分的。”
看得出,“红版图”在强压心中的愤怒,不怒而威地说:“什么意思?”
小林说:“局座,您甭装了,老实说,您的这幅画到底是哪里来的?”
“什么哪里来的!是我自己画的,墨迹还没干哪。”“红版图”耐心地说。
小林装模作样地又仔细看了一遍画作,他看一眼画,抬眼看一眼副局长,摇一摇头,点一点头,边看边叹息。他满腹狐疑地说:“打死我我也不信这是您才画的。依我看,这一定是您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国宝哎。局座,我虽然眼拙,也能看出,这恣肆汪溢,飘洒俊逸的画风,分明就是唐伯虎的真迹嘛!”
我晕了。好小子,真有你的,就凭这一点,你还能大大地进步!
“红版图”喜笑颜开:“小林哦,看不出,你对绘画还是蛮有研究的嘛。这回你可看走眼了,是我信手涂鸦,见笑了!”
小林万分惋惜地说:“大手笔啊,局座。不是我说您,您怎么就从政了呢?咱们国家并不缺少您这样一个官员,而缺少了您这样一个有天分、有深厚造诣的艺术家,这可是国家和人民的极大损失啊。”
“哈哈哈,过奖了,过奖了……”
两个人“切磋”已达到胶着黏合状态,大有惺惺惜惺惺,英雄相见恨晚的意思,我完全成了局外人,便悄悄关上门,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