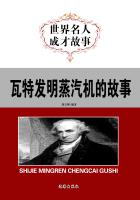“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天下已定,人心思定,再搅起叛乱就是不忠不孝了,三藩之乱尚且不能动了大清的根基,其他小股义民聚众滋事不过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曾静连连摇头,“先生此言欠佳,以我多年夜观星相推测,最近几年之内将会出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百年不遇奇观,这将预示新君下凡,好世道就要来临。而在新君降生之际,天下必然大乱,有识之士正好可以利用大乱之际揭竿而起,打起——”
曾静见左右无人,才小声说道:
“打起反清复明,驱逐鞑满的旗子,此旗一举那些暗中活动的反清义士必然云集响应,鹿死谁手还难说呢。当年三藩起兵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各自为政,缺少配合,才被清军分而瓦解。另一面也因为他们都是降将,出尔反尔失去民心,汉人不拥戴,满人叛之,当然必败无疑。”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急匆匆跑过来,瞥一眼胤禛,然后就给曾静收拾卦摊,边收拾边说道:
“师父,严先生回来了,让你回去呢!”
曾静马上面露喜色地问道:“是鸿逵吗?”
“除了他,还能有哪位严先生,他说把吕义士的《时文评选》也给你带来了呢?”
“太好了,我早就想看一看吕义士的《时文评选》了,如今可以如愿以偿了。张熙,快帮师父把东西收拾干净,我先行一步。”
曾静又向胤禛拱手说道:“这位官人,曾某失陪了,新来了一位要好的朋友等着我回去招待呢。”
曾静说完,转身兴致勃勃地走了,望着他的背影,胤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有心亮明身份擒住曾静,又怕自己身单力薄吃亏。转念一想,这曾静背后说不定有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呢,与其抓他一人打草惊蛇,还不如放长线钓大鱼呢。只要他们在大清的版图内,就是藏在天涯海角也不愁抓不住他们。
这时,张熙收拾好摊点就要走,胤禛急忙上前问道:
“薄潭先生匆匆离去,家中到底来了何人他这么心急,看神色像是远道而来的贵宾?”
张熙见这人一口道出师傅的号,又见他刚才同师傅谈得十分投机,估计是师傅的朋友,小声说道:
“从浙江石门来的严先生,严鸿逵。先生可能不了解严先生的大名,但他的老师你一定听说过,有‘东海夫子’之称的吕义士。”
“‘东海夫子’是谁?莫非是当朝什么大儒不成?”胤禛笑了笑说道。
张熙见胤禛真的不知道“东海夫子”是谁,于是卖弄说:
“‘东海夫子’就是浙江石门的吕留良,号晚村,人称晚村居士的吕义士,此人以学识气节享名,宁死不愿到清朝做官,吐血削发明志,最终出家为僧辞却地方官的举荐。”
胤禛经张熙这么一提示,想起了吕留良这个人来,他曾是朝中谈论的一个话题呢。据说此人诗文俱佳,就是科考不中,在万念俱灰之下隐迹山林。朝中也曾派人请他出山作事,但被拒绝了。皇阿玛十分生气呢,当时想派兵捉拿,但被大臣们劝阻。据说吕留良已死去多年,他的《时文评选》是怎样一本书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胤禛继续沿苏堤前行,边走边想着曾静的谈话和吕留良这个人,心里乱糟糟的,一点也理不出个头绪。湖光山色,碎波倩影再也引不起胤禛刚才的兴致,郁积在心头的却是一腔无端愁绪,何愁何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正当胤禛怅然欲归之时,旁边的一个亭子间传来少女酽酽的歌喉和铮铮琴音,弹唱的却是柳三变的那首千古名篇《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山献清嘉,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
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
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向凤池夸。
胤禛听罢暗想,短短一首词能把杭州城刻画得如此淋漓尽致,也实在是词坛圣手,有地理形势,有山水风光,也有繁华的市井街巷,民殷财阜,商繁市茂,官民同乐,确实是盛世气象,用这首词形象现在的杭州城应该是恰到好处。
若是在没有见到那算卦先生曾静前,胤禛听了这首词一定会喝起彩来。而此时此刻,他却提不起一点精神,对眼前的艳词丽曲也感到十分茫然。柳永一个沦落在勾栏瓦肆间的下层文人写这首词的用意何在?是应时应景应事即情而作,还是受人之所托故意写一些违心的文字?当时的杭州真的像词中所写的这样繁华吗?这繁华的背后是否存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慨叹呢?胤禛实在分不清繁荣与萧条,盛世与亡国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界限,更分不清颂歌与哀歌、挽歌之间的区别。有时,看似歌颂其实是讽刺,有时,表面上是拥护而骨子里却是反叛。胤禛想起“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千古治国至理精言,那么,束缚思想,控制人心是否也涵盖在“烹小鲜”之内呢?得民心者得天下,威慑天下不仅靠刀剑弓马,更要牢牢钳制民心,从心智上愚民与乐民。
胤禛抬头望去,亭子问只有一男一女,男子说不上英俊,倒也风流倜傥。坐在琴边的女人说不上貌美,却也中看。显然,这曲子是她弹奏的。胤禛不免多望一眼。
噫,一却是一位孕妇。嗬,原来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在此赏景弹曲调解心智,为孕妇逸情舒心开怀。
胤禛看看孕妇悠然安闲的神色,想想正在旅店里快要分娩的喜子多少有几分愧疚之色。
这时,那男的站了起来,向胤禛招呼道:
“先生独步苏堤,面有疑虑之色,举步迟缓,踽踽而行,一定有什么不快之事吧?人生不过百年,何必为身外之事烦扰心境,愧对西湖美景呢?如果先生不外,请坐在亭间听内子抚琴,也分享我夫妇的快乐。”
胤禛知道西湖岸边的人都十分好客,也急忙还礼答道:
“多谢盛邀,恭敬不如从命,打扰你们夫妇的雅兴了。”
那男的边让坐边自我介绍说:“在下姓陈,名世倌,字元龙,浙江海宁人。请问兄台如何称呼?”
胤禛欠身说道:“我姓赢,名真,并无配字,自京城而来,想做点买卖。”
“赢先生一定是生意场上不得意吧,杭州城就是这样,有名的鬼市,物价不稳,这与那些官商屯积居奇、轰抬物价有关。即使生意场上稍有失利也不必太在意,能赚得起,也能赔得起,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呢?像我——”
不待陈世倌说下去,他夫人就阻止住他的话。
“赢先生刚刚坐下,连一杯茶还未喝呢,你就滔滔不绝说个没完,还不知人家愿不愿听呢?”
陈夫人说着,把一杯沏好的西湖龙井递给胤禛,又陪礼说:
“赢先生不必在意,我家夫君心直口快,胸无城府,有什么说什么,刚一见面就说起自己的事,请赢先生多多谅解。”
陈世倌也有所歉意地说:“不是夫人提醒,我差点又把自己不愉快的事说了出来,平白无故给赢先生增加烦恼。其实,我的意思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看得淡一些,得失荣辱实在难以定论,古人都能‘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何况我等读书之人呢?比如我——”
陈世倌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胤禛急忙向他点点头:
“如果陈兄觉得合适,但讲无妨,我是十分乐意为他人排忧解难的,当然,也喜欢让他人帮我分担忧愁。”
陈世倌看一眼夫人道:“我还是讲了吧,话到嘴边不说出去心里憋得慌。”
夫人嘻嘻一笑,叹道:“你这毛病是改不了啦,吃了大亏还不警心,那就说与赢先生听吧。”
原来这陈世倌是进士出身,官至杭州学政,因不清官场事务,又心直口快,得罪浙江巡抚,被参劾罢官,闲居西湖。
陈世倌说道:“十年寒窗苦读时,一心想着考取功名荣宗耀祖,凭着个人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出将入相,做一代名臣名相。真正入仕为官时,才发现凭意气用事在如今的官场吃不开,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仍落得罢官在家的下场。”
陈世倌自嘲地笑了笑:“陶渊明辞官不做,隐居南山也许是看自己混不去了,与其让他人赶下来,不如自请辞官,这实在是一种明智之举。在写‘误入樊笼里,一去二十年’这句时,虽然看得开说得慷慨,但内心多少有几缕愤慨与不情愿,而到了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时,经过辞官后的心境调整,那才真正是不着丝毫痕迹的‘悠然’呢?正如我现在的心情,确实有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无为的超然心境,荣辱得失皆付清风明月。每日携夫人慢步西子湖畔,抚琴品茗,赏花咏柳,安度天年,不久再生下一位千金或儿郎日子也许过得清贫一些,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逸享天伦,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呢?”
陈世倌说着向夫人靠近一点,做了一个亲昵的动作,逗得三人哈哈大笑。
胤禛微微叹息一声,道:“陈先生谈古论今如数家珍,可见是位博学之士,如此人才被逼隐退,纵情田园山水,于己也许不是坏事,于国却是一大损失啊!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天下之大也许像陈先生这样的博学之士灿若群星,只可惜被贪官污吏给丧送了前程,如珠埋粪土,虽然放光,但放出的光只能给蝇虫蛆蚧便利,可悲可哀。”
“赢先生虽是商人却无半点铜臭气,举止高雅,谈吐不俗,句句让人深思,字字是珠玑,怜才之心让陈某感动。如果赢先生做官定是治世英才,经商也定是陶朱公那样的商人,为官与理财理不同而道同,途异心归。敢问赢先生从事何种买卖?”
胤禛唯恐说露了馅,让陈世倌看出自己的身份,淡然地笑笑道:
“我做买卖同陈先生为官不一样,陈先生是认准一个理,从得中看失,从失中找得。我却没有固定的买卖,看什么赚钱做什么买卖。也许是在下才识浅短吧,我至今还没达到陈先生‘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思想境界,我只能赢得起却赔不起。陈先生不会见笑吧?”
“如此说来,赢兄的心智更是高人一筹,能够胜算在握,决胜千里,这是张子房、诸葛亮的经营之道。但在下也提醒赢兄一句,输赢一盘棋,求之愈高,付出愈多,而胜之可能则愈小,身外之物只能留之子孙,是福是祸也难有定论。日月运行,阴阳互变,更何况是瞬息万变的生意呢?赢兄还是尽早从‘格物’中走出,在‘正心’上下点功夫。”
胤禛立即致谢道:“陈兄见教的极是,我也早有此心,只是在生意场上天长日久了,心智钻人了死胡同,敢问陈兄有解救的良法吗?”
陈世倌正要开口,李卫跑着喊着过来,他一见胤禛在此,急忙上前风风火火地说道:
“四、四爷,少奶奶肚子痛得厉害,看样子马上就要临产,而店主说什么也不允许少奶奶住在店里,立马赶我们离开,请四爷快回去。”
胤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十分不解地问道:
“我们住店给钱,在店里生产有何不可,告诉店主,我付双倍的钱行不行?”
“博尔多说了,只要同意让少奶奶在店里生产,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店主仍然不同意。博尔多又到隔壁几家旅店询问一下,情况大致类似,他们一听说要在店里生产都一口拒绝了。”
陈世倌解释说:“杭州这个地方有个风俗,他们最忌讳女人在自家生产,当然,自己的女人例外。他们说别人的女人在自家生产会给家中带来血灾,甚至灭门之祸,这虽是一种不可信的说法,但街头百姓却奉若神明,认为祖宗留下的规矩破不得。特别是这些经营店铺的人,他们更看重这些。”
胤禛一听陈世倌这么说,也露出为难的表情,如果亮明身份只怕会惹出更大的麻烦。杭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多年来一直是反清势力的聚居地,随时都可能有歹人出现身边,正如刚才遇到的那个叫曾静的算命先生,此人身份就十分可疑。
陈世倌见胤禛沉思不语,面有难色,便说道:
“如果赢先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去处,又不嫌弃敝宅简陋,可以让尊夫人到寒舍生产,我家中也有足够的仆从服侍尊夫人衣食起居,请赢先生尽管放心。”
胤禛知道陈世倌是刚罢官的杭州学政,话虽说得谦虚一些,从言谈举止、穿衣打扮看来也是富庶之家、豪门贵族。尽管与他是萍水相逢,但从谈话中可知他们夫妇也都是乐善好施之人,应该十分可信,喜子能够到他家中生产那是再好不过。于是,拱手施礼说:
“赢某在危难之中承蒙陈兄相帮,实在感激不尽,只是这样太委屈陈兄了。”
陈世倌还礼说道:“赢兄不必客气,我等读书之人也不讲究太多的陈规陋俗,一切还是救人要紧,佛家不也有句偈语:救人一命胜造五级浮屠吗?赢兄快去旅店收拾行囊,我这就回府让家人去车来接。”
胤禛急忙同李卫回到客栈,见喜子面色红晕,额头上挂满汗珠,知道就要生产了,一面安慰她几句,一边下令收拾东西。准备就绪,陈世倌派来的车子也到了,又忙着把喜子抬上车。这时,胤禛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陈府虽然不十分大,但却玲珑别致,布局摆设倒也雅致,从中见出主人的爱好与修养。
陈世倌把喜子安置在一个优雅的西厢房内,并请来了接生的稳婆,又安排两名侍从人员,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婴儿下生。
客厅里早已摆上酒菜,陈世倌和胤禛吃酒谈天,等候消息。从谈话中胤禛知道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从前明中叶陈氏家族就日渐兴旺,成为海宁望族,族中代代都有几位外出为官的人,也不乏官至极品之人,只是到陈世倌这一代,陈家就出了他一位进士,仅仅坐了几天杭州学政却又罢了官。在谈及身世时,胤禛只说祖籍东北,随父在京做些生意,曾经参加一次科考,因未就从此断绝为官之心。
二人正谈在兴头上,李卫跑来报告,说少奶奶平平安安地生下一位少爷,胤禛喜不自胜。陈世倌也很高兴,举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