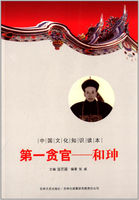在如意馆内效力的画师,通称“画画人”,传教士身分的外国画师则被称为“西洋画画人”,有的太监也称他们是“画画蛮子”,可见其地位并不高,但郎世宁除外,他被皇帝破例授予奉宸苑使,赏给了饰有蓝宝石的三品顶戴,所以在周围人的眼里,他是一个特殊人物。有的传教士对他有如下的描述:“画画的郎老爷,官名‘世宁’,圣名‘约瑟’,很有德的,万岁很爱他的,他有河道雪亮蓝顶戴,王公大臣面前,有体面。”
乾隆三十一年,年近八旬的郎世宁客死中国,乾隆命追赠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隆重办理丧事。郎氏葬于京西阜城门外葡萄牙墓地诸传教士墓中最西一列,北数第三号。
郎世宁为了主的事业,万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他遭逢人间圣主——乾隆皇帝,从而把西方的艺术和华夏古老的艺术融合在一起。郎世宁之所以能蒙受皇帝的垂爱,似乎是他不仅适应了宫中刻板而单调的生活,而且也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固有的画风,以迎合乾隆的审美情趣。
中国画大抵分工笔和写意两派,前者用笔细密,渲染工致;后者着意高简,传神而不求形似,但无论写意,还是工笔,都讲究气韵,强调不为物象所役。在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可与同时代名画家比肩的乾隆皇帝慧眼独具,对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域画风给予了高度评价,允许郎世宁等人用纯西洋画法,在皇家园林的殿阁楼台中绘上大量的油画,也为自己画了一幅幅油画御容,并让这些西洋画师把透视法等绘画技法移植到中国画苑,用中国画的传统材料和工具,仿照西洋画风格,追求物象的质感和流动的笔触。乾隆皇帝赞誉郎世宁为“神笔”,主要是欣赏他所代表的为中国画所不具备的西洋画写实的长处。因此他说“写真世宁擅”,“写真无过其右者”。正由于乾隆对西洋画法的偏爱,所以在当时清官中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国的艺术家们可以从那里窥见西方近代绘画的一角,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创作天地,让郎世宁这样才华出众的西洋画家们发挥他们独擅的绝技。
然而,乾隆皇帝毕竟只能从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去理解、赏析、品鉴和裁量这些纯粹异国情调的图画。他认为包括郎世宁在内的西洋画师们的作品,缺乏中国画特有的神韵,因而批评郎世宁的画说:“似则似矣逊古格”。这个看法与如意馆里中国画家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乾隆绝不满足于当一名客观的批评家和高明的鉴赏家,他还要按照自己的绘画观和审美观对这些“西洋画画人”的技法加以改造。奉旨作画的郎世宁等西洋人在清宫中是找不到一座可以恣意发挥自己才华的舞台的,他们只能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冲突的漩涡中艰难地寻觅一隅立身之地。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郎世宁在宫廷中所画的“线法画”虽给观者以纵深感,但又不尽守透视法的规则。来华的泰西使节看后不满意,说它“既不守透视法之规则,于事物之远近亦不适合”。他作画施彩虽兼顾浓淡深浅,使肖像、静物富于立体感,却因此而笔力不周,显得气韵不足。中国画家也不满意,说缺乏神逸,全无笔法。总之,郎画既非中国画,亦非西洋画,而是在乾隆皇帝的审美趣味塑造之下,开创的一种以西法为本,参以中法,据其西洋写意的素养,而仍以中国笔描彩绘为依归,最大限度地追求形神兼备的别具一格的新画体。尽管远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但它在中西艺术交流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
在中西两种文化传统、审美观点大异其趣的环境中作画的郎世宁处境之难堪是可想见的,然而他没有向旁人倾吐过自己的苦闷。他的如意馆中的同事法国人王致诚却难以忍受,在向教廷发回的信函中抱怨道:“终日供奉内廷,无异囚禁,主日瞻礼,亦无祈祷暇晷,作画时频掣肘,不能随意发挥。”怀着这样近乎愤懑的情绪,王致诚拒绝了频频掣其肘的乾隆皇帝授予他四品官衔的隆恩。
清朝最伟大的三个皇帝——康雍乾三帝——对西洋文化艺术的爱慕是一脉相承的。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喜爱郎世宁所绘的《百骏图》,他让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等验看步行日晷仪、西洋显微镜等,表现了对西洋器物的求知欲望。为人们所熟知的雍正头戴西洋假发的画像,最生动的地揭示了这个令人生畏的东方君主神往西洋文明的内心世界。不过雍正也好,乾隆也好,在真正了解西洋文化底蕴上,谁也不能同康熙皇帝相比。康熙也喜欢西洋艺术,但他更重视的是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乾隆则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他在诗中坦率地承认:“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再来看看他们祖孙二人对待西洋钟表这件小事的差异吧!康熙不仅热衷于搜集各式西洋自鸣钟和时辰表,而且在宫内创建了做钟处,聘请英国著名钟表设计师法斯·斯塔林主持仿制欧洲机械钟,终于制造出了“当时西欧技术最先进,工艺最精良的各式钟表”。而乾隆似乎对钟表的机械构造和功能毫无兴趣,他的精神贯注于玩意钟的外在细节,如“人头、手做象牙,衣纹另作鲜明,里面安排玻璃镜四块,门上玻璃三块”之类钟表的造型与装饰上,以显示他超人的艺术眼光。康熙皇帝从当时世界大势变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中西方的差距,敏锐地觉察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乾隆皇帝则缺少这种极可宝贵的忧患意识,至少他没有公开这么说过。他陶醉于数十名为达到传播上帝福音目的而效力内廷的画师、天文学家、测绘专家、外科医生……对他的崇拜和忠诚上,陶醉于对异国奇珍的广泛搜集,以及圆明园中几组欧式建筑的非凡气派上。乾隆的西洋意趣,固然反映了他的艺术气质,但他的“纵情恣意”于“异国风味”中,主要是为了炫耀,炫耀富有、炫耀权力、炫耀超越今古、至高无上的尊严,既向海内臣民炫耀,也向前来观瞻“天朝上国”的周边藩属和泰西各国使臣炫耀。
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若瑟第一的使臣巴哲格来华,这是乾隆登极后首次接待前来朝觐的西洋使节。当时长春园北路一带的谐奇趣等欧式庭园楼阁正在兴建之中,皇帝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加紧施工,想赶在巴哲格来京前完工。据如意馆内的西洋人记述:“钦差(按指巴哲格)未来之先,万岁对西老爷(西澄之)说过好几次,你们快快完西洋房子,你们的西洋大人来了,我叫他看我的西洋房子里的陈设,都是大西洋的很好的东西。”
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包括海西各国恃以夸耀的东西,也荟萃于皇家的禁苑之中。乾隆皇帝要让这位博尔都噶里雅国(即葡萄牙)的“钦差大人”瞠目结舌,自叹弗如,而拜倒在中央之国伟大君主的脚下。这种心情在他怡然自得地漫步于西洋楼时,往往从心底油然而生,且看他的《观谐奇趣水法》一诗:
连延楼阁仿西洋,信是熙朝声教彰。
激水引泉流荡漾,范铜伏地制精良。
惊潮翻石千夫御,白雨跳珠万斛量。
巧擅人工思远服,版图式廓巩金汤。
不幸的是,西洋“远人”并未宾服,中华版图也没有固若金汤。清咸丰十年(1860年)秋英法联军打到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包括乾隆皇帝用以向五洲四海夸耀中华声教的西洋楼,而时间恰恰在西洋楼落成后的一百周年。
据一位这场人类文化浩劫的目击者叙述:
圆明园和附近的所有宫殿,都一齐架火燃烧起来,两天两夜。这些遭劫的避暑行宫,火光熊熊地烧着,仿佛一张幔子,罩着当日的行幸处所,并且随着大风,烟雾吹过联军的营盘,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没资,仿佛一个长期的日蚀。
与焚毁同时,英法强盗开始疯狂的剽掠和野蛮的破坏,一位作壁上观的法军随军翻译描述道:
有互撞而相争者,有将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复起者,有矢誓有讪骂者,有大声嘶喊者,所获如是,犹之蚁穴为足所蹴,群蚁各衔米粮虫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军士至有以首探入红漆衣箱,或卧于织金绸缎内,搜寻珍物者;或有项悬珍珠朝珠者;或攫取时钟者;或以斧劈取箱笼所嵌宝石者。更有一兵,愚鲁可嗤,毁一钟,系先法皇雪斯第十五时代所制之物,以其水晶计针,而误以为金钢石者。火势正烈,若辈各运所抢之物,置于空地上,复以绸缎皮衣压火上以熄之,而火愈烈,穿过高墙,而若辈仍穿越宫殿,肆行抢掠。
被焚毁和劫走的除开有价值可以计算的金银珠宝外,还有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满箱满筐的珍贵书籍,神采飞扬而潇洒自然的名画法帖,以及商周鼎彝、秦砖汉瓦、历代名砚、乾隆时代的玉雕、漆器、名瓷等等绝世珍品……这一切一切,包含着乾隆皇帝那一言难尽的西洋趣味,在顷刻之间都被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