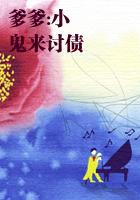云安由于产盐,早在西汉的时候,其所在地就设县了——朐忍县。北周时,将县治由万户驿迁至汤溪口,将县名更为“云安”。到了唐代,以云安盐的重要地位,太宗在云安盐场设云安监,以收盐课。宋元时期,云安监一直隶属于云安军。
以白兔井为首的云安盐井,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究竟流出了多少盐卤?又有多少盐卤熬成了盐?这些数据可能我们永远也不可知,但是一些基本数据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意象。
早在宋代时,云安盐就已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了,那时,云安监年产量约814000斤。明代洪武年间,云安盐产量突飞猛进,是宋代盐产量的2倍多,达2124620斤,到弘治时年产盐更是达2490000斤,是宋代的3倍。但是盐产量的过度增加,意味着燃料的大量消耗,云安附近的山林几乎都成了童山。到了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终因柴薪奇缺,产量大幅萎缩,仅产67200斤。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终致停产。
清初,为恢复和发展云安的盐业生产,开始鼓励私人凿井熬盐。又由于逐渐采用以煤替柴,解决了燃料的问题,云安制盐业逐步恢复,并有较大发展。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盐产量达13000000斤,是明代年最高盐产量的5倍,也使云安一举跃入四川最大的盐场之一。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令川盐济楚,产量又有较大增长。清末,由于改一锅一灶为一锅多灶,云安日产盐70000斤,年产盐达创纪录的24600000斤。
宣统三年至民国24年(1935年),云安盐的年平均产量约为31400000斤;其中颇有戏剧性的是,1920年云安地震,盐井卤水变丰,导致年产量提高10%左右。第二次川盐济楚期间,云安年产盐达49400000斤,创造了历史纪录。
从以上冗长的数据来看,云安盐的产量在三峡地区首屈一指,其他盐场难以望其项背,堪称“三峡盐都”,甚至与川南的自贡井盐也差不了太多,所以又有人将它与自贡并列为四川两大盐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靠盐的则吃盐。盐业为地方乃至国家的财税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学者估算,清代盐业正课加上各项摊派,每引可高达百两以上岁银,一个年产量有2000吨的盐场,实征岁银便可逾百万两之多。在宋史传记中,有一位名叫李周的御史,曾任过云安知县。他在任上时,为安抚百姓,免征盐课达百万之多,此举还得到了皇上的赏封,由此便可见其一斑。免征且百万,实征之数就可想而知了。总之,盐业生产事关国计与民生,稳定的盐业生产,既是当地贫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政府财政来源的主要渠道,又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为古代“下川东最巨之盐场”,清代云安围绕盐业生产谋生的灶户、佣工、商贩等在十万人左右,光是专为煎盐运送煤炭的就有上万人,“业此谋生者无虑万数”,因此,“邑人食盐利多,男女付贩”。在明嘉靖时,云阳“邑共九里,场家则四里,县家则五里。于四里煎丁优免以责,供煎于义为当”。可见,云阳县的盐业人口几占全县人口的一半。
“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筋力登委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食盐是生活必需品,许多人都在围绕它谋生。大诗人杜甫寓居云安,目睹汤溪河畔运盐船队穿梭如织的繁忙景象,在《负薪行》诗中为我们记录了反映劳动妇女不辞辛劳,不顾生死,上山砍柴,到盐井负盐贩卖的情景。当地的男孩长大成人后,或扬帆远行,或在山间奔波,或投身盐场养家糊口。“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便是杜甫在云安的亲身见证。经营盐业,销量大,获利丰。渝东自古以来就是产盐区,富商多出自渝东,而且多为盐商。如被称为“三蜀大贾”的龚播,《太平广记》卷四百一《龚播》就记:“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为业。”就是靠贩盐而致巨富。盐业使当地人摆脱了落后状态,生活在渝东地区算比较富足的。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诗赞叹道:“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归。”
由于盐业生产的繁盛,云安的商品交易也极发达。唐代李贻孙《夔州都督府记》载云安:“商贾之种,鱼盐之利,蜀都之奇货,南国之金锡,而杂聚焉。”云安甚至超过县城,成为域内最大的城镇。正如民国《云阳县志》所云:“蜀盐之利,比于全国,率在中上,县盐务之于全蜀,率于如此,然任土所出,于县境食货,实为大宗,利之所凑,食其业者,自卤主、煎户、运商、肆夥、汲拽、都养、洎乎沿江煤窿、舟挽、驮驱、转移执事于其间者,无虑数万人……亦为县境一大都会。”一代代的商人运盐出川,又带回本地没有的物品,使峡江内外的交流逐渐增多。
云安的盐除了本地销售外,还一度远销重庆、成都、渝东南和鄂西等地,这样,除了本地人在云阳贩运食盐外,还聚集了大批外地人来此做各种生意。在明代中期以前,盐业生产一直处于官方的严格管理之下,由具有特殊户籍、承担产盐徭役的灶户充任。到明代中期以后,政府逐步将盐井卖与私人;至清代,更是允许私人开凿盐井和从事盐品交易。于是很多外地人携资到此投资。一时间,云安镇商贾云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各地商人依靠自己手中的资金实力和特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行业分工:江西、陕西巨贾购置井灶,湖北黄州人拽扯卤水,忠县、丰都、万州、涪陵人熬盐,茶陵人刘、张、彭、陈四姓成立“四合店”总揽运输。这些离乡背井前来开拓新天地的人,依据自己的籍贯,逐渐在云安镇上开设了各自的会馆,有陕西会馆、湖北黄州的帝王宫、忠县的川祖宫、湖南的炎帝宫等。在清乾隆时期,云安有商号300余家,成为川东重要的工商业重镇,富甲一方,有“银窝场”之称。
盐是云安的特殊物质,是云安人的衣食父母。如果说盐是血液,被输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那么云安镇就是心脏,是盐铺就的网络的中心。云安的兴亡,关系到好多古代场镇的兴衰。
在离云安不远的长江边,就有这样一个与云安荣辱相连的古镇——西沱。西沱是古代闻名遐迩的“盐镇”,以经营云安盐(包括自贡盐)享誉巴蜀内外。早在宋代,云安盐就通过西沱转运湖北恩施、利川、来凤一带,西沱镇就是千里盐道的起点和转运站,到了明清时期,这里更是长江岸边商业贸易往来的重镇。西沱镇上的“下盐店”就是云安盐业商史的历史见证。下盐店依山面江,与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忠县石宝寨隔江相望。下盐店建于清初,相传为清代举人杨氏所建,建筑面积达1.3万多平方米,现存有正厅、回廊等。整个建筑系木质结构,金黄色的木楼掩映在重重叠叠的古民居之间,别具一格。下盐店的盐仓为封闭式建筑,墙壁全用木板横装,木板与木板之间吻合得天衣无缝,玲珑剔透,古色古香。西沱镇有一条著名的云梯街,街梯直上山顶,两边则分列各式店铺,云梯街就是一部不断运盐进山的梯子。在云梯街的下面,是始设于元代的水驿站。据说,每到夜里,停泊在这里的大都是装运云安盐的盐船,声势浩大有上百只,把整个江边挤得水泄不通。正是这些来自远方的盐,让西沱兴盛了上千年。
云阳县境内,除了汤溪河外,另一条著名的河就算澎溪河了。在澎溪河的高阳镇,有一大片平坦的土地,现在上面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居住劳作。可是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却是一处繁华的江边小镇。1998年以来,四川大学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多年的考古发掘,他们揭露了唐代的街市、寺庙、交易市场等,城镇的格局活灵活现。这个已经消亡的唐代古镇与距此约几十里的云安镇有一些关系。考古领队李映福教授认为,这个唐代小镇,有可能是食盐集散地,或者食盐集市交易场所。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宋代《云阳县志》说,云安盐在盐渠道上(水市)起滩(转陆运),运往高阳(明月坝)这里,再转水运,可通开州、利州等地,这条盐路的通道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云安盐造就了这些古老的城镇,云安镇就更是一座闪烁着盐之精华的古镇了。
如今的云安古镇,在两千多年的繁华后,终于抵挡不住现代制盐工业的冲击,日渐衰落了。1988年,与云安同在一个大盐矿——万云盐盆的万州高峰乡“万盐一号”井钻通后,云安的千年卤井正式废止了。自此,那些浸满卤味的盐井成为了人们凭吊的遗迹。2002年,考古者来到这里,发掘了一些远古的盐井和盐业作坊,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制盐遗迹,以及盐工们用过的遗物。考古学者的到来,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和记忆时代的开始。
云安,一个曾经富商云集,一个积淀了厚重历史的古镇,它的柜台、祠堂、会馆、龙君宫、五显庙、陕西箭楼、九间铺,它的幽深的附着青苔的盐井,如今都已沉入江底。那些盐井上的井架,提卤的木辘轳,蒸盐用的尖底锅,汲卤的桶,如今都被怀旧的人们珍藏着,但它们再也没有实际用处了。古老的云安,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