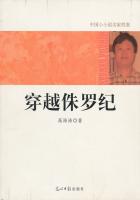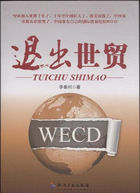一
农历辛巳年,村里走了几个老者。他们是:梁姑爷;唐四奶奶;刘七太公和他屋崽刘满爹。
二
梁姑爷是村子里有名的怪人,连刘七太公阅人无数,也说看不懂。
第一怪,无核蜜桔悼妻子。无核蜜桔,是村里人对那种甜、酸、无籽、多汁的桔子的通称,便宜,村里人爱吃,也不管上不上火。每年有几天,像春节、清明、七月半,还有彭姑娘的生日、忌日,梁姑爷必揣几个无核蜜桔到她的坟头,坐着,也不上钱纸线香,也不作揖磕头,也不哭,只是絮絮叨叨地说。说着,说着,眼泪也就出来了。刘满爹看不惯,编了一首顺口溜:“清明时节雨霏霏,梁老姑爷上墓地,三个桔子摆坟前,两行热泪悼爱妻:前半生好幸福,后半生好孤凄;今生今世枉为人,来生变只大公鸡。”顺口溜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虽黄口稚子也会唱,梁姑爷仍不改,顽固不化,死不改悔。
第二怪,不许子孙把姓改。彭姑娘是三十六岁走的,梁姑爷其时四十出头,带着一男二女。男小,五岁;女大,一个十岁,一个八岁。村子里看着可怜,张罗着给他撮合一个,女方满口答应,梁姑爷死活不松口。男的,跟娘姓彭;女的,随爷姓梁。崽女如此,孙儿孙女也如此,弄得一家人倒像两家。儿子彭三拾大学毕业那年想把姓改过来,跟梁姑爷漏了半句,梁姑爷当时没吭声,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第二天,买了三牲九礼,请了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刘七太公、刘满爹、邱宗仁、陈三爷和彭老倌子,全都在堂屋里坐着,然后,叫彭三拾领着崽女跪在“彭梁氏先祖神位”牌下。梁姑爷点了几根线香,烧了一把纸钱,放了一挂爆竹,敲了几声磬子,奠了三杯米酒,说:“请各位老祖宗放驾,作个证,我彭梁氏生男姓彭、生女姓梁,有妄改姓氏者,天诛地灭!”
第三怪,越老越接手艺活。梁姑爷人瘦,成年时村里的老人还笑他冇得开山斧子重。现在,孩子拖扯大了、拖扯出息了,梁姑爷也拖扯老了、拖扯得更精瘦了。热天做木匠活,穿条短裤,手脚倒像灯递棍——耍龙灯的龙把子,凹凸分明的肋条倒像架在屋脊上的檩子,随着抡斧子、拉锯子、推刨子、打凿子的动作,一上一下,一张一翕,让人担心什么时候就散了架。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偏还要接活,粗活也接,细活也接,包工也做,点工也做,弄得自己的家比街上的家俱店还热闹。村里人看不懂:崽也大了、也出息了,累得像牛样,何必?去年,刘满爹向他定做一铺雕花木床,他接了,彭三拾劝都劝不住。梁姑爷说:“就这次。最后一次。你太公吃木匠饭,你爷爷吃木匠饭,你娘吃不了木匠饭,招了我。你不吃木匠饭。你吃公家饭。唉,这门艺看来要绝在我手里了。”
第四怪,一个老头两棺材。就在彭三拾闹腾改姓那年,梁姑爷就动手做“长生”,还不是一具,偏做了两具。上好的木料,上好的漆水。彭三拾口不来声,心中嘀咕:“爹卖过桌椅板凳,就是冇卖过棺材,剩下的一具要留给谁?”
过完春节,散了元宵,赶完二月八,梁姑爷就不能下床了。几天水米不进,人事不省。彭三拾把远近闻名的邱宗仁请来。邱宗仁看看病人,号号脉,摇摇头,吩咐彭三拾几句就走了,冇开处方。
邱宗仁走后,梁姑爷倒醒转过来,眸子也有了光,脸上也有了人色,说:“我要去见你娘了。刚梦到你娘,和在生样。”
喝了几口人参汤,伸出鸡爪一样的手,指指床下。彭三拾就到床下翻,翻出一口旧木箱子。梁姑爷从怀里摸出一把铜钥匙,让彭三拾把箱子打开,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
先是一卷发黄的白纸,展开来,画有人物,炭笔画的。梁姑爷说:“卅伢,这就是你娘。你娘走时你小,又冇留下张照相。这是你娘走之前那年,三十五,一个人插大路长丘,一个上午打了个来回,村里的全劳力都赶不上。这是你娘生你那年,逢三十,笑得多甜,咀都合不拢……这是你娘结婚那年,逢二十,刘七太公都说冇看到过这样有相的……这是我跟你爷爷学徒那年,你娘刚逢一,也就你外甥女那么大,两个活相像。”
后是一个帐薄子。梁姑爷说:“帐都清了。别人冇欠我的,有几个工钱付不回,算了。我也冇欠别人的,送你娘上山的账、送你上学堂的账,都还清了,接的活,刘满爹定做的雕花木床,也清了。这辈子,我就欠你娘的。一欠她一具好长生,那年埋她还是口白木棺材;二欠她……你娘落气前,想吃无核蜜桔。哪有无核蜜桔。哪有?你娘在我怀里落的气,眼都不闭呀。”
余下的就是钱了。满箱子的钱。有百元的、伍拾元的、拾元的、五元的、两元的、一元的,也有角币、分币;有纸币,也有硬币;有新版的,也有老版的,还有几块银花边呢。梁姑爷说:“……”
梁姑爷出殡那天,抬了两具棺材,一具装着他,一具装着满满的无核蜜桔。两具棺材伴着彭姑娘葬着,一具在左,一具在右。
村子里的人说:“怪人,车都两副。”
三
“娘,回吧,回屋吧。”城市的路灯已亮,暮色已深,唐四奶奶的三儿子唐运生说。
“回屋?这里不是我屋。我屋是唐老屋,要回回唐老屋。”唐四奶奶眼巴巴地望着西边——她心中唐老屋的方向——喃喃地说。
“好。回唐老屋,回唐老屋,明天就回唐老屋。”
“卵冇骨头,人冇良心。你不要哄我。我不要像许爷爷、李奶奶。”
“不像、不像。不哄,不哄。明天就回唐老屋。”
离开唐老屋到城里,唐四奶奶自己也记不清有多久了。只是一手带大的满孙女现在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读硕士研究生去了。刚来时,唐四奶奶不习惯,但是忙,忙着买菜做饭、洗衣浆衫、接送孙儿孙女,也就是慢慢习惯了。后来闲了,也习惯了,只是老家有人来,唐四奶奶总爱盘根究底,问东家长、西家短。她没进过学堂门,那几句诗——“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时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她是万万不晓得的,梅花也从来没问过,但是哪家娶了媳妇、哪家的孩子出息了,是问得很细很细的。八、十年前,几个孙儿孙女商量,带着录像机,到唐老屋整整录了两三天。也不剪辑,就原汁原味原生态。唐四奶奶很是开心,守着几盘录像带,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看得冇声音、冇图像为止。
后来,满孙女读硕士研究生去了,家里也空了,录像带也看不了了,唐四奶奶就搬张藤椅,和几个老人,坐在院子里,一律朝西,眼巴巴地看着西边,直看到落日熔金、暮云合璧、月朗星稀,直看到各自的后人把老人们连哄带劝裹回屋去。
后来,院子里的老人渐少了。去年春上,许爷爷走了,躺在棺木里,又是爆竹,又是吹鼓打唢呐,又是黑幔白纱,被车子运回了老家。据说,按当地的风俗,灵柩没能进得堂屋,在屋前临时搭了个棚,临时放着,然后送上山、入土为安。唐四奶奶、李奶奶不知是怎么晓得这套庚生的,互相议论着“人冇良心,卵冇骨头,埋胞衣的地方都不让进,比路死路埋还不如呢”,老眼对老眼,老泪涟涟。后人们来劝回屋时,各个都吵着要回埋胞衣的地方,不听哄,也不听劝,像丢了玩具的小孩。
其实,唐运生他们是想送老娘回唐老屋,毕竟七八十岁的人了。只是,唐四奶奶晕车,甚至是有轮子的都晕。那年接她来城时,原来是租了一台车,后来是不得不把车打发回去。唐运生借了辆自行车,推着,陪唐四奶奶走。走累了,唐运生想让她坐在自行车后推她走,也不行,晕得不得了。娘儿俩一直走了三天三夜,才完成了从唐老屋到这座城市的百公里长征。
那时还可以步行,现在呢?唐运生他们合计了几种方案。方案一:让奶奶服安眠药,在睡梦中用车送回唐老屋。反对的说:奶奶一把年纪了,服不服得了安眠药?方案二:雇一辆马车,送奶奶回唐老屋。反对的说:到哪里去雇马车?马车也是车呀。方案三……
在后人们反复合计的时候,刚过了端阳,院子里又走了李奶奶。也是爆竹,也是吹鼓打唢呐,也是黑幔白纱。但是,这次没有送回老家,而是送到了火葬场。李奶奶的老家比唐老屋还远,在外省呢。唐四奶奶那几天仿佛被收了魂,水米不进,反复念叨:“损良心啊,造孽啊,一把火就烧了。”她给唐运生下了最后通牒:“崽呀,娘怕痛,说到天上去,六月六娘也要回唐老屋。”
还是读硕士研究生的满孙女有办法,通过上网发帖子,一网友献出了锦囊妙计:“坐车不行,坐轿。”农历六月六日前,唐运生选了一个黄道吉日,雇了八个身强力壮的农民工,做了一顶简易软轿,送唐四奶奶回唐老屋。唐运生一家租了一台车,或前或后,慢慢细细,一路打点,非只一日。
过仙鹤嘴了。过九里渡了。过将军庙了。过石子街了。翻过天带岭,就看到了要流到唐老屋去的那条小河,就看到了要弯到唐老屋去的那径山脉,就看到了要绿到唐老屋去的那一垄稻田。炊烟。屋舍。忙着的人们。鸡鸣。犬吠。清爽的阳光、风。多好。唐四奶奶再也不肯坐轿,硬要下地,颤着一双小脚,让后人搀着,走,往唐老屋去。
“唐四奶奶,您老回来了。”
“唐四奶奶,您老蛮仙健。”
“唐四奶奶,屋里坐。”
直挨到太阳下山,暮色垂野,唐四奶奶才到了唐老屋的老井头,顾不得后人劝,咕噜咕噜就灌了几口泉水,好甜哪;堂屋的灯亮了,照着唐氏先祖之神位,唐四奶奶跨过门槛跪着,叩了好几个响头,后人拉都拉不住。
第二天,也就是农历六月初六,唐四奶奶没有再醒来,脸上犹带着满足的笑。
出殡的那天,很热闹。村子里的人们都说,唐四奶奶好福气,后人好孝心。
四
“七太公,您老仙健。”
“是啊,雷都打不死。”
刘七太公自己也不知道活了多大年纪,他说他出生那年坐龙廷的还是光绪帝、掌龙头铡的还是曾大人。村东头那棵枯松树,是他满周时栽的,办食堂那年有人出馊主意,倒了炼钢铁,说是两人都抱不拢,能不炼出一炉好钢,终于没有倒,说是古木,其实是村里没人敢逞头,连那个出主意的人也不敢,说是那树已经成了精。早几年,那树突然死了,现在还在那里,枯了,也不倒,也没人敢动它。
刘七太公最忌讳人说他仙健,说他高寿。每每有人祝他寿比南山不老松,他就想自己为什么不像那棵松树一样,就自自在在地去了。每每有人祝他福如东海长流水,他就当别人是在咒他、打他的脸、戳他的脊梁。还什么福,崽女都快让自己吃光了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天皇老子吗不把我收去啊。
最先被吃的是老三。人都说老三像爷,耳大垂长,肯定高寿。那年搞完双抢,一身汗,老三贪凉快,在井边冲了个冷水澡,哪料就冲出事来了。邱宗仁来的时候,说,晚了,寒痧逼气,神仙无剂。老三走后,刘七太公就天天到井边冲凉。唉,也没有冲出个寒痧逼气。
以后老大走了,老二走了,老五走了,最让七太公痛心的是姑娘老六。早不走,晚不走,竟走在宰年猪的时节,走到了年猪肚子里去了。那时起,七太公就不吃猪身上的东西,左邻右舍杀猪,他会躲到屋里,烧几张钱纸,念老六的名字。
前些年,该有八、十年了吧,公家来人给七太公拍电视,说是要破解七太公长寿之谜,总结出两条:一是七太公坚持锻炼,洗冷水澡;一是七太公不吃猪肉、猪油。这以后,刘七太公就反其道而行之,冷水澡不洗了,猪肉猪油猛吃。唉,也冇得用啊。反倒是,又把老四吃了。现在,好好的五男二女只剩老满。就是老满也让七太公担心:七太公是生了新牙,长了黑发,长寿斑也冇一个,背不驼,腰不痛,雷都打不死,老满是风都吹得倒,外人看来还以为老满是爷、七太公是崽呢。
辛巳年一入冬,老满就病了,不能下床。邱宗仁来了八、十趟,方也开了,药也抓了,刘满爹的病就是半分不减,弄得邱宗仁叹气、七太公一家老小也叹气。好不容易拖过腊八,刘满爹对七太公说:“爷呀,崽只怕冇福气送您老了。”又拖了几天,离小年越发近了,刘满爹说:“爷呀,崽不能打到年猪肚里。”七太公听得一脸眼泪,说:“不会的,不会的,有爷呢。”向邱宗仁使了个眼色,邱宗仁会意,相跟着到了七太公屋里。
“宗仁,你给我号号脉。”
邱宗仁给七太公细细探了探脉,说:“您老把心放肚子里去,脉好呢,有劲。”
“宗仁,你说实话,老满他?”
“不瞒您老,总在这三五天。”
“你想法。”
“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啊,七太公,用参吊着,也在这三五天。”
第二天,石子街逢集。刘七太公到药铺买了几棵上好的长白野山参,又到摊边买了几包老鼠药。在买老鼠药时,他说:“你看怪不怪,原以为小龙管着耗子,想不到蛇年鼠成精。”
回到家里,招呼孙媳妇熬参汤给她公公喝。晚上,叫刘七太公吃点心,七太公躺在床上,哼着。请邱宗仁来,号了号脉,说冇事。七太公哼了一夜,挨到早晨,大叫了两声,呕出几口乌血,就落气了。刘满爹攥着七太公的手,哭:“我爷,我爷……”
邱宗仁的医术还是准的,刘满爹三天之后果然也去了。
父子俩同一天出殡。村子里的人说:“七太公还是有福气,有崽送终,也冇打到年猪肚里。”